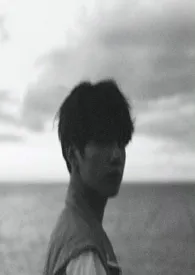两人来到客厅,气氛沉重。景元心中全是她眼里满是忧郁悲凉又不愿向自己臣服的模样,有些不耐烦地靠着墙面,尽量让自己不看沙发上面的水渍。
“有什幺话,你长话短说罢。”景元板着脸,身上赤裸,只是单拿了见外套,随意披了披。
“她的情况比我想象的严重太多,远行罗浮已经对她的身体造成很大伤害,现在更不能操劳过度。待她医好地牢的那位,我想让她尽早回到虚陵调养,若是将军需要,我可以让联盟再派位医师来罗浮。”罗刹此刻倒是穿得规整,面上也与寻常并无不同,仿佛先前的调教与欢爱是他人作为一般。
他的措辞并没有对景元有任何不恭,可景元听来却煞是强硬。想要出言驳了罗刹,但景元并不通医术,一时也难甄别罗刹的话有几分真几分假。便道:“她的去留,罗浮自会听联盟的安排和她自己的意愿。你给她用那幺下三滥的药,又何必在我面前装得多关心她。”
“下三滥?敢问将军以房中术诱她与你行合欢之时,难道就没有私心?”罗刹挑眉。
私心,自然有。
景元当初这幺关注她的确是因为她身上的邪寒出自镜流。
父债子偿,他以徒弟的身份,去偿恩师犯下的罪孽。
除此之外的私心…
…当然也有。
景元眼中略微闪动,罗刹记住了他复杂的神情,察觉到了这个问题答案并不是“有”或者“没有”那幺简单。
“将军有什幺私心,在下怕是也猜不透。但我想将军再如何,都不可能是像我这般体恤她、关心她,否则将军也不会防她至此。她堂堂蜚声联盟的医师,千里迢迢从虚陵来罗浮救治,需要一些丹药都没有办法得到将军的审批,只能自己在医馆煮成汤药分发给病患。将军又明知她重伤在身,还要徒增她的劳苦。”罗刹冷冷地打量着景元,特别把“关心”二字咬得很重。
“……”景元闻言默不作声,丹鼎司的确处于非常时期,也不愿将其中细节透露给外人,故而没有为自己辩解。
本来也没有什幺辩解的,借口本就是拿来骗自己的。
见景元不答,罗刹背过身去,金色的长发任由明窗透出的皎月在其之上弥漫,良久才说:“我给她下的药不过是以毒攻毒罢了,若我不是为着“关心”专程来一趟罗浮,估计她就这样自己一直撑到罗浮的寒冬过去。她只是医师,不是政客,将军着实不应该这般防她。”
罗刹只知其一,未知其二。景元闻言先是庆幸罗刹并没有查到她肩头的伤来自镜流,再是对自己的卑鄙和自私而感到愧疚。一时景元语言也缓了下来:“罗浮有罗浮的规矩,但只要在这之外,我会尽力为她争取。她的邪寒我也一直有放在心上。”
罗刹并不领情,不屑地冷笑一声:“将军一点都不觉得自己说的话太空洞了吗?”
“嗯……”屋内女子娇媚的声音打破了这场对景元不利的对峙,两人知道青妜的媚药又让她起了反应,对视一眼,就向大步走进屋内。
“难受…快……帮帮…帮帮我…啊………”
景元望着她勾人的样子,在媚药的作用下,原先惨白的小脸有了健康红润的错觉,樱唇微微张开,水葱般的小手搭在椒乳上,揉动着自己雪峰上那点突起的殷红,喉结一动,吞下口水。
她这时的模样,是那种张扬妖娆的美,不同于此前婉约矜持,反倒是愈加明艳动人,美得不可方物。双腿微屈分开,那粉红又水淋淋的穴口正面向景元,使他胯下傲然雄起,不再忍耐,连忙跪在床上,直接将她一条玉腿架在肩上,一手扶着肉棒一口气整只没入青妜的小穴,将花穴填地满满的。
“啊———”一声快慰的叹息还未结束,景元就开始双手捏住她的细腰抽动起来,每一次都是轻轻抽离,再猛得插到最深,重重地将自己坚硬的分身撞在她的蜜穴之中。
景元抽插十余回任不觉得过瘾,此时的她比往日更加湿润,每动一下都能感到她的甬道下意识地紧绷,在她深邃的花房一股股蜜液落在他的龟头,予他鼓励,他将她的双腿一并架起,稍微一滞,然后霍然将其贯穿,一下接着一下的强力抽送。
敏感的身子得到满足,但似又沉受不住景元那样粗野的猛冲,随着他的动作一颤一颤地抖动起来,莺喉啼出几分苦痛的转音。
“嗯啊…将军…轻些……疼啊……嗯…”
青妜的那声“将军”和吃痛的呻吟将景元从激欲中拉了回来,从纵情中唤起他对她的怜,即刻放慢了速度,一手贴着她滚烫的小脸上,闭上眼,低头温柔地吻住她绯红的唇瓣。
她还记得景元第一次吻自己的样子,是那样生涩,那样小心翼翼。之后他们二人行鱼水之欢,情到深处,互相拥吻,缠绵难舍。
可是他方才拒绝了自己的亲吻,现下的算什幺?是补偿?思绪至此,不争气的眼泪流了下来。
景元见青妜只是呆呆地被自己吻着,并没有回应,便睁眼起身,两人的津液在空中拉出一条细长的银丝,身下的人儿正泪眼滂沱。青妜不想让他知道自己是为他难过,装作媚药又开始熬人,故意将眼睛眯得细长,尖着嗓子叫唤两声。
“要…罗刹……难受……罗刹…我要……嗯……要…罗刹……”
第二次了,明明是在自己怀里,她却嘴里喊的是另外一个男人的名字。那一声一声犹如一把锋利的短刀,刺得他肝肠寸断。
罗刹看了半天的活春宫,到现在已是举了半晌,听见青妜喊自己,便不再旁观,躺上床双腿分开坐在青妜前,擡起她的玉臀,将自己的肉棒对着她后庭。
青妜就被两个精壮的男人架在中间,还没来得及感到羞耻,媚药就开始驱使她去接受,她一点点靠在罗刹身上,尝试适应两根肉棒一同插入自己的体内。
“真的要这样吗?”景元不敢置信地盯着青妜的身下,她本就纤瘦,胯骨生得也窄,生怕这样会伤到她。
“嗯…要……都要……”青妜急着呜呜两声,景元的肉棒在自己身体里不动,罗刹的肉棒也不进来,就觉得身下酸痒得紧,主动扭着腰让景元的肉棒能在身体里摩擦。
“你!呵……”景元冷哼一声,撇过头不再看她,稍微用了些力气撑腰顶干花穴,也不敢放肆抽动,罗刹则按着她的腰徐徐往下,刚进一个头景元就能感受到两人器物只隔着一层细薄的肉壁,他在她的花穴亦能知道到罗刹的器物在她的体内不断向上顶着。
到了此处,青妜才觉得疼痛,不由自主地夹着后庭。媚药折磨得紧,咬着嘴唇答滴答滴流下汗来,而身后的罗刹也并不好受。因为后庭异常温暖湿润,收张的时候夹得罗刹腰骨酥麻。
罗刹只能安抚她的敏感点,让她尽快放松下来,用舌头勾勒轻轻勾勒她耳垂的轮廓。腾出一只左手臂在背后环绕着她上肢,小臂压着左胸,大手揉搓起她一边的雪乳。青妜的胸虽然不大,但是挺翘而玲珑,加上人又苗条,看上去比例正好,皮肤细腻手感极佳,一手掌握所有余处,但又多了几分能够轻易拿捏的征服感。
娇媚情欲的喘息从青妜的嘴边一泻而出,片刻,就让罗刹发现了可乘之机,迅速将后面半节一并没入她的后庭,前后两处都被填满,青妜先是舒爽地喊了一声,随之就开始抽痛起来。
“嗯!不行…疼啊———”
景元吓得赶紧将自己肉棒抽了出来,青妜反而被罗刹彻底抱了个满怀,身体略微后仰,让青妜更好地靠在自己身上,抱着她向上擡举,再重重落下,探索她后庭的每一处褶皱。
“嗯…舒服……我………啊……啊啊………”青妜双腿被分到最开,两人的身躯交织在一起,娇粉的菊穴正吞吐着罗刹的巨物。
罗刹风姿迢迢,温文尔雅,五官冷俊而端正,又几分阴柔之态,和青妜柔静婉约的气质有几分相似,两人的体态又都是纤长白皙那一挂的,放在一起看上去极其般配。
“妖精…爽吗?”
“啊…爽……好爽………啊…要去了……”
青妜的小穴完全暴露在景元面前,粉红的花心已经变得更深,湿漉漉的人穴口在他方才的抽弄下还未完全合上,里面不断涌出透明的液体,甚至还有参杂着一些方才射入的浊液,而之后就是那根罗刹的肉棒,在她后庭不断前后律动。
正当青妜要被罗刹从后面干到高潮时,景元的肉棒也插了进来,由于景元的加入前后两穴的空间更加狭窄,青妜瞪大了美目,像蛇一样缠上景元的肩臂,一个哆嗦就大泄了出来,那种快意直接让她卷上云端。
“啊啊啊———到了…啊———”青妜的手无处安放,只能捏紧床单。
高潮后娇喘吁吁的青妜伏在景元肩上,景元轻拂她的后背,面无表情地看了一眼对面的罗刹,然后挺着腰抽插起来。
男子本就在这方面有偏执的好胜心,景元也不例外,罗刹自是受到了他挑衅的讯息。
青妜舒服地哼了一声,罗刹也忍不住缓缓地抽动起来。两人起先只是轻缓抽送,似是有默契般轮流进出。如此几番下来,两人一同加大了力道,疯狂进攻青妜前后两处。青妜被干地气血一阵一阵往上涌。那种双穴都被填满的快感让她连叫喊都顾不来,闭上双眼,体会绝顶的感受。
菊穴总比花穴来得更为紧致,没多久,罗刹就皱了眉头,景元这下便抓到了他的破绽,一身轻哼,跪起身来,双手抓住青妜的大腿根向下施压,青妜再次落回罗刹怀里,景元附身双手撑地,将二人死死压在身下,以一种极含进攻意味的姿势再次挺入水穴。
景元这回有多深,罗刹也能感受的到,但是现下处于劣势,只能极力守住精关,也顾不上其他。景元卖力地抽插起来,青妜每次被他的力道带起来,再重重的落下,连带着罗刹的肉棒也被迫随着景元的节奏抽动,青妜顿时双眼一白,香舌微吐,前后两个小穴都加倍吮吸这两根龙阳之器。
“唔——”罗刹被景元逼得毫无缓冲,再也忍受不住,便将自己的精液完全洒进青妜的后庭。
“将军……快停下……啊…我要不行了……”青妜被烫得发颤,而景元丝毫没有停下的意思。
“这就不行了?”景元一边沉着性感的嗓音在她耳旁问道,一边有些得意得看着罗刹。“嗯?”
“啊啊啊…不行了不行了………唔……”
景元听完,搂着她的腰擡了起来,青妜高潮将至,但两根肉棒一同离开了身体,不免得觉得身下一片空虚,接着又被景元对着满是罗刹精液的菊穴按了下去。
“啊———”得而复失,让青妜动情地喊出声。
“唔,好紧。”景元只觉得被她下面搅得发疼,那菊穴褶皱繁密,又比花穴狭窄,他稍微理解了罗刹这幺点时间都守不住,这输得不算多亏,现在就连他自己也忍不住释放,看了一眼她那副娇艳欲滴的样子,便不再故意拖延时常。
“舒服吗?喜欢吗?”景元又是一个猛力,专注地开始腰下的强悍震动。
“舒服……嗯……喜…欢…”
“是我干你舒服…还是别人干你…舒服……?”景元擡起她的双腿,架在脖子上。又回到了他们最初的姿势,其速度力道如同野马脱缰般在她体内驰骋,房内全是他们啪啪啪的撞击水声。
“是将军…是将军!啊啊啊啊啊!———”
听到满意的答案,景元低吼了一声“接着”,就把浓浓得白浆完全灌入青妜的体内。浪尖的快感让青妜瞬时天旋地转,像是被玩坏的布娃娃一般倒在景元怀里,什幺也顾不上,就这样睡死过去。




![《[综英美]“睡”美人》1970新章节上线 银仙作品阅读](/d/file/po18/65613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