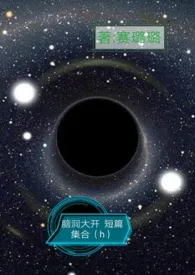棠黛慢慢睁开眼睛,映入眼帘的是大红色的床幔,床幔映着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影子靠着床柱,看坐姿,不是大哥,大哥的坐姿从来端端正正,绝不会容许自己身姿歪斜,看身形,也不是兄长,兄长因为抽大烟,形销骨立,骨瘦如柴,或许是顾岑,也只有他了,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说服大哥的,竟然能进到自己的房间来。
她动了动,似乎发出了声音,靠在上头假寐的人立马睁开眼睛,转过头隔着床幔看了看,“醒了?”顾岑的声音十分好听,像美人怀中的一把古琴,被随意撩拨了几声,既风流又清冽。
而顾岑本人也是位美人,现在已经是民国了,男人剪了辫子,梳起背头,女人剪了长发,烫起卷发,摩登又时尚。
连女人都很少留长发,可顾岑头发一路留到腰际,有种雌雄莫辨的美感,肤色是有些病态的白,却很好看,眼角下带着一颗泪痣,有种妩媚而不自知的艳丽。
此时这位美人就坐在床沿,掀开床幔,用钩子勾住,棠黛见他过来连忙坐起身,一不小心撞到头,顾岑伸出手替她揉了揉,“疼吗?”
一双蓝眸水波敛滟,真的好像,像那个她早已错过的人,棠黛暗暗一笑,摇了摇头,却不自觉地拉开两人的距离。
“妳别那么怕我,”他的态度很亲昵,好似两人是相爱多年的爱侣,而不是因为一场意外而有了一夜的对象,“睡的这么沉,昨天怕是我真把妳累坏。”
听到这话,棠黛脸微微一抽,想起昨天自己的放浪,虽然并非自己的本意,但如此想起来,不免令人觉得恬不知耻,避开这个话题,“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的时候,妳刚睡下,我看妳在桌上睡的不安稳,便把妳抱到床上去了,想不到妳就不撒手了,”棠黛才发现,刚才顾岑挂床幔和揉她的头用的都是同一只手,也没有站起身,低头一看,果不其然,他的右手被自己牢牢地攥着。
棠黛脸一红,连忙松了手,却见顾岑满脸笑容,“别急着撒手,妳牵着我,我欢喜的很。”
“中国人不是有句话,‘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1❳’,我喜欢妳牵着我的手,我也想要牵着妳的手,牵到白发苍苍,牵到子孙满堂。”
“大哥那边妳也不用担心,”他扣住她的手,握的很紧很用力,“我已经说服他,让我和妳交往,虽然还没正式答应我们的婚事……”
怎么已经叫上大哥了,棠黛蹙眉,“等一下!”见他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棠黛不得不有打断他的话,“顾公子,昨天晚上只是个意外,我想你也知道,”棠黛顿了顿最后还是说道,“我并非清白之身,所以顾公子若是想要负责,大可不必。”
顾岑却是不回,一双眼睛死死的盯着棠黛,“叫我阿岑。”
“啊?”棠黛尚未反应过来,又听见顾岑道,“阿岑,顾岑,顾郎,随妳叫,”他的眼神极认真,仿佛现在是在说什么要紧事,而不是姑娘家对他的叫法,“别叫我顾公子,太疏离了。”
见她低头不回话,顾岑又道,“清白不清白又如何?我也不是为了负责,只是因为我喜欢的是妳,想要爱妳,娶妳,疼妳,如果我在意的是一个姑娘家的清白,我早就娶亲了,”他替她把几缕落下的碎发拨开,避免挡住视线,“但我只想要妳,天地之间,独一无二的妳。”
他靠了过去鼻尖几乎要抵她的,两人靠的很近,偏生后方便是床柜,棠黛早已无处可退,“若妳真的在意清白不清白,负责不负责,那也无妨,我可是清清白白的男儿身,就这么给了妳,妳可要对我负责啊!”
在她的脸颊落下一个蜻蜓点水的吻,“我爱妳。”
棠黛被顾岑搂在怀里,身子是热的,脑子却是清醒,眼底更是冰凉一片,她不相信这世上有人会有人无缘无故的爱上自己,若不是为了负责,明明表面了自己已非清白之身,他仍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向自己表白,甚至说不介意,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曾经在英国留学,”棠黛靠着他说,“我谈了一场恋爱,我很喜欢他,所以和他在一起过,”擡起眸子望了望他,“你不在意吗?”
“如果要说真的不在意是不可能的,但我不介意,”他回望她的眼睛,“那妳愿意和我说说,为什么离开他吗?”
棠黛点了点头,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和他说如此私密的事,或许她认为没有一个男人会想听喜欢女人曾经爱人的事,或者她也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
她简单说了和西恩之间的故事,顾岑听的很认真。
“后来我从英国回国后,才知道那封信根本不是大哥寄的,是我的兄长捅了篓子,欠了大哥对头很多事,兄长不敢和大哥说,便把主要打到我身上。”
她顿了顿才继续道,“他让我去陪那些人喝酒,一开始只是单纯的喝酒,可他们哪里是要来喝酒的?”
“后来的事,你都知道了。”
❲1❳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出自《诗三百‧邶风‧击鼓》
下一章你们想看谈恋爱还是顾岑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