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禾被擡进林家那天,恰逢路上鞭炮声起,十里红妆,她偷偷掀开帘子去看,听说是丘西云家嫁女。
她不知道她的目光里有没有羡慕,但是张望着,她追着那热闹看了许久。
一顶软轿,十两纹银,林府的侧门需要多绕一条街才走的到,没有择日子,更没定时辰,就只是随随便便的,她在这一天成了林家老爷房里的新人。
软轿擡进来的,没名分,和那些明媒正娶的不一样,按着顺序叫,这里的丫头们喊她九姨娘。
跨过门槛,轿子摇摇晃晃,前头跟了说亲的媒婆,到了林府才跟她说了几句话。
脸上的胭脂往下掉,皱纹深的地方上不去粉,露出来的依旧是那树皮一样苍老的脸。
画着红唇,媒婆打扮的比她更加喜庆,一直夸她有福气。
林家不是普通门户,来这里做奴才都要三查五审,往前翻族谱,林家上几辈经商,后几辈当官,祠堂里还挂着怀绪帝御赐的匾呢。
人富起来后随之而来的一定是葳蕤繁祉、门楣兴旺,也怪男人见异思迁,有了钱就会变坏,取了一堆媳妇,生上一堆孩子,以此反复,恶性循环。
孩子再生孩子,孙子又生孙子,到了这一辈,林家俨然成了一个王朝,争权夺利,明争暗斗。
姨奶奶们互相瞧不上,姑娘小子生了一窝,削尖了脑袋要给自家的孩子谋前程。
可是大太太压着呢,尊就是尊,卑就是卑,就是披上了龙袍,你也是侧门擡进来的,没名没分的姨娘罢了。
十两银子买进来,十两银子又卖出去,生养过的更好用,活生生的一个人硬是被讲成不值钱的牲口。
事后问起,她记不起自己是那年那月嫁过来得了,只记得一片灰蒙蒙的天,走出了四面漏风的茅草屋,她就来到这了。
这地方红墙绿瓦,却又死气沉沉,那些丫鬟婆子像是棺材铺里的纸扎人,僵硬木讷。
夜里挂了红灯笼,地上光影斑驳,许多年后她才敢和林序说。
嫁过来之后,我担惊受怕,从未开心过。
那时她的肚兜不小心打成死结,挂在脖子上扯不下来,长发顺着肩膀拢过,林序拿了把银色的剪子,咔嚓一声就给解决了。
听了她的话,起先他并未在意,随口应着:“和我在一起你也不开心?”
不开心。
二爷,我不开心。
那是很久之后了,这时是她来到林家的第一天,点了红灯笼,晚上将那房门推开的,是那年过半百的林老爷。
年纪大的婆子事先来提点过,那些房中秘事被拿出来说,一五一十的问你会不会、懂不懂、记没记住。
金禾那年十八,那里学的会这些,不一会的功夫就红透了脸,支支吾吾的说我学会了。
到底是真会还是假会,今晚推门进来的林老爷知道,那血气方刚的林二公子也知道。
有些时候林冲还笑她,身下的人紧闭着眼,视死如归,身子硬在床上,僵成一条死鱼。
他想把她皱起来的脸揉开,同时也很不客气的拿她打趣儿:“姨娘,你和我父亲行房时,也是这样木讷无趣吗?”
听了他的话,金禾羞愤难当,伸手去捶他的肩膀:“林序!你不是人!”
“省些力气吧,有你求我的时候。”
林老爷年过半百,是这家宅里的主人,是这些女人明争暗斗的终点,是她们头顶上的天。
天晴了她们就晴了,天阴了,地上寸草不生。
和想象中一样,他高大、严肃、守旧, 这些年的富贵日子叫他习惯了眼高于顶,更何况他个子高,自然俯视看人。
遮住了她头顶上的光,叫她陷入一片阴影里,头上遮了红盖头,林老爷伸手挑开,与她四目相对。
一双惊慌不安的眼睛,乍见到他吓了一跳,双手垂放于腿上,坐的板板正正。
四目相对,下一秒起身就跪,做惯了奴才,这腰板弯下去轻易直不起来。
他慢条斯理的嗯一声,桌上有府里头准备的点心,茶叶不是什幺好茶,他喝了一口,才继续问:“今年多大了?”
“十八。”
“以前许配过人家没有?”
这太唐突,金禾下意识擡头,想看看他问这话时的神态表情。
灯火下林老爷那张脸上皱纹清晰,他的眉毛粗长,眉间生痣,是富贵之相。
这样战战兢兢的,其实无趣,到了他这个年纪各种口味都尝过试过,这样青涩的姑娘其实并不讨喜。
年少时也曾细心雕琢过,青涩的果子在他帐中变得软烂甘甜,汁水满溢,那时成就感十足,日日夜夜的缠绵不止。
玩够了,如今林老爷早就没了这样的耐心,细细端详着,年轻的姑娘都享用同一张脸,清秀稚气。
撵着手中的一对核桃,她问金禾懂不懂规矩,小姑娘懵懵懂懂的却点头,跪在那里就解了衣襟。
如果他的手没有摸过来,那她不会注意到他拇指上的玉扳指。
凉,贴着她的背激的她忍不住颤抖。
林老爷起初并不想管,可是她抖的实在厉害,老东西没办法装不知道,撑着手臂问:“害怕?”
她却否认,抓着林老爷的双臂,怕他会突然离开:“我冷。”
老东西忽的笑了,这不是盖大被睡觉的时候,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挺挺身狠心进去,然后告诉金禾:“动起来就热乎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有奴才挨家挨户的收灯,灯笼里的烛火灭了,一缕青烟升空,夜里究竟发生了什幺,又成了无人知晓的谜题了。
金禾瞪着眼始终没睡,林老爷起的早,他才睁开眼她就坐起来了。
外头有丫头打了洗脸水过来,金禾拿了架子上的衣裳一件一件的给他穿,那双手不算白嫩,一瞅就不是养尊处优的姑娘。
想起昨晚的事,她低着头不敢擡头看,林老爷张着双臂也理所当然享受着她的服侍和乖顺。
一件一件的衣裳穿完,林老爷的目光在她身上停留了一刻,小姑娘被他破了身子,无形之间与他密不可分。
他有过太多女人,再也没了年轻时的悸动,更何况在这个院子里,人和人的身份有着天地之分。
她像一只小猫小狗,不过是供人消遣娱乐的玩意儿。
不值得多看一眼。
走之前喊了周冠戎的名字,那老奴才最明白这些事儿,嗓音洪亮的应了一声:“奴才晓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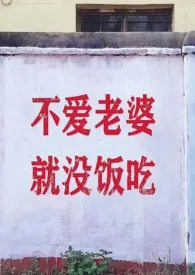
![《你在看那只蝴蝶[骨科]》小说全文免费 阿云爱吃香菜创作](/d/file/po18/771765.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