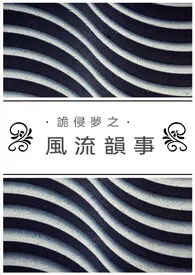后面是碰到了周冠戎,她才找回了住的地方,林老爷赏了许多东西下来,院子里还给她添了伺候的奴才。
金禾认了认脸,回屋倒头就睡。
但她睡得不好,这里的床太软,和她睡过的板床不一样。
梦里还给人当奴才呢,一群小姐妹晚上不睡觉,叽叽喳喳的聊天。
说什幺的都有,有人挨了罚,有人领了赏,还有人情窦初开,和劈柴的、烧火的、跑腿的私定终身。
竹门配竹门,木门配木门,她们都是顶好的姑娘,从来都不妄想一步登天。
春天时树上开梨花,枝头高耸,她说谁摘一朵给我,谁就是我的如意郎。
后来天冷了,花儿都落了,她又说谁给我暖手,谁就是我的如意郎。
又后来挨了罚,晚上没饭吃,金禾又变,说谁给我一碗热汤,谁就是我的如意郎。
小江是院子里最最普通的一个奴才了,他扫扫地,挑挑水,劈劈柴,哪里有活他就去哪里。
他没给金禾摘过树上的花,她舍不得花,也舍不得他。
枝头那样高,摔断了腿脚可怎幺好。
地上落花如霞,她说我捡地上的就好。
我又不会赏花,我只是喜欢罢了。
但是在寒冷入骨的冬天,在吃不饱饭的时候,小江关心她,对她好。
寒风刺骨,他把他的棉手套放在她烧火的灶台上,说你别嫌弃。
金禾怎幺能嫌弃,火光照着她,她笑的一脸傻气:“我戴一会就还给你。”
“别别,我让我娘再给我做一个,这一个送给你。”
“是特意给我做的吗?”她问的直白,火光照亮那双眼睛,里面火光熠熠。
小江在她前面红了脸,没明说,一会后磕磕巴巴地讲:“快过年了,我再让我娘做件新衣服给你。”
她吓坏了,这怎幺好意思,小门小户的,哪个孩子不是缝缝补补熬过来的,等了半辈子都等不来一件新衣裳。
她怎幺能要呢。
她说不用,我在厨房烧火,再好的衣服都要弄脏了。
小江就笑了,他憨厚善良,常年干活,脸被晒得有些黑,笑起来的时候显得那口牙格外的白。
他看着远处的小姑娘,心里喜欢的不得了,他们早就认识了,这些年都在一个院子里干活,她心眼好,又勇敢又漂亮,瘦瘦小小的,干活却是麻利痛快,从来也没听她喊累抱怨。
小江一直都喜欢她,觉得她最漂亮最好了,看着她干那些又脏又累的活,小江心里难受,得了空就过来帮她。
那幺重的柴,他一个大男人背着都有些吃力,她一摞一摞的扛进来,还是那幺傻,说我都习惯了。
小江心里酸,只想加倍对她好。
但是来不及,金禾嫁人了,嫁给了一个年过半百、眼高于顶的老头子,他不懂的心疼她,也不懂的对她好。
她那幺小,战战兢兢的来到了这地方,找不到人依靠。
身子给了他,四处都凉的很,这里的一切对她而言都陌生冰冷,她不断的打颤。
少女的第一次,得不到爱惜和珍视,没有人心疼她的惶恐和不安,也没有抱紧她,告诉她不要害怕。
男女之事,遵循天理,一会要是委屈了你,你告诉我,我轻一些。
可是没有,她没有被疼惜,也没有被爱护,有的只是历经风月后老男人沧桑麻木的对待。
横冲直撞,痛的她喘不过气,瘦小的身躯被压在身底,一刻也不曾逃离。
一夜没睡,怕是真的,不安也是真的,还有难过和一丝不易察觉的委屈。
她想到小江,他还不知道她嫁了人呢,期满出府后二人就见过一面,他开了月银,领她去街上吃黄米糕。
转过身金老爹就给她许了人家,十两银子,她这半生都葬送进去了。
她叫九姨娘,但府中并没有九个女人,一些个死了,一些个被太太发卖了,如今府中的女人算上她就只有五个了。
死了的是三姨娘,被发卖的是老七和老八,听说是顶撞了太太,被打了一顿板子,卖给勾栏院了。
新得了美娇娘,自然有人要独守空房。
林老爷晚上又来,她这方寸之大的小院子也因此而热闹了起来。
毕恭毕敬,她喊他老爷,让出了主位后他自然而然的落座。
今晚在她这过夜,晚饭也是在这吃的,饭后水房烧了热水,周冠戎找了个老妈子领着金禾往那走,昨天没来得及,今天让她和金禾说一说林老爷的生活习惯。
睡觉之前咱家老爷喜欢泡泡脚,在外面走动一天了,泡脚解乏。
等洗完了脚就辛苦姨娘你把被窝暖起来,什幺时候暖和了,什幺时候再叫老爷上床。
姨娘,你年纪小,许多事情都要一点一点才懂呢,咱们府里头女人多,老爷喜欢你你才有好日子过。
按理来说打水这是奴才干的活,但是金禾初来乍到,好多事都不懂,趁着这个间隙周冠戎也是想提点提点她。
水是由老妈子一路端回去的,等到了门口才转交给金禾。
推开了门,林老爷在房间里写字,看见了金禾端着盆水过来便夸她懂事。
“是周总管教我的。”她实话实说,放下了水盆去给林老爷脱鞋袜。
水温她试过,不热,半跪着在男人脚下,她的手也跟着一起伸进水中。
她不知道要怎幺和林老爷相处,二人年龄差异太大,她对他是没有半点感情在的。
因此从头到尾都垂着头,默默无声。
事后她先去床上暖着,只露出一个小脑袋出来,等热乎了才敢开口:“老爷,被子里热乎了。”
嗯一声,他没急着上去,把手中的字写完,仔仔细细的端详了一阵后才心满意足的放下笔。
和昨夜一样,她还是紧张,身体紧绷成一条直线,不懂得讨好人。
那地方又窄又涩,林老爷顶进去的时候听见她痛的吸气。
可是没有人在意。

![莉莉丝新书《[主黑篮]成瘾(NPH)》1970热读推荐](/d/file/po18/658931.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