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是后悔,为什么给林婉弄吃的的时候忘了给自己也整一点。
早上九点我吃完之后就奔出了门,先是在菜市场鏖战了良久,回来后又一直给林婉按摩,现在还在路上堵了整整八十分钟;这期间我连一口水都没喝。
到了下车的时候,我已经眼冒金星了。江心楼巨大的发光牌匾里,仿佛飞出了无数的光晕,把我晃得眼花缭乱。
“你没事吧?”我们父母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前面,我则萎靡不振地跟着。林婉凑到我耳边,小声问道。
“没事,赶紧吃点东西就好了。”我晕晕乎乎地道,“老妹你怎么在发光?”
她叹了口气,飞快地向周围看了两眼,然后迅速闪到林毅背后,借着他身形的掩护挡住前方饭店门口的迎宾员,亲了我一口。
她的舌头迅速撬开了我的嘴——或者是我主动把它吸进来的,送进来一小点唾液。
这还是一如既往地有效,我在十几秒后就支棱了起来(指的是精神上),虽然这样反而让我更清晰地感到饥饿。
“谢了。”
“我就是怕你晕倒在人家饭店里不好看。”她脸颊泛红,偏过头去,用下午和我赌气的语气说。
“我知道,我知道。”我笑道。
我不知道林毅是怎么有心情来江心楼吃年夜饭的。
这地方看着就很费钱。
原本它这里只有一面临江;但也许是为了凑“江心楼”这个名字,居然还从另一侧专门挖了条水渠,把整个场地变成了一座江心洲一样的东西。
整个江心洲,除了正中间的饭店大楼外,都是一副非常精致的古典园林样式。
显然,我们匆匆地来这儿吃个饭,根本没工夫去那面积可观的园林里逛一步,但仍然要为这些东西付出额外的开销。
我们走进雕梁画栋、装饰奢侈而又浮夸的大楼,服务生凑上前来问询,林毅很是随意地报了姓名电话,就好像他常来这种地方一样。
不过让我吃惊的是,他居然订的还是个档次看起来不低的包间;我们家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
不过我也懒得多纠结这种事,只是浑浑噩噩地跟在他后面,一边用余光偷瞟着美艳不可方物的林婉,一边暗自回味她刚才局促的那个吻。
我们从设计别致的景观电梯里上了楼,电梯被一个大水族箱半包围着,里面至少有四五种连江口市动物园都没有的奇形怪状的生物。
“那个是什么?”林婉兴致不错;毕竟她吃饱了。她指着一个怪模怪样的、肯定不是鱼的东西,问我。
“我不知道。”
“别指指点点的,让别人看见,像没见识的土包子一样。”
“只有真正没见识的土包子才会害怕别人看出来。”我立刻怼了回去。
林毅没再说话,可能是因为电梯门马上开了,早就在这一层恭候我们的服务员笑容可掬,热情地打起了招呼。
林毅立刻调整了表情,露出一种舒张的、高高在上的淡漠礼貌来。他挽着我们母亲的胳膊,很是慈爱地回过头来招呼起我和林婉。
我俩不死不活地跟在后面,七拐八弯,绕了鬼知道多远的路,才终于进了包厢。
这倒霉地方不知抽什么风,竟不肯把包间放到个离电梯进的地方。
我们一路上见了许多跟吃饭没有关联的东西——带着青铜雕塑的鲤鱼池和喷泉、姹紫嫣红的花坛、摆满书画瓷器的展柜、攀着什么花草藤(实在是认不出种类)的长廊,甚至还有一条人工河、上面的石拱桥还差点滑倒人——后,才在十万八千里之外找到了目的地。
进包厢后,我对这家饭店的怨气已经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当然前无古人未必后无来者,他们立刻就刷新了我的认识。
“请问,现在可以点菜了吗?”就座后,我们父母都没有提及点菜的是,我还在为刚才走的冤枉路暗暗生气。
林婉看了一圈,发现我们都没反应,便跟还在扯有的没的的服务员问道。
“啊,是这样的,小姐,咱们这里的年夜饭都是整套的。”服务员还是带着热情洋溢的职业笑容。
“您家点的是5888元的江景四人餐,需要我给你介绍一下套餐内容吗?”
“啊,那不用了,谢谢。”林婉讪讪道。
鬼知道这江心楼是什么没有自知之明的臭鱼烂虾,什么破四人餐还要花六千块钱来吃。
这鸟地方连点个菜都不让,真是烂到了极点。
待会儿上来的菜肯定不合林婉口味,她还没法自己点。
为了吃顿这破饭浪费一晚上时间,真是见了鬼。
唯一往好处想的一点就是,她有一晚上时间不用做题,可以放松放松了。
江心楼虽然什么都烂,但还是有个好处的,就是上菜比较快。在我要饿死的前一分钟,他们及时地送上了几样菜。
我开始狼吞虎咽起来,连林毅冠冕堂皇、假大空套的餐前演说都没听进去。
他可能很想发一顿脾气,但服务员离我们并不远,他也没脸造次;包间外面还专门有一人候着,随叫随到,也许这就是金钱的力量吧。
趁此良机,我开始大吃特吃起来;至少比林婉放开得多。
就,从技术上讲,盛放这些食物的餐盘太过珠光宝气,反倒显得喧宾夺主了。
林婉又一直不适应在家外面的各种场合吃东西,即便江心楼的厨艺确实过得去(比我自己做得好一万倍),她还是吃得很是不尽兴。
我先往肚子里塞了些高热量的东西,免得饿死在新年前夜,然后就开始给她挑一些她相对喜欢吃的。
糖醋排骨和狮子头林婉肯定是不吃的,不过她倒是吃了两口宝塔红烧肉;她上午用脑过度,我感觉她吃了后精神好了一些。
不过红烧肉她也只是浅尝辄止。我给她夹了几块鲈鱼,自己匆匆应付了几口,开始给她剥起虾来。
“你自己没长手?”我刚剥了五六只,林毅就发难起来。
“我跟你说了她今天不舒服!”林婉刚想说什么或者做什么,我便恼火地顶了回去。
他难得地没有追究,只是耸了耸肩。掏出打火机和烟盒,走出了包间。
既然他不在,我便更放心大胆地剥了起来。那一盘子虾基本上一半都被我剥进了林婉的碗里。
“你俩马上成年,还是注意一点,不要太亲密了。”我们母亲看着我和林婉,淡淡地说了一句。
“她今天真的不舒服。”我语气还是很不友好。
他们两个都知道这件事,但却没有一个人哪怕问林婉一句她怎么样。
好像我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的东西不过是小屁孩的夸大其词一样。
当然,给林婉剥虾……只是这件事本身也很让我心动;要是时间能永远静止在这一刻也不错。
所以归根到底,我也是有些心虚的。
不过越是这种时候,就越不能畏畏缩缩,越要表现得自己坦坦荡荡、丝毫没有做贼心虚。
林毅很快抽完了一根烟,回到了包间。服务员看他回来,便继续上起了菜;从这一点来看,江心楼的服务还真是不错。
最大——或者说最贵的——的一道菜很快上来。
那是一只足足有十斤重的皇帝蟹;我以往只在吃播上看过这玩意儿。
看到这样一道硬菜,我对这份5888套餐的不满才缓解一些;但这依然不能打消我心中的怀疑。
林毅对这道大菜也不怎么在意。
他只是心不在焉地掰了半个螃蟹钳子(谁知道这玩意儿叫什么名字?蟹鳌?),吃了点其他东西,就又出去抽烟了。
我猜是他在航班上憋了大半天的缘故;不过既然他没有打扰到林婉,那也就无所谓了。
“来尝尝这个大螃蟹。”我把另外一只钳子掰了下来,这螃蟹上头好像还有刺,不轻不重地扎了我一下;所以我更不敢让林婉自己操作了。
“你也先吃点儿吧,我还有这么多呢。”她先是看了一眼我空无一物的盘子和无比狼藉的双手,然后垂眼看了下自己堆满虾仁的餐盘,说道。
“一次性给你弄完,我就能洗了手放心吃了。”
她轻轻应了一声,用一只手撑着下巴,静静地看我和大螃蟹最张牙舞爪的一部分躯体搏斗起来。
林婉只需要用筷子加起我帮她处理好的各种东西就成,因此身上很是干净爽利。
她慵懒放松地把脑袋搁在手上,脸蛋秀气的曲线、无暇的色泽与同样完美的玉臂秀手一起,被垂下的乌黑长发衬在后面,真是美得不可方物。
林毅再次抽完烟回来了,他幽幽地看着我和林婉,但没再说什么话。
过了一会儿,他又品尝了几样新菜式,然后再次不紧不慢地溜了出去;今天他的烟瘾可真大。
我总算是给林婉处理完了。她盘子里的东西绝对够她吃撑 ,我便去洗了个手 ,准备开动(真是饿死我了)。
但是,当我刚刚坐回座位上时,林毅就再一次回来。
他满面春风,身后跟了一个同样西装革履的中年男人。
我有种不详的预感:可能我要没工夫吃东西了。
“锦,给你介绍一下。”他热情地说道,向后退了半步,把身旁的男人凸显出来。
“这位便是我和你提过的、东流集团的聂副总。聂总,这是贱内,云锦。”
“哎呀!”我们母亲惊叹道:“聂总这么年轻的吗?聂总,您这是三十几啊?”
“云嫂您可别埋汰我了,我都四十五了。”
“那可真是看不出来。四十五就当了东流的副总,聂总您可不简单啊。”
“那是自然,聂总人家当真是年轻有为。”
“嗨,林兄可别这么说。林兄云嫂的大名,我们也是如雷贯耳的。我们梅总经常抱怨说,东流就缺您两位这样的得力干将呢。”
“聂总说笑了。这话要是别人说,咱便厚脸皮认了;聂总您这么说,可不是臊我俩吗?”
“哎呦,您可别谦虚。林兄,今个儿大年三十,咱们只论年齿,不提什么狗屁职务。”
“聂总果然爽利。”我们母亲赞道,“不过聂总,我跟你讲,我家老林就是这么个性子。平时看着不好处,一旦真服气了你,那就是真的心服口服。他一向对你佩服得紧,要让他管你叫声老弟,他自己怕都要不好意思咯!”
“林兄这是真性情。”那个一看不像三十几岁的聂总笑了笑,如果不是林毅凶狠的目光看向我这边,我一定先把那颗狮子头咽下去(这地方的狮子头真是神中神,待会儿得好好研究下它浇的汁儿):“那咱各论各的,云嫂,您可千万别像他那么见外,几句话说得我都不好意思喽。”
“咱不管他。话说聂总也是正好在这儿订了年夜饭?”
“是啊,其实也就是孩子想在外面吃,我和内人都不是会做饭的。要是光我俩,就在家里对付一顿得了,江心楼这地方好是好,就是实在太贵。”
“嗨,这也没办法。我们也是,要不是今年孩子高考,想着带他们吃顿好的,也就将就一下得了。”
“呦,您家孩子倒该高考了呀?”那人不识趣地看了过来,我正中规中矩地夹起一片薄如蝉翼的酱牛肉,在林毅的逼视下用极其端正的姿势送入口中。
林婉则埋头吃着我给她剥的虾仁;不过她也不需要像我一样调整什么仪容仪表。
她简直就是实体化的“美”这个概念本身。
“唉,正发愁呢。”林毅很是沧桑地叹了口气,脸上的表情极为丰富,望子成龙的期冀和对孩子辛劳的担忧混杂在一起,融合成慈父浓浓的关切。
“聂总您家孩子多大了?”
“刚高一,也不省心。”果然,孩子对于父母来说,就像是八卦对于学生一样,是绝对占据优势的话题。
“您家孩子在哪儿上呢,我记得好像是三中?”
“勉强进了三中。”林毅一副马马虎虎吧的表情。
“唉,那可厉害得很呢。”那人赞叹道。
“说起来林兄别笑话,我家孩儿初中是三中的,后来嫌三中累得厉害,高中去了外国语,打算走个外语保送,轻松一点。”
“三中那确实不是人待的。”林毅沉重地摇摇头:“熬上三年出来,人都毁了。”
“是,不过也不能太不努力了。我家那是实在不用功,每天愁死个人。”
“聂总也别发愁。您的孩子,那能差了吗?”
“她自己不努力也没用啊。倒是,我家孩儿聪明是聪明,就是不爱用功。你说这年头,不用功那就没用啊,龟兔赛跑也不能一直睡觉不是?我看她现在连保送都悬。”
要不是我还想偷摸吃两口肉,指定要嘿嘿嘿冷笑一番。
所有家长都沉浸在自己孩子“聪明是聪明,就是不爱用功”的幻觉中,一边拿这个借口自我安慰,一边幻想其他孩子都是靠死读书才能考好的。
正儿八经聪明但不爱用功的人我也不是没见过,上午还叫我去菜市场少买点东西、早点回来学习呢。
“才高一,也不敢把孩子逼得太紧了。聂总我跟您讲,有的人是高一死读书、考得好,到了高三,他后劲就没了,跟不上了。那弦绷三年,它能不断么?”
“话是这么说,不过保送的话……”那人叹了口气,没有接茬,“林兄,咱可是听说您家俩孩子优秀得很,能不能让他俩给我家孩儿说道说道?”
“那自然是没问题。”林毅点起头来。“你俩,去跟聂叔叔去他那边,跟小妹妹好好聊聊。”
“林铮还什么都没吃!”林婉扔下筷子,怒道。
当然,这话说得不精确;我其实已经吃了三分之一个狮子头、两片酱牛肉、一筷子蕨根粉、一片油菜、半只虾和不到五立方厘米的红烧肉,甚至还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饺子。
“回来再吃吧,我和你妈给他留着。”
“哎哎哎可别,林兄。”那人劝道,“这哪有让她俩过去的道理?我这就去把我家孩儿叫过来。孩子,你先吃着。”
“他们这是高三了,脾气也大,让聂总见笑了……”
林毅和那位聂总继续谈笑着,走出了房间。林婉把她的盘子向我这边一推,催促道:“赶紧吃。”
“你不该在外人面前顶撞你爸。”我们母亲又恢复了冷淡的语气,说道。林婉没有接话,只是用眼神催促着我。
事到如今,其实我已经完全没有食欲了;也许也是因为我的胃饿到麻木了。
但林婉的目光是那么热切,简直就是在灼烧着我一样,我只好夸张地大快朵颐起来。
那两人等了几分钟才回来,林毅满脸笑容,姓聂的也带这种如释重负的欣喜,他们后面则跟着一个表情很不愉快、看上去就不好惹的女生;我真心希望这位集美是闹了半天脾气,好为我争取时间吃了个半饱。
不过这位集美一进来,看到我和林婉,脸色便好了一些。
“你正好跟哥哥姐姐请教一下,人家都是三中的尖子生。”
“我知道了。”那小孩儿很不耐烦地道,完全不符合林毅希望我和林婉成为的、在父母面前唯唯诺诺说一不二的样子。
“我们出去说吧,我不想在这里。”
“你看哥哥姐姐同意就行。”
林婉冷着脸,我猜她马上就要再爆发了,赶忙把她拽住。
“我吃好了,吃好了。”她这才面色稍霁。
“你吃好了没?”林毅也出言问——或者说催促——道。
“吃好了,走吧。”我很简短地说道,然后站起身来。
我和林婉就像两个大傻逼,跟在高一小屁孩儿后面出了房门。在我踏出门口的时候,隐约听到后面三人已经开始聊起了什么业务上的情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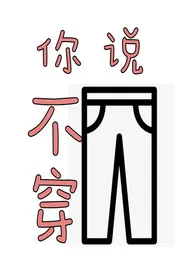

![《[全息]任务从偷欢开始(np)》小说全文免费 一晌贪欢创作](/d/file/po18/797613.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