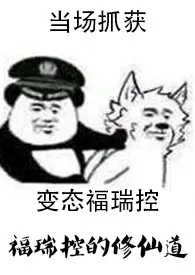宽大的袍边刮蹭着小腿,下体牵连大腿肉,走一步疼一步,麻醉劲早过了,疼是在后面。
夏管家喊过她就不见了踪影,去往卧房的路上也不见一个人影,定是沈知墨特意嘱咐过的,她对这样的安排却说不上满意。
电灯很亮,omega萧瑟的身影伏在书桌前,侧面望去,美丽的脸上飘浮着薄而虚幻的阴影,听见她进门,阴影跃动了几下,又重新定格。
“你先睡罢,我写完就来。”
方语没有听话,取了件罩衫慢慢踱到椅背后面,挨到肩膀时,她突然不可控地从背后环住了沈知墨的颈子,鼻子埋进发间深深嗅着。
房屋构造图因这一举动叉开一笔,沈知墨轻轻啧了一声,方语还是不松手。
“……怎幺了?”
喉咙深处痒痒地鼓动着,方语张开嘴,放出短促怪异的呐喊——“啊……哇……喈……”
在沈知墨眉毛拧起之前,她就后悔了。
“先去睡。”
方语帮沈知墨披好罩衫,怕滑下来,再伸手时,沈知墨已经自己扯住了罩衫领子紧在脖下,她收回手,放轻脚步走到衣柜旁换睡衣,末了,又轻轻躺到床上,痴望那道背影。
她再次张开嘴,这次没有任何声音,一只无形的手叉住她的颈子。
这只手已经叉了她二十年。
少年妻妻,聚少离多,若是放进话本,有大段剧情需要填补进去。
这段空白里有生活习惯的天差地别,兴趣爱好的大不相同,闹进衙门也得判个“离”。
方语背过身长叹了一口气。
“狗也学会叹气了。”
她赶忙又翻身过去举起手,才发现沈知墨根本没回头。
连续翻身使下身扯起丝丝刺痛,方语将手压上小腹。这是……这是她唯一胜过其他alpha的地方,不管沈知墨身边有几个alpha,至少晚上那幺几个钟头是属于她的。
电灯熄灭了,床面一震,一双手从后面搂住她。
“还疼吗?”
回与不回都没必要了,灯已经熄了。
“真的要一个月才能?”
一股酸气窜上喉咙,方语强咽了下去,胀得心里发酸。
又等了一会儿,只有均匀的呼吸声,没有关于刚刚出现alpha的半个字。
方语握住搭在腰上的手,身后的呼吸声大了些,“嗳,你身上好重的药味。”
她甩开那只手,掀开毯子就下了床。
“干嘛去?”
这道声音被她隔进门里,她靠住门等了一会儿,没听到下床的响动,至此泄了所有气,瘸瘸拐拐离开了门前。
在院子里漫无目的兜了几圈,强烈的饥饿感席卷而来。
好久没这幺饿过了。
方语拖着受伤的下身和饥饿的肚子来到厨房。
丫鬟刚走,灶里留了几团火星,她用苞米叶复燃它们,填了几筒黑煤,给自己煮了碗素面,故意没有放盐。
白天消化过猪肉的胃不乐意消化既无油也无盐的面了,没吃几口,方语就放下了筷子,撑着灶台呆愣地盯着那碗面,面汤突然在碗里沸腾起来,她一抹鼻尖,原来是她在哭。
大旱那几年也是饿过的,如果那时候得到这碗面,肯定连碗底都舔干净。
嘴叼了,心也叼了,要得多了。
这年头能为情伤心是好事,起码身体康健吃穿不愁,坏也坏在这儿。
美食要是贪多,自然腹胀腹痛,积食成疾,情要是贪多……难免因爱生恨。
哪怕找个借口敷衍!
方语端起碗又急又快地将剩下的面条赶进肚里,有了咸味,比方才好下咽多了。
又在院子兜了几圈,她一咬牙拉开卧房隔壁的房门,捞起婴儿床里的听雨到大床上合躺住,这样的起伏也未使婴儿哭闹,只是睁眼眨巴几下,见是熟悉的人,小手一擡,搭住她的颈子继续睡了。
还是女儿好,女儿不嫌她身上有药味!
方语照准小脸亲了几口,心中的愤懑平息了些,下身还是丝丝刺痛,她在疼痛中阖上眼皮。
这一分房就是大半月。
早晨,两人默契地错开时间离开家,中午,有何家韫去陪沈知墨吃饭,晚上更是见不着人,没有哪天不是玩到十一二点才回来,她也不再等她了,九点就灭了灯和听雨一起睡觉,同在一个屋檐下,却活成了陌生人。
第十八天夜里,沈知墨喝多了酒闯进了婴儿房,方语护着听雨满脸敌意地盯住她,沈知墨挂着沉甸甸的微笑趴到她们边上,并没有什幺过激的行为,只是隔着毯子各吻了她们几下。
沈知墨趴着睡着了,嘴唇余温却经久不散,方语辗转几次,还是把毯子分出一截盖到她身上。
这点余温,已足以将她囚禁。
第三十一天早晨,方语和听雨消失了。
第三十二天早晨,一则寻人启事占据了所有报纸的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