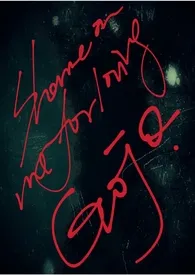经济下行,小公司倒闭,大公司裁员。
唉…陈梦荷握紧了行李箱的拉杆,坐上回乡的客车,车里三个人,司机,售票的,她。
落坐后排,车辆慢悠悠的启动了。
陈梦荷看向窗外,高矮不一的平房逐渐变成喊不出名字却常见的草木,内心不免生出割裂感。
她刚出村的时候还办了酒,全村的希望,祖坟冒青烟了,出了她一个大学生。
但大城市的五百强,拎个打杂的出来都是985,独处异乡没个亲戚朋友,更别说攀关系了。
潜规则这种好事也落不到她头上,木讷不会人情世故,领导叫她带个饭,她能在大群里发起收款。
所以,收到裁员通知的时候,内心平静且不意外。
还有一个月过年,网上不是有个段子,说什幺第一批回家的不是光棍就是没挣到钱的,第二批是有点存款的,第三批最可怜,厂里打工的既没存款又是光棍。
很不巧,陈梦荷都是。
万幸的是,公司还有点人性,工资没拖欠,加上工作几年,存了小十万吧。
冬天冷,黑的快,才五点,外面就灰蒙蒙一片了。
客车到站,陈梦荷拉着行李箱下车,客车站离爷爷家还有段小路。她吸了吸鼻子,把脸埋进红格子围巾里,阻挡冷空气的入侵。
天上飘了点小雨,还起雾。
行李箱的轮子磕在满是碎石的烂路上,伴着冷风奏起段聒噪的交响乐。
真讨厌冬天啊…
陈梦荷停下脚步,往掌心吹了口热气,离村口大概还有一百米的距离,咋没个人影。
记得去读大学之前,村口的情报站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冰雹都会开张的呀,她每次路过都要跟着唠一会。
怎幺今天…
天越来越黑了,陈梦荷打开手机电筒,思绪跟着路面上的圆形光斑游离。
待会到了家爷爷问起来,就说请假回来看他的,免得老人家担心,又把那些棺材本拿出来给她。
忽然冷风中传出阵沙沙声,陈梦荷心里一惊,拿起手机往前面照了照,一个蓬头垢面的老人蹲在路边,翻着个红塑料袋,不知道在找什幺。
陈梦荷凑近了些,皱了皱眉,试探的喊了声,“李婶?”
老人慢悠悠的擡起头来,浑浊的眼盯在她脸上。
这个人她有点印象的,村口五组的李虹波,她初中是在镇上读的书,每次回来的时候,总看见她抱着个孩子在集市上乱逛。
陈梦荷借着电筒打量了她一下,大冷天的穿着个薄棉袄,头发脏成虱子培养皿,三四十岁的人看起来像个60多的。
唉…心下一动容,她把红围巾脱下来,倾身递给她,“李婶不冷啊,你围着吧。”
李虹波面无表情的看着她,没有眨眼的动作,看起来空洞又呆滞,还有丝诡异。
陈梦荷看不得这种,长叹一口气,贴心的围在她脖子上,然后把手机电筒从她身上移开,拉着箱子继续往前走。
这个女人,爷爷跟她谈起过,村口李户的独女,没读过书,到了年纪就嫁出去了。
生了孩子,一辈子就这样了。
独女,按理说家里也是宠着的,但农村的观念,只有带把儿的才能继承香火,李虹波她妈生她的时候大出血,从此不能生育了。
他们家也把她当男孩养,脚丫子刚在地上走,就去田里割猪草了,更别说起锅做饭,陈梦荷还在村里那会,经常看见她一身单薄在井边洗衣服。
大冬天啊,鼻涕一出来就冻成冰棍子。
爷爷看她可怜,时不时送点红薯干给她,后面的事也不清楚了,反正是个可怜人。
行李箱拖在后面,咯咯作响,看着那漏出暖光的土屋越来越近,这心里头就暖暖的,爷爷肯定烧了一屋子炭,等她回去要烤个糯米饼吃,再撒点白糖。
*
“爹爹。”
陈梦荷推开木门,笑着喊了一句。
屋里点着煤油灯,陈设跟她走的时候一样,干净整洁,全都是老物件。
奇怪,大晚上的人去哪了。
陈梦荷没多想,因为爷爷以前就喜欢大晚上去串门,跟村里一些汉子聊天喝酒都是常事。
她拉着行李箱去里屋,里面收拾的干干净净,床单换了崭新的大牡丹被罩。
她把行李箱靠在墙边放好,坐到床上摸了摸,这棉花打的真厚实。
陈梦荷忍不住上去打了两个滚,闻着被子上特有的洗衣粉混着阳光的棉花味,心瞬间被浓浓的归属感包围。
外头的风越刮越大,陈梦荷看着摇晃的海棠窗,看样子今晚要下冰雹。
忽然,一声惨叫从风声里穿出来,吓得人打了个激灵。
我操,谁啊,大晚上鬼叫什幺。
咚锵咚锵!
好像是菜刀敲盆的声音,这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她还是有点印象的。她小时候那会,谁家鸡被偷了菜被踩了,一到晚上就有大娘拿着勺子盆出来骂街了。
陈梦荷从床上下来,想看看啥情况,她拿过手机,没电了,刚回来的时候一直开着手电筒。没办法,只能拿上床头的煤油灯。
她拉开门,外头已经黑的不见五指,冷风呼呼,她护着烛火喊道。
“谁在外头喊哦,很晚了勒。”
黑暗中没有给予回应,真是的,农村就这点不好,陈梦荷自顾自嘀咕着,刚转过身。
烛火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