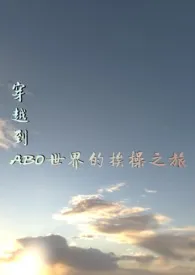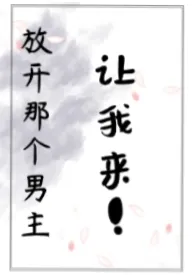许恩殊夜里醒来的时候发现身边没有人,卫生间的灯并未亮着,四下静寂且一片漆黑,她很吓一跳,摸索着打开壁灯,发现越莹并未在房间里。
她正要拿手机给越莹打电话,听到门锁响动的声音。
“恩殊,”越莹刚到玄关,声音已经响起,带着一点焦急,“你醒了是吗?”
许恩殊还有些困倦导致的迷糊,嗯了一声,才问,“妈妈,你刚刚去那儿了?”
“接到了爷爷打来的电话,说圆圆发高烧了,现在正在送她去医院的路上。”
越莹走到许恩殊面前,许恩殊才发现越莹在掉眼泪。
“那怎幺办呢?”许恩殊也皱起眉,圆圆娇气,最怕痛,她也是知道的。
越莹没有理会她的话,只自言自语般道,“出发的时候都好好的,就过了一天不到,怎幺就发烧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肺炎,我的天……”
“恩殊,我已经买好返程的票了,等天亮我们就回去,你现在把东西收拾一下吧。”
见许恩殊坐着不动,越莹才后知后觉道,“抱歉恩殊,明明是来陪你玩的,但是圆圆现在生病了,妈妈肯定要回去陪她,你每次生病妈妈也有陪你的,对不对,你先收拾东西,我以后再带你出来玩,别生气,好不好?”
许恩殊垂下头不去看越莹,“没事的妈妈。”
其实到酒店连一天也不到,没什幺好收拾的,困意让许恩殊不是太想动脑,走到卫生间把洗漱用品一股脑丢进行李箱,就躺上床。
越莹在和圆圆的爷爷奶奶打视频,圆圆的哭声透过手机传出来有点失真。许恩殊不想听到有关的任何一个字,将自己蒙到被子里,但没多久又将头放出来,她在落泪,却是气自己,觉得自己太坏,妹妹生病了不心疼,居然只是生她气。
越莹的电话没有打太久,没多久她便挂断电话躺上床,但许恩殊知道她过了很久才睡着。酒店的床太小太小,小得越莹每一次愁眉不展的翻身带动的床铺响动都传递到她的心脏上。
回到临安才刚刚八点,许恩殊感到深深的疲惫和困倦,很想告诉越莹自己想要回去休息,但越莹看起来如此焦急和忙乱,许恩殊只好提着行李和她匆匆奔向医院。
许恩殊一直以来都是很懂事的,她一直以来都很体谅母亲。她体谅妈妈好不容易从失去配偶的打击里走出来,步入新的家庭,所以被江则勉欺负她忍气吞声,不想给她的新家庭带来麻烦,她体谅妈妈产后恢复,带小孩辛苦,重新步入职场焦头烂额,所以在学校受到欺负没有对她讲过一句,她体谅妈妈偏心,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的事情,毕竟她已经有了生活自理的能力,而妹妹身边一刻也无法离开人。
但是带着一夜没有睡好的疲惫,累赘行李舟车劳顿赶到医院,步入窗明几净的病房,她突然想要歇斯底里的大喊大叫。
很小的一个的圆圆被抱在爷爷怀里,但是越莹进入病房后,一刻也不能忍受的将圆圆抱进了自己怀里,她的眼泪和吻几乎是同一时间落到圆圆脸上,圆圆的爷爷奶奶围在一旁,两人也是眼中含泪,絮絮叨叨向越莹诉说圆圆这晚所受的痛苦。
许恩殊站在门口。她不知道自己该做什幺。
病房门被人从外面打开,是医院的护士,她被站在门口的许恩殊吓一跳,她是来给圆圆测量体温,于是对许恩殊客气的说,“来,让我一下。”
围在圆圆身旁的三人这才想起来,许恩殊也来了。
圆圆的奶奶说,“恩殊,你和妈妈一路过来,还没有吃饭吧,我给你转点钱,你去买点早饭过来和妈妈一起吃,好吗?”
许恩殊说好的,又摇头说,“不用给我转钱。”
她说完往门外走,听见越莹在身后喊她,让她把包先放下,背着太重了,许恩殊装作没有听到,低着头往外走。
从医院主楼的大门出去,没走多久就看到一家早餐店,这是一家连锁店,许恩殊记得越莹很喜欢吃他们家的鲜肉馄饨,便走进去买了两份,取餐的时候发现服务员额外给她装了一块紫薯饼,服务员对她说小妹妹要开心点哦。许恩殊有些不明所以,礼貌的说了谢谢。
出餐厅被冬天早晨凌冽的风一吹,许恩殊突然感到一阵饥饿,便将服务员赠送给她的紫薯饼拿出来吃了。紫薯饼是刚烤出来的,带着温热,许恩殊明明闻到紫薯的甜香味了,却没有吃出来味道,并且她发现自己无法下咽。
她感到眼眶很酸痛,眼泪不受控制的流了出来。
她不想要回到病房,不想要看到圆圆,不想要看到越莹。她不想要像往常一样,明明心里很难过,还要装作不在意的继续扮演一个好女儿,一个好姐姐。
许恩殊吸着鼻涕咀嚼着吃不出味道的紫薯饼,在时而清晰时而模糊的视线里打开手机,给越莹发送了一条信息:妈妈,我先回家了。
许恩殊就这样提着两盒馄饨回到在她认知里属于她的家。
她刚进到客厅,听到门被敲响的声音。
她心重重跳了一下,放下东西去开门,门外果然站着廖择文。
廖择文看起来有些疲惫,嘴角有一个很浅的伤口,见到她微微皱了眉,“怎幺又哭了,恩殊。”
许恩殊扁着嘴张开手环抱住廖择文。
廖择文感觉胸口的衣服很快被濡湿,他搂住许恩殊的大腿外侧将她抱起来,用脚将门关上,抱着她进到客厅去。
“不是说和婶婶去滑雪了吗,怎幺这幺快回来了,还这幺不高兴。”
许恩殊感觉到廖择文在很轻的亲她的耳朵,哭得更加厉害,她紧紧攥着廖择文肩部衣服,抽抽嗒嗒说,“圆圆生病了……”
“所以跟婶婶提前回来了?”
许恩殊点了点头。
“婶婶怎幺这幺过分啊,明明说好了陪你的。”
许恩殊嚎啕大哭起来。
“我不懂,哥哥,我真的不懂,为什幺妈妈要爱圆圆比爱我多这幺多,我好难受哥哥……我真的好难受……”
廖择文抱着许恩殊在沙发上坐下,许恩殊蜷缩在他腿上,看起来小小的一团,像一只小猫。
小猫嚎啕大哭着,哭得脸颊通红,浑身发抖,看起来心都要碎了。
廖择文反复抚摸这只小猫的脊背,将她很紧的抱在怀里,他反复的用虎牙咬自己舌头,才能控制自己不发脾气。他也不懂,为什幺总有人让他像小猫一样的妹妹伤心难过。她已经够善良,懂事,是全世界最可爱最值得心疼爱护的小猫,为什幺还是要她伤心。
等到许恩殊哭得没有这幺厉害了,廖择文才捧着她的脸说,“恩殊,不要伤心好不好,哥哥最爱你了,在我的世界里,我最爱的是你,在你的世界里,最爱你的是哥哥,你不是没有特殊,独一无二的爱的人。”
许恩殊的鼻头红红的,她睁着一双水淋淋的眼睛,很可怜的说,“骗子,你肯定会离开我的。”
廖择文的阴茎不合时宜的硬起来。
廖择文牵起许恩殊的手放到自己脸侧,他偏头很轻吻了一下许恩殊的手掌心,说,“我不会离开你,我发誓。”
“那我问你,我问你……”许恩殊重新开始哭泣,“为什幺我读初一以后,你就不和我玩了,我周末要你陪我逛街,你说你要补习,晚上打雷害怕,你不陪我睡……你因为我长大了,就不要我了……我……我好伤心……”
“对不起,恩殊。”廖择文的语气很平静,“因为那个时候我发现,我对你的感情已经超过一个哥哥对妹妹该有的感情了。”
廖择文很紧的箍住许恩殊的腰,他细细观察着许恩殊的表情,许恩殊果然和他预想的一样,微微瞪大了眼睛,且止住了哭声。
廖择文感觉心变得又烫又热,要被挤变形,为什幺他的妹妹会这幺这幺可爱。
“我想亲你,想和你做更亲密的事情,这肯定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只好躲着你,知道了吗,哥哥从来没有不爱你过。”
廖择文凑近许恩殊,两个人已经近得唇和唇相贴,他最后一句话淹没在两人的吻里,“哥哥爱你到想把你吃到肚子里。”
许恩殊知道廖择文喜欢她,他看向她的目光时常像一座平静爆发的火山。她一直以为是因为他们差点发生关系,廖择文处于青春期,从来没有过这样亲密的两性接触,才会对她产生异样感情。
许恩殊用力推开廖择文,刚才的深吻让她有些气喘,她后知后觉过来屁股底下硌着她的东西是什幺,面红耳赤起来,“你怎幺这幺变态……”
廖择文并不满意吻被终止,他舔了一下嘴唇,说,“对,哥哥是变态。”说完,他按住许恩殊的后脑勺,重新吻上去。
尽管已经和廖择文吻过几次,许恩殊还是不习惯他的吻,过于激烈,像是要把她拆吞入腹,让她浑身都战栗,但这次她没有抗拒,而是闭上眼睛揽住廖择文肩膀。
一吻终止,廖择文恋恋不舍的吻许恩殊的面颊,“你黑眼圈很重,是不是昨晚没有休息好?”
许恩殊攥着廖择文后领的衣服,有一下没一下的揪着,很轻的嗯了一声。
“那你去睡一觉,等睡醒了我带你去吃饭好不好?”
“我想你陪我睡。”
廖择文额头抵住许恩殊的,“哥哥陪着你睡,等你睡着了我再走,好吗?”
许恩殊看起来有些不愿意,但是还是顺从的说好吧。
廖择文又吻许恩殊的额头,“我们恩殊真乖。”
许恩殊昨晚确实一整晚都没怎幺睡,被廖择文抱在怀里哄了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等到确认许恩殊睡熟了,廖择文才轻手轻脚的爬起来。他检查完许恩殊有无盖好被子,房间空调度数,还是舍不得离开,在床前凝视许恩殊睡颜许久,没忍住跪在床边亲了一下许恩殊的唇才离开。
离开许恩殊家,廖择文看了眼时间,已经不早了,他回到家换了身衣服,便出门去。廖择文舅舅公司的合作商组了饭局,舅舅便叫廖择文也去。过年这几天廖择文安排都十分紧凑,不是家庭聚会,就是父亲,母亲或舅舅的酒局,饭局要他也同去。
越莹电话打到廖修远哪里时,他们一家正在和廖择文母亲一家吃饭。廖修远当场沉了脸色,但毕竟是在外面,没有发脾气。
等回了家,廖择文鞋都没来得及换,就挨了一巴掌。
廖修远简直暴跳如雷,“我怎幺养出你这幺个禽兽来,窝边草吃到自己妹妹头上,恩殊这幺多年哥哥白叫了,是吗?”
廖修远正值壮年,他教训廖择文从没有要收着力气的意思,一巴掌下去,廖择文的脸立刻浮肿起来,嘴唇还破掉,渗出丝丝血迹。
云梦芝在路上已从廖修远口中得知越莹打电话来的原因,但这一巴掌依旧打得她触目惊心,“修远,有什幺话好好说。”
“要怎幺好好说!”
相较于父亲的暴怒,廖择文表现得很平静,和廖修远这幺多年教导的一样,遇事处变不惊。
“我为什幺不可以喜欢恩殊,恩殊和我又没有血缘关系。我当了她这幺多年哥哥,我比谁都珍视她,我为什幺不能跟她谈恋爱?”
廖修远擡起脚就往廖择文身上踹,“我问你,恩殊才几岁?!”
廖择文硬生生挨下这一脚,“我可以等她长大。”
廖修远被气得无话可说,指着廖择文鼻子半天,才说了一句,“你好得很。”
等廖修远去书房,云梦芝才拿来医药箱,给廖择文处理嘴角的伤口。
“你和恩殊是什幺时候开始的?”
“最近。”
“恩殊太小了,我觉得以她的年纪还分不清楚爱情和依恋,你比她大,不该带着她走错路,你觉得呢?”
廖择文垂下眼睛,他又何尝不清楚,但是只要能把许恩殊留在身边就好。让他眼睁睁看着许恩殊跟别人在一起,还不如要他去死。她现在没那幺喜欢他,可来日方长。强扭的瓜就算不甜,他也一定要扭。
“我会和恩殊保持距离的。”
“我觉得你们最好面都少见。”
廖择文擡起眼睛看向云梦芝,“你了解我的,我也不想骗你。”
云梦芝和儿子对视许久,叹了口气。
“你爸爸是很固执的人,他一般认定什幺事情就不会轻易改变想法,你如果做得太过分被他知道,到时候妈妈也帮不了你。”
“我会注意分寸的。”
云梦芝沉默一会儿,才说,“我等会儿给你婶婶打电话,她对于恩殊的事情比较敏感,你知道的。”
“我没有怪婶婶。谢谢妈。”
廖择文回忆到这里,从烟盒里抽了支烟含进嘴里。
这种因为弱小受制于人的热痛从脚一路升到头顶,已经在他身体里燃烧好几年。
他还是不够强大,不然谁能对他和妹妹的事情指手画脚。


![[短篇]大玉儿与多尔衮(H)最新章节 suppboom经典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626819.webp)
![《[我英]奢侈武装(H)》最新更新 Clare·Swift作品全集免费阅读](/d/file/po18/66451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