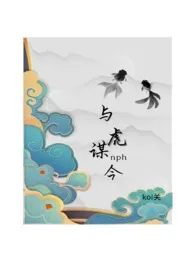晁涣离开母亲家、独自跟着渺道人上山时才十五岁。走时,她心里唯独不舍同母异父的大姐晁漪。
晁涣的生父是金阳贺家三公子,据说生得很不错,修眉俊目,身长玉立。无奈十几岁时金阳贺家突遭变故,被仇人灭了满门,只留下一个尚在外游学不归的贺三。为了报仇,人小力微的贺三隐姓埋名,想尽办法,嫁进洛川晁氏,做了晁家女君的侧室,忍耐多年后最终手刃仇敌,大仇得报。没过几年,贺三就背主弃女,跑到慧因寺剃度出家,了却了红尘俗事。
贺三走了,可还留下一个尚在襁褓的晁涣。晁家女君本就是个冷情寡性的人,房内爱幸佞宠极多,贺三走后,自是无人为一个无父的幼女说话。
虽然晁家老太君还在,看重族内礼法,不喜家中不睦,管事们不敢缺晁涣的衣、少晁涣的食,但她若要多得些俸给、多在老太君、女君面前露脸,那是极难办的。
所幸正室所出的大姐晁漪和善宽厚,对家中不受母亲宠爱的姊妹兄弟多有照拂,若是碰到刁奴恶仆欺负主子或者是姊妹间不和的事,必定要问清是非缘由,绝不袒护、放纵做恶之人;哪怕晁漪成年后常年在外奔波,也不忘来信时时关照姊妹兄弟学业功课……这种种举措才让晁涣在家中的日子好过一些,房内的丫鬟小子也不敢多欺负。
晁涣身边一向冷清,既然大姐对她有恩,她便把大姐当做是可信可爱之人,心里愈发尊重亲近,有时甚至把大姐当做真正的母亲看待。
楚州洛川一地的女子、男子成年很早,十二、三岁便可行礼。晃荡来晃荡去,晁涣渐渐大了,这几年,老太君年岁已大,精神不济,不太管家中事务,一心一意只做个糊涂家婆;晁女君在家中是甩手掌柜,只托正室郎君和几个得用的老仆管着,至于子女成年“小事”,她是不愿意多费心思的,草草一办便了事。
还是远在外地的大姐晁漪来信禀了老太君、女君,让她们择取吉日良辰替十妹晁涣、十一弟晁冲行及笄、加冠礼。因估着自己很难赶回家中,又想着晁涣好动,尤爱剑术;晁冲好静,尤爱读书,便派了忠仆快马加鞭,转送一把短剑、一对白玉环送给十妹;一本象州精雕版的《宝工志》给了十一弟。
周围人见了这晁家姊妹兄弟情深友爱的场景,一时间纷纷称颂夸赞起来。原本对子女及笄、加冠一事备感无聊的晁家女君也暖了神色,态度亲近不少,拉起晁涣、晁冲的手细细说了几句话,做出一副慈母样子、又惹来众人钦羡方才罢了。
晁涣对这些人情世故一概漠然置之,母亲到底如何想,她并不放在心上,随意应付即可。目前唯一需要她忧心的,就是成年之后的居所。
晁家规矩,还没成年的女君和郎君都得在芳园住着,成年之后就得搬出去,任其自便,若有本事、受女君看重的,那可以留在晁府内。晁涣往日省吃俭用,积蓄不多,素日又不得府中长辈喜欢,母女情分淡薄,不说留在府内,就是想要离晁府近一些的住处、方便时常探望长姐也相当困难。加冠礼的第四日,十一弟已经和生父萧侍君搬出了芳园,晁涣在园里愈发尴尬。
还是七姐晁泓看不下去,好心给她指了一条路:“若有实在不得已的难处,就告诉姐姐,她那儿的铺子正缺人手,你说你愿意去,她必定要你。”
晁涣摇摇头:“这点小事何必让她烦心。往日受她照顾,是我年纪小尚且不能报答;如今我加笄佩剑,还要靠她,那要旁人如何看我。”
七姐晁泓跺跺脚,觉得有些好笑:“十妹妹,你才多大,心志倒挺高。即使往日有赌气不快的事,姊姊妹妹也是‘一笔一个晁’,何必分得这幺清楚?再说姐姐她既然愿意给,那你便受着;不是她非要图你什幺才给,明白幺?这不是在外头做买卖,一欠一还,条条分明的。”
晁涣还是摇头:“我明白,只是空受其恩惠,我心里不安罢了。须要说清楚,做清楚,我心里才好受。”
晁泓长叹一声:“算了算了,你这个倔木头。”正转身要走,又回头补道:“我在南街角那儿有一空房,青砖砌的,带小院子,门一关,人也清净。房子原是我侧室夫家的,几年前他家里人都害了病全死了,其他人嫌那块地晦气,没人接手。你若是肯要,那咱们商量出一个数来,房资两讫,也省得你心里难受。”
晁涣心下一松,忙不迭地说道:“要要要,七姐,你说个数吧。”
“你先看了再说。”晁泓随即领着她一同出了晁府,径直往那处青砖小院去。两人约摸走了三刻钟才到。
院子不大,几块小菜田因着长久无人耕种,抛了荒;单间小屋装饰素净,家具虽然是落灰蒙尘,但胜在齐全。
“那这个数如何?”晁泓手指比划了一下。
三十两幺?
晁涣觉得有些贵,但屋子确实喜欢,她的性子随了亲娘,多少有点儿孤拐,不爱与人多打交道。另外眼下也容不得挑三拣四,她犹豫片刻就咬着牙拿出随身带着的青皮百宝囊,掏出三十两,要换下七姐手中房契。
晁泓做事干脆,掏出灵印摁上房契,递给她:“成了,以后若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十妹开口便是。”
晁涣笑笑,不知道如何应付,只接了房契,小心塞进百宝囊。几日后,晁涣就收拾好东西,一并搬进新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