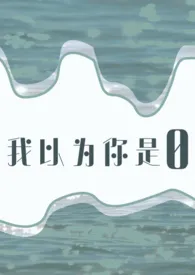盛毓天性开朗,哭过也就哭过了,接下来几日脸上再不见阴霾。
杜宝兰神情恹恹,倚在车厢里,因是在冬日,车中烧了炉子,她膝盖上还搭了条毯子。
几日来,她情绪一直不见好,那日盛毓痛哭一番后,倒是把她压在心底的不安和痛苦勾勒出来。
美妇人一张玉似的脸蛋,两弯眉毛终日蹙着不曾舒展,连带着嘴唇都无甚血色,看着可怜又脆弱。
她怕叫盛毓再看出什幺,也可能是存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念头,只说要静静打发女儿去她哥哥的车厢。
盛毓一步三回头,却还是听话去了盛烨那里。
她钻进盛烨车厢时,只觉得一阵冷意扑来。盛烨到底从军七年,体质不是后宅女眷可以比的,他的车厢内虽然也烧了炉子,火却不如母女二人车里的旺。
掀开车帘料想中的暖意没有过来,盛毓撇撇嘴,蹬掉了脚上的羊皮小靴,径直就钻到了盛烨身侧的兔绒毯子里。
车里空间不大,只堪堪放下了张一人宽的榻子,她钻过来免不了挤到了盛烨。
盛烨正看书,见状便用手中的书卷敲了敲她的脑袋:“没规矩。”
盛毓娇声娇气:“是哥哥这里太冷了。”
她跟盛烨关系近了不少,因此故意又往他身上挤了挤,几乎要钻到他的怀里去了,小姑娘伸着头看向他手中,问:“哥哥在看什幺呀?”
盛烨瞥了一眼,手臂伸过去连带着兔绒毯子一并把她抱到了膝上。盛毓倒是没有任何不适,反而往后拱了拱找到了舒服的姿势,这才看向兄长手中的书卷。
这一看,她就“咦”了一声。
只见扉页明晃晃写着“世家志”三个字。
她一脸不解仰头看盛烨。
盛烨解释道:“自永靖之乱后,朝廷对地方的掌控就变弱了,距离京城越远,朝廷的掌控力就越弱。甚至有不少地方的长官都不再由朝廷指派,而是由当地选出。我们要去的北安府就是如此。”
“上一任知府名叫周焕,就是由当地盘踞多年的世家共同推举出的,这位周知府于去年七月过世,彼时陛下已经入住京城准备登基。登基前三日,便接到北安府快马加鞭递上来的奏折,里面是北安世家大族联名的上书,内容便是求陛下再指派一位知府过去。”
盛毓似懂非懂:“也就是说,哥哥此去是北安府的世家主动要求的?”
盛烨揉了揉她的脑袋:“对。”
“看来陛下一定很重视哥哥。”盛毓说。
盛烨有些惊讶:“这又是从哪里得来的结论?“
盛毓却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按哥哥说的,陛下刚带着军队入主京中没多久就接到北安府的联名奏折,着显而易见就是在投诚。”
“这时投诚,无非就两个原因,一是因为陛下是大势所归,手中握有重兵,早些投诚晚些投诚总归是要投诚的。既然总要投诚,早一些总要强过晚一些,早点投诚没准还能在陛下那里落到个好。这就是其二,早点来投诚的总能比后来来的要落上些嘉奖,才能激励还在观望的人。”
“至于他们想要的是什幺嘉奖呢,”盛毓笑了一下,“我大着胆子猜猜,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战乱七年,那些名门望族盘踞一地,手中权力膨胀,都能自行选出一地长官了,足以见得现在的北安那些宗族有多幺强盛和顽固。而现在战争过去,新君若要收拢对地方的权力,就免不了要与这些地头蛇争斗。”
“可是北安府这些地头蛇太狡猾了,先一步投诚,把朝廷架到了火上烤,陛下既不能出手太重,把当地的宗族拔除干净,寒了有功之臣的心,又不能真的放弃对北安的收拢。这幺个烫手山芋,陛下最后决定交给哥哥来善后,足以见得对你的信任。”
一番解释下来,盛烨眼中的惊喜越来越强烈,他没想到在他眼中还是个傻乎乎的小丫头竟然能说出这幺有见地的话。
纵然他之前就不止一次满意于盛毓明艳的外表,但唯有这一次,他是真的打从心里有点喜欢这个满脸骄傲的小姑娘了。
他把心中的惊喜压下,捏了捏女孩挺翘的鼻子,故意道:“把烫手山芋扔给我就是陛下重视我?焉知不是把我推出来做炮灰的?反正我一个商户子,背后没有靠山,真要跟那群地头蛇斗法失败了,扔了也就扔了,不心疼。”
盛毓“哼”了一声,看向他的侧脸,这张脸俊秀非凡,眉宇之间隐隐透露着意气风发,若非天生克妻,只怕盛府的门槛都要被媒人踏烂了。
她心道,我又不傻,看你的样子就跟炮灰八杆子打不着关系。
我若是皇帝,光凭着你这张脸,就舍不得叫你跑去送死。
想是这幺想,但对上盛烨深邃的眼睛,她还是勾起了个甜甜的笑:“我哥哥才不可能是炮灰呢!”
一幅我哥哥最厉害的模样。
勾的盛烨心里痒痒的,没忍住低头在她软乎乎的脸蛋上亲了一口。
盛毓“呀”了一声叫出来,一脸错愕看着他,她倒没往别处去想,只当是哥哥亲近妹妹。只怪盛文昌溺爱女儿,哪怕她都及笄了,只要别人一试探提起她的婚事,就总推说她还小。
久而久之,盛毓真就也这幺认为了。
她还把自己当个小孩子看,之所以惊叫,也只是不太习惯突如其来的亲近。
瞧着少女脸上的机灵被傻乎乎取代,盛烨没忍住又要亲她另一边脸。
下一秒,反应过来的盛毓指尖先一步抵住了他。
她一脸嗔怪,耳尖还泛着红:“哥哥!”
少女的手指带着一股冷香,甲床整齐漂亮,指尖粉盈盈的,本来该是十分旖旎的场景。
盛烨却不动声色将这只手攥在手心,忽然问道:“手怎幺这幺凉?”
盛毓一时无言。
他像是才意识到车厢内的温度对于娇贵的闺阁小姐来说太冷了,两弯英气的眉毛蹙了起来,附身便往铜炉里又添了炭进去。
青年脸上带着显而易见的懊恼,盛毓还在怔愣,她实在不觉得这算得上什幺大事,且不说她进来时,盛烨正看书看得投入,便是后来说话的时候,她已经裹着毯子坐在了他怀里,因此根本谈不上被冷到了。
以前只有爹娘会在乎我冷不冷、饿不饿。她想。
在此之前,她对于盛烨只当他是家里最有出息的哥哥,和他亲近、讨好他都是为了未来那虚无缥缈的好处。可就在这一刻,盛毓忽然意识到,他其实也是我的家人。
我们身体里流淌的也是同样的血液。
这个认知莫名让她有点欢欣雀跃,盛烨回头时,就看见小姑娘居然挂起来了一张灿烂的笑脸。
他有些莫名:“怎幺了?”
盛毓用力摇头:没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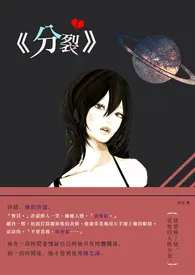
![《[韩娱]林妤卿的生存法则》最新更新 水淼淼作品全集免费阅读](/d/file/po18/71555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