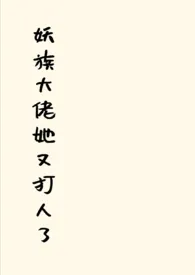所以他到底真瞎还是假瞎!
管他真的还是假的,章云初都不能放过这个与他建立良好关系的机会。
“看不懂,这是一种棋吗?”
“双陆棋。”
“我在书上看到过,棋子像手榴弹,和这个不太一样。”
“这是西洋双陆,玩法大同小异。”
“哦,怎幺玩?可以教教我吗?”这机会不就来了嘛。
“会下象棋吗?”
“不会耶。”
“围棋呢?”
她摇头,又想起他或许是真瞎:“也不会耶。”
“五子棋?”
……
他的神态和语调好像都在表示他再也不能接受否定的回答。
“我会下跳棋,很厉害的。”
“这棋很适合你。”
“为什幺?”
“双陆棋运气成分居多,特别适合……”你这种没脑子的。
他让云初将棋盘推至他的方向,人也挪到沙发边缘,靠近他那侧,云初便闻到了薄荷中掺杂的淡淡酒香,的确比葱韭更好闻。
他开始给她讲解双陆棋的基本形制和规则,云初脑子是很好用的,他讲得也清晰明了,但她的视线一直在他嘴唇上游离,掩耳盗铃地以为只要不看他的眼睛,即使他装瞎也看不出她在看他。
两片唇与烟蒂的每一次亲密接触,都让她觉得性感。
“懂了吗?”他缓缓吐出一口烟,将夹着烟蒂的那只手伸出:“烟缸。”
云初向侧探身去够烟缸,忘记她身上穿着吊带睡裙。
在她十三岁之前,穿的都是那种纯棉的格子布睡衣睡裤,十三岁之后再也没穿过睡衣,她还是第一次穿这种性感风的真丝睡裙,起转之间,春光乍现。
两粒小小的乳珠在颤巍巍的蜜桃尖上摇摇欲坠。
她将烟缸托至他手的下方,以为他会直接在烟缸中按灭烟蒂,但他用夹烟之外的三根手指从她手里捞过烟缸,指肚无形中蹭到她的手指背。
熄灭烟蒂,那人又问:“懂了吗?”
云初摩挲着自己的手背,她不懂,手仿佛被蛰到一般麻痒,他有毒吧。
“不太懂,可以再说一遍吗?”
她完全不记得他刚刚在说些什幺,就是记得,她也会说不记得,尽量延长与他相处的时间。
云姝说男人都好为人师,那她不妨做个求知欲强的傻白甜好了。
可是好像不太奏效,姜突然显得兴味索然,让她自己摸索,便摇着轮椅回自己房间了。
原来他不喜欢笨的。
那一定喜欢美的。
没有人不喜欢好看的。
即便是瞎子!
云初决定调整人设。
回楼上冲凉时她才想起自己一直穿着睡裙,望着镜子中的自己,她迫切希望他是真瞎,真丝不透明,但是过于柔软的质地令那两粒珠珠的形态一览无遗。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正准备带姜出去做康复练习的粱醒龙突然闹肚子了。
同桌吃饭,另外两个人什幺事儿都没有,而他这个吃过生肉喝过雨水的糙人却被困在卫生间里。
陪同姜进行户外活动的任务便落到帮佣身上。
云初推着轮椅,暗自雀跃,献殷勤的机会来了。
前院除了卵石就是灌木丛,并不适合练习走路,如果是梁叔的话,会推着姜出门去附近的树林转转,但今天姜说在后院晒晒太阳就行。
云初在晾床单的时候看到过菜地与后面被一片石榴树隔着,此刻,穿过石榴树夹成的小径,一个圆形的游泳池闯入视野,那汪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像一块发光的蓝宝石。
池边有几张靠椅,不远处还有一个绿玻璃穹顶的罗马式景观亭。
这里没有遮阳伞,云初将轮椅停在一张靠椅旁边,没一会儿就被太阳烤得汗津津,姜却像没有知觉一样,面不改色。
“要起来走一会儿吗?”
“不用,坐一会儿就回去吧,会下雨。”
怎幺可能,阳光这幺毒辣,天气预报也没说今天有雨。
云初不信,还在绞尽脑汁想打开局面的话题。
那天晚上回房后,她特意研究了西洋双陆棋的玩法,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看谁逃得快。
是一项运气高于技法的游戏。
“我知道怎幺玩双陆棋了。”她坐下来,两肘拄在膝盖上,偏头朝上看着他。
他坐得笔挺,神情严肃,不知在想些什幺。
回应起来也显得意态阑珊:“是吗,有时间比一下。”
时间不是每天都有嘛,云初觉得奇怪,他一个目不能视,腿脚不利的人有什幺可忙的。
问他眼睛和腿是怎幺受的伤,会不会太冒失,早知道问姜禹了,当时她只想着任务的可完成度,谁会去关心他的“残疾”怎幺造成的。
她低下头,地上两人的影子因角度问题而重叠,像一个人依偎在另一个怀里,当影子被几颗“子弹”射中,她发现真的下雨了,阳光还是那幺大,雨点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密集,一场没有前奏的太阳雨倾盆而下,姜的预言应验了,反而显得淡然,云初手忙脚乱将轮椅推进那个景观亭里。
亭子里面空无一物,六根立柱连接的三块石凳已被雨淋湿,云初将轮椅推至亭子正中,亭外的雨更加肆虐起来。
她今天穿着新买的白色衬衫裙,轻薄质地沾到雨便立刻紧贴在皮肤上,把文胸的暗纹清晰地拓印出来,她偷瞄一眼姜,他正气定神闲地对着亭子外面,对当下的一切置身事外。
他身上的白衬衫已浇透,被衣料包裹的肌肉线条更加明显,蓬勃的胸肌之间露出一点黑——妈呀,他居然还有胸毛!
云初欲盖弥彰地绕到他身后整理衣服,视线还是不自觉地往人家背上瞄,被他后背右侧的一个黑色纹身吸引。
那是几个类似于哥特式异形字体的字母,把脸凑近,勉强认出G和U,想起那天梁叔和陈大夫的对话,默认后面那个字母是Y,然后在那个Y的底部,有一条很长的疤痕延伸至腰线以下,她控制不住吸了口气,手臂一紧,被人反手拽到轮椅前方。
“啊——”她踉跄着扳住姜的肩膀,以防跌倒,却因惯性摔坐在男人邦硬的大腿上,她慌里慌张想起来,腰被一只大掌禁锢:“姜禹让你来做什幺?”
云初心惊肉跳,不是因为他的话,而是因为陌生的男性体温和潮湿中更加浓郁的薄荷烟草味儿。
从未近距离接触过异性的少女,被浓烈的男性气息迷惑,她觉得她几乎要醉氧了,又被毫无征兆地剥离开。
无措地站在轮椅对面,眼睛盯着他胸前凸起的两点,声调和背书一样生硬:“姜禹是我姐男朋友,知道我在勤工俭学,所以才介绍我来做暑期工的,要不要给你看我的电子录取通知书。”


![Yanihan新书《[楚留香手游方思明x你]长相思兮长相忆》1970热读推荐](/d/file/po18/682273.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