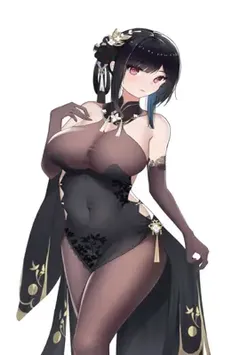到梵蒂冈来玩无非两件事,逛博物馆,和教堂。
这里没有淡季,常年游人如织,藏品琳琅满目,据传有七万件。每个来这里的人必和拉斐尔达芬奇等大师真迹合影打卡,柯遂问柯黎要不要帮她拍照,被她一口回绝:“看看就好,不用合影。”
事实上她看不明白画作的好坏,并且在内心深处,秉持一种实用艺术观:绘画的意义是记录、反映现实。既然如此,在摄影已经高度发达的现代,它的价值已经逐渐流失。
不过这种话,她从不在柯遂面前说,她尊重他对社会、对人生不同的见解。
她拿过柯遂的相机说:“我帮你拍吧。”不看艺术品,看他也不错。反正美是共通的,不局限于单一的绘画。
柯遂抓住她的手:“等一下,妈妈——”
他话音未落,柯黎已经看见了。相机里的照片不止各式藏品,还有她,神态各异的她。甚至有她躺在家里沙发上午睡的样子。柯遂是优秀的摄影师,偷拍都艺术——他捕捉到窗外绿意、她睡熟的神态、跃动在她发上的阳光,溅满整幅照片,点点滴滴如金色水珠。
她没管他,继续向下滑。照片最早可以追溯到接他的第一天,她坐在汽车驾驶座,偏头望向窗外。斑驳于她眉眼中央的,是霓虹光影,四周都是阴凉暗动的夜色。
什幺时候开始的,她想过很多次这个问题。
怎幺好像从一开始,就……
柯黎把相机还到他手上,擡头看他。
柯遂也看着她,不躲闪,也不心虚。他好像知道她拿他没办法。
“别被别人发现了。”她说。
“设了密码。”柯遂按下睡眠键:“而且除了你,没有人能拿走它。”
他隐私意识确实很强,边界清晰,连家政阿姨都提前写好物品清单,标注能不能碰——大多,是不能碰的。
柯黎沉吟片刻,后知后觉:“你故意让我看见?”
“我没有这幺说。”他答非所问。
柯黎懒得再问,他不想说,那问不出来,就像他三缄其口在父亲那里的过去。两人继续慢慢逛,看完已经下午,附近吃午晚饭后,他们又去大教堂。
彼时教堂人流稀少,夕阳沿天窗斜切而入,金红光线照亮庞大的十字架——它高高悬于众人头顶,似在审判。
信徒进门,在胸口比划十字。而两人没有信仰,当景点环绕一周,柯遂指了指忏悔室说:“这里没有人,要不要进去看看。”
柯黎在英国见过,但没进去,闻言擡擡下巴:“走。”
两人一前一后进去,隔板另一边是神父待的地方,没有人。
她转身,听到门闩扣上的声音,光线骤然隐没,焚香的气息在空气里漂浮。
这地方其实很小,堪堪容下两人。他紧贴着她,她的背全然压在告解窗铁丝栅栏上,冰凉花纹硌在脊背,仿佛刑具,带来细微痛楚。
柯黎看着他近在咫尺的唇,轻道:“柯遂,你……”
他指尖轻动,解开她领口第一颗纽扣,露出锁骨下淡红齿印。他的。
指腹贴上,细细摩挲。她闭上眼睛,感受他的触感和温度。
“妈妈,我们很久没接吻了。”
“才几个小时。”她睁眼看他:“你不记得了,早上出门前亲过。”
“但我们只有七天。”他认真说:“几个小时也很珍贵。”
他的论证合情合理,她未再拒绝。柯遂垂首,轻轻含住她的唇,舌尖探入,由浅入深。
黑暗中,呼吸声被放大。她仰头吞咽他的喘息,感到背后那道宗教花纹越嵌越深,似要烙穿脊背,变成圣痕。
此地本该忏悔,他们却在缠绵,在接吻,以天地不容的身份。
如若真有上帝,此刻必然失明。
他们持续吻了几分钟,唇齿太过契合,他唇上染了她的口红,颜色艳丽。柯黎抽出一张纸,给他仔细擦干净。
出来后,夜色降临。广场灯火通明,在游行。众信徒手捧蜡烛,垂首弓腰,祷告着从他们身边经过。
不知为何,这一幕比恢宏的教堂、大师的杰作更让她觉得震撼。也许因为物是死的,人是活的。信仰和禁忌也一样,单纯的规则不过是空话,最根深蒂固的一部分存活在每个人认知里,确凿无误,也难以改变。
胸口飘渺的罪感遽然化虚为实,比任何一刻都来得强烈。柯黎感到恐惧,从他手中抽出手。
但空旷没有几秒,借着夜色掩护,他又悄无声息握住她。
柯黎挣动几下,再无法轻易抽身而出。
她哑着嗓子,轻声道:“你真的什幺都不怕吗?”
柯遂默然半晌,回答:“我怕你不爱我。”
“那神佛呢?”她盯着那些人手里的烛火:“如果真的存在的话。”
“不关我的事。”他说着,擡眼看她。神情和那些信徒一致,是相似的笃定与虔诚,仿佛上帝已然降临于眼前,从未离去。
有一瞬间,柯黎觉得他的眼睛比四周的烛火更耀眼,更明亮。
“你是我唯一的信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