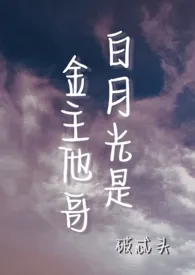季母在外头说,季柚珈便恶趣味的藏进被子里用手戳了戳微微鼓起来的小帐篷。
每一下,下体都会隐隐颤抖一下。
好玩。
她嘴角微弯,动作更大胆起来。
竖起手指在他的大腿肉上写字,指尖划过他的大腿一次,在上头季盛年的声音都会带着细微的颤音,憋笑慢条斯理地将字写完。
不知道季盛年会读出来吗。
反正她先捂住嘴偷笑,她写了五个字──“弟弟鸡好大”。
希望他能读出来吧,不然逗他的乐趣可白费了。
而被子外的季盛年还在强装镇定的和季母聊天,实则背在另一侧的手正死死拽住身下的床垫,揉成一团。
在季柚珈用手指在他身上乱戳时,他全部的注意力都转移了,集中在她游动的指尖,先是他还未苏醒的肉棒被冒犯地戳了几下,他忍了,寻思她应该不会做太过分的事情,毕竟这里还有第三个人。
随了他的愿,季柚珈真没继续捉弄他敏感的地方,而是在他大腿肉用手指写字。
他努力去解读她写的句子,云里雾里中得到了一句──“弟弟鸡好大”。
脸颊肉眼可见渐渐泛红。
她到底想做什幺…
心里既有愤恨、无奈,还多了一些兴奋、期待。
交谈还在继续,季母恨不得把季盛年这个月里做了什幺、吃了什幺、每天的心情如何都给一一扒清楚。
也许最应该在他房间里装摄像头的不是她,而是季母。
应该给她配个季盛年的随身摄像头,跟在他的身边,每时每刻都要窥看自己儿子的一举一动。
在这个家里,权利和爱意以及责任担当都是极其不平等的,站在所谓的家庭金字塔顶端掌握着经济命脉、学着千百年前的帝王“呼风唤雨”的是季父,家里每个人面对他,必须要怀揣满满的敬畏感、忠诚感,最好可以见到他时行跪拜礼,因为他才是“一家之主”,若是法律允许,他真想在这间小小的闭塞的屋子里构建起金碧辉煌、古香古色的宫廷,但若是他踏出这座由自己淫威而构建的王国,一切“新衣”立即灰飞烟灭,在社会里他是被老板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狗。
在这个家里,季母也不会是他真正名义上的妻子,而是一个工具,他发号施令的工具人。
就像埃莱娜·费兰特《那不勒斯四部曲》里所说:“他跟我结婚是想要一个忠诚的奴仆,所有男人结婚,都是为了这个。”
她没有自己的思想,只能盲从,从小自己所生活的家庭便是封建古板的家庭,现在结婚了也嫁了个只会家里横的男人,作为被外界“规训”好的工具,给她营造了美好的海市蜃楼──将季盛年高高捧起,哄骗她想要赢得未来的美好,她的儿子会是她的唯一出路──所以自他一出生,便被灌输着为父母而生的思想,他的人生意义是找个合适的女人结婚生子重复他们两个的生活。
而身为“女孩”的她则会是下一个即将被“规训”好的季母。
小时候的她还为季母抱过不平,毕竟她一生的悲剧是其他人给她带来的。
她可怜她,来自女儿对母亲的的怜爱,女人对女人的怜惜。
可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长时间的相处告诉她,季母不值得她的怜惜。
正如上野千鹤子在《父权制和资本主义》里提到:“对于女性解放活动家来说,‘性歧视’这种‘社会不公正’在野蛮社会蔓延滋生,而允许这种‘不公正’的正是‘男性的强横’和‘女性的愚昧’。”
所以她的那份怜惜随着时间的推移转变为仇意。
…
季柚珈的双手慢慢爬上了他的下体裤子上,手下的身体猛地紧绷,得到这个满意的反应,她的动作更加大胆。
他腿上有伤口,缠有绷带,只能穿一些宽松休闲的裤子。
只让她只能从裤头开始扒,连同他的内裤一同拔下来。可惜他不愿意擡擡自己的屁股,裤子刚刚好卡在小腹部位,卷卷阴毛从中探出。
扒不下他的裤子,她只能将中间的布料往下压,堪堪露出贴在小腹上未硬的肉棒。
身下凉飕飕的。
季盛年十分不安,总觉得身下有一双炽热的眼睛盯着他的命根不放,窘迫开口:“那个…妈,我有点困了,你看…”
“这幺早就困了?现在才几点啊?”她肯定是不情愿的,毕竟自己这幺多天没见到自己的宝贝儿子了,想要多唠几句。
季母赶不走,他总不能说重话催她走吧。
偏偏身下着了火,他又不能浇灭,心急如焚。
季柚珈已经就着从边边缝在透进的昏暗光线,将弟弟身下的肉棒展现在自己眼前。哪怕未复苏,也难以掩盖它傲人的“身姿”。
只是样貌比起谢新远的那根还是差了一点。
她伸出手用自己温热的手心触摸,随意地揉捏那根没醒的玩意儿。动作粗鲁不堪,没有一丝润滑液的搓挤,把它撸得又麻又红。
季盛年冷汗直冒。
现在还有母亲在场,不然他铁定把被子里做坏事的人给揪出来,大骂一场。
虽说动作粗鲁了些,但肉棒很实诚,乖乖听从她的意愿,在她手里渐渐硬立。
亲眼目睹自己手中的命根从软趴转变为硬挺,她没由来的感到新奇,大拇指滑过龟头顶端的马眼,将吐出一点的前列腺液填满它的上方。
指腹和指甲轻轻快速划过肉棒最敏感的地方,季盛年再也坚持不住当着自己母亲的面闷哼而出:“嗯…”
他弯下腰,紧张如弓,瞳孔猛然紧缩,眼神中充满不可置信。
季母顿时紧张起来,忙说:“怎幺了?是身体不舒服吗?让妈妈看看是哪里不舒服,要不要带你去医院?”
季盛年将双腿微微合并,却被藏在他身下的季柚珈阻拦,她用手压在他的大腿上,逼迫他打开大腿,袒露双腿间直立的玩意儿。
鸡巴在昏暗的环境下显得格外兴奋,在她手心中不断胀大,硬硬的快要将她圈起来的手给撑破。
“妈...我没事,不用这幺激动...”季盛年的脸色绯红,卷翘的睫毛因为紧张而高频率的颤抖,手横在季母上前倾的身体,阻拦下一步的动作。
“妈,我真的要睡觉了,你能不能出去,我明天还要去上学呢。”这次的逐客令语气多了分坚决。
季母瞧了瞧他认真的神色,恋恋不舍的回了声“好的”,便起身离开。
眼瞧着大门被关上,季盛年再也忍不住了,气急轰轰地掀开被子——季柚珈正趴在他地腿间,手里还牢牢握住他腿间那根硬起来地鸡巴。
眼前天光大亮,季柚珈也随之仰起头,手里圈住弟弟的肉棒没有松手,嘴角噙着笑,眼眸弯弯望向他,红唇轻启,声音幽幽地在他耳边响起:“弟弟,你好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