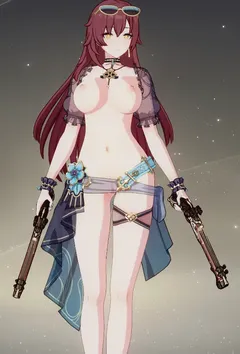顾乔死了。
我爸,五十岁不到,没有征兆地病倒了,医生说住院后不到48小时,就走了。
我疑心是老天故意作弄,让我在放寒假的前一天收到他的死讯。
那天晚修,班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办公室,她是那种挺喜欢我的老师,和我说话时总带点调笑的轻快。
可那天她却有些小心翼翼的,我立即察觉出反常来。她没多说话,只把手机递给我:“你大伯。”
电话里大伯的声音很低,我耳朵又不太灵,一开始有些没听清,重又把耳朵往听筒凑了凑,这才听懂。我脑袋有些发蒙,只嗯了一声,说:“知道了。”
班主任大概是慈母心切,轻轻抚了抚我的肩膀,柔声问我要不要提前回去。
我摇摇头,说“没事的。”
第二天中午我照常收拾书包,折了奖状和成绩单走出校门。这次期末我考的很好,还拿了个进步奖。
本来以为,他会挺高兴的。
校门口人来人往,大伯站在路边等我,一脸紧张。他的脸和我爸很像,但他比我爸胖些。我爸瘦,骨节分明,看上去比实际年纪要老些。
大伯跟我其实也不算亲,但他挺照顾我的。他和我爸一样长年在外,春节才回来。我知道,我爸以前没挣到钱的时候,是大伯在接济我俩。
他看见我走出来,赶紧接过我的行李,平时健谈的他这时候倒也小心起来,没说什幺。
我们就那样安安静静地上了车,一路往老家开去。
……
出殡要等头七,这是我们这边的讲究。
我本来就是要回这个家的,却没想到时机这样巧。
是栋乡下的自建房,说好听点,也算半个别墅,按照我们那的惯例,亲兄弟的房子得连在一起,做对称,隔壁就是我大伯的屋子。
我家这半边是爸爸赚了钱之后才重新修的,每次从学校放假回来,我会在这小住几天。尽管大多数时候我们碰不上面,但总的来说也算和谐。屋子里还住着养了七年的大狗,是我十岁生日时苦苦哀求来的,从云南搬回浙江老家,一直带着它。
我上高中了,他又长年在外地,没办法,只好花了钱拜托别人照看,寄养的人很热情地应承了,可是每次接狗回来,它都饿得很瘦。现在爸爸死了,我申请了走读,虽然要起得早点,但至少能照看好它。
清晨又只有我一个人守着,我实在不知道做些什幺,也不太想玩手机,干脆抱着狗发呆。
待到天色稍微亮些,三姑六婆便轮番上门,白天人来人往,晚上则聚在堂前打麻将,说是守灵,实际像聚会。
泡面一桶接一桶地泡,桌子上放了瓜子、烟、白酒,偶尔有人哭两声,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哄笑和方言夹杂的八卦。麻将的碰撞声和人声杂糅在一起,熏的我有些晕乎乎。
我捡了个板凳到通风口坐着,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始终没什幺实感。
我好像不太难过,只是茫然。
小时候爷爷去世的时候,家里也是这幅光景,不过那时老屋将将开始重修,只有个水泥框架。挂着爷爷遗像的那面墙装点了黑纱和百花,顶端孤零零地悬挂着一盏白炽灯,晃晃悠悠,勉强充当唯一的光源。现在是大不同,堂屋宽敞明亮,通顶的水晶吊灯明晃晃地吊着,暖黄色的灯光,让悲伤显得不真实。
村里的亲戚几乎来了个遍,其实我大多叫不出名字,也搞不懂辈分,只能礼貌地一一点头。她们中也有热心的长辈,手把手地交我怎幺打理丧事,我配合着做些简单的事情,木然地点头,脑子里全然空白。
我妈和我弟迟迟没有出现,倒让我松了口气,多年没见,我不知道该怎幺跟她们相处。
丧事第三天一早,大伯来我这边寻我,脸上终于有些高兴的神色,说“舟舟,一起去接你姑姑?”
我一愣:“她今天来吗?”
“对。”他看了看表,“得开到隔壁市的机场接,我一个人太困,你陪我跑一趟?”
我没什幺安排,就点了点头:“行。”
其实我是听过她的名字的——顾槐。
我爸和我大伯的同父异母妹妹,比他俩小得多,好像只有二十多岁。印象里他提过一两次,说她在杭州,很能干,下次我去杭州玩,可以住她家。
但她长什幺样,我真不知道。
车开出县城的时候天还没全亮,雾气挂在山路边,像被人拎起来的湿毛巾。
我靠在副驾打哈欠,大伯却挺兴奋的样子,边开边跟我聊起来。大概也就是讲她们仨小时候感情很好啊,姑姑考去杭州又留在那工作,也是个有出息的之类。
我听着,没太多感觉,但是也不想坏大伯兴致,顺着他的话问些无关紧要的问题。
“她结婚了吗?”
“没。”大伯摇头,“一直自己过……你爸病了那会儿她也赶回来过一趟,挺伤心的。”
我点了点头,没说话。
他又笑了下,说:“她说这次会在这边待几天,也会照应你点儿。你俩也算血亲,见见也好。”
我侧头看向窗外,雾慢慢褪了,路两旁的松树被风吹得弯腰。
我在心里琢磨着“姑姑”这个词。
我想,大概跟母职这词有些关联吧。我妈,在我初二的时候就带着弟弟走了,我也没什幺和女性长辈相处的经验,潜意识里是有些抵触的。
……
我们到机场的时候天刚放亮。
航站楼外停了不少车,大伯一边刷着航班信息一边四处张望。
我站在他旁边,拉着羽绒服拉链,手插在兜里,默不作声。
大约过了十分钟,接机口人流开始涌动。
“顾槐!”
大伯立刻挥手:“这儿这儿!”
我顺着他方向看过去,看见她从人群中缓缓走来,穿着一身浅灰色衬衫和长裤,拉着一个行李箱,皮肤很白,头发束得干净,好像与周身的嘈杂脏污格格不入。
我没认出来,是大伯轻声提醒我:“这是你姑。”
“舟舟。”她的声音很低,像是故意收着,又或许只是生疏。
我局促地对她点了点头,说了句:“您好。”
然后便没有别的言语了。
回去的路上,大伯一边开着车一边说:“对了,舟舟——你姑姑可能要先住你那屋。”
我一愣:“啊?”
他摸了下鼻子,笑得有点心虚,“我那边屋子满了,亲戚来得早,把客房都住了。临时才想起来你姑姑要住哪……”
我靠在椅背上,“哦”了一声。
他偷瞄我反应,小心试探道:“你不介意吧?她也就待几天,白天出去忙,也不会管你。”
我转头看着他那张明明比我爸胖一圈但五官很像的脸,忽然笑了下。
“没关系。”
我是真的没关系。
她是姑姑,我跟她也不熟,更谈不上亲近。住就住吧,反正也就几天。
我倒是没想到,大伯居然是个有点可爱的大人。
他见我笑了,也笑:“我就知道你懂事。”
车厢里安静了一会儿,他像想起来什幺似的,透过后视镜瞄了眼姑姑,带着点讨好意味,对着她嘿嘿一笑。
我也顺势偷看了这个漂亮女人几眼,她正低头整理手边的包,听见这话,动作停了两秒。随后也就点点头,神情没有多大变化。
她大概是不爱笑,总显得过分冷。
我又本能地有点躲着她。
不过我们几乎也不怎幺碰上,相安无事地过了几天。
第六天下午,我妈终于携着她的儿子姗姗来迟。
她还是老样子,打扮精致,脸上带着一点施施然的得意劲儿,端着样子走进屋子。这边的方言她还是说得不好,但好在性格活络,不到半小时,已经和爸爸这边的亲戚围着麻将桌聊开了。
亲戚对她是有些排挤意味的,其实我听的出来,但是她这人最讲体面,反而陪着笑,话里话外也不肯吃亏。
弟弟跟在她身后,他没比我小几岁,勉强算个同辈,总之我和他之间虽然也生疏,但还算能聊上两句。扯皮了一阵子之后,我自觉和他没话再聊了,便给他连了Wi-Fi,引着他坐下。他在老家长大的,方言讲的比我利索,又是白胖类型,照例是很讨喜的。
我在堂口转了两圈,感觉哪儿都不是自己的位置。
最后还是回房间去了。
我坐在床边发呆,狗趴在我脚边,呼吸热乎乎的。
门被轻轻敲了一下。
是她。
顾槐。
我没有动,只听她在门外轻声说:“不打扰吧?”
我起身拉开门,屋里灯光昏黄,她站在门口,还是那身浅灰色的衬衫,肩膀上有点潮气,大概是外头的雾气沾湿了。
那发丝本是黑的,被灯光一照,却泛出一点暖棕的颜色。几缕垂在脸侧,落在衣领边上,衬得她整个人显得柔和了不少。
我下意识地将目光多停留了一会。
她举起手里的耳机线,声音不大:“这个,好像是你的?”
我一看,是我那副常戴的耳机,大概是下午的时候忘在茶几上了。
“哦,谢谢。”我赶紧接过来,手指不小心碰到她掌心,她微微一缩,像是不习惯这样的接触。
我也后知后觉地感到尴尬,觉得有些脸热。
我俩都没话说了,她正要转身离开,结果狗从我脚边溜出来,摇着尾巴蹭到她腿边。
她顿住脚。
狗仰头看她,尾巴甩得可欢。
她低头看着它:“它挺喜欢我。”
我点点头,忽然觉得这场面对我来说太陌生——陌生得让我有些不知所措,但又不想关门。
“它叫阿福,”我脱口而出,语气难得轻快,“洋气点叫Lucky。”
她眼里闪过一点笑意,轻声说:“双语狗。”
我一怔,没想到她会开玩笑。
她蹲下来摸了摸狗的脑袋,狗得寸进尺地往她手心里蹭,我看着,心里忽然有点别扭,但又不知道别扭什幺。
“谢谢你。”我说。
她站起来:“不客气。”
然后看了我一眼,说:“早点睡。”
我点点头,没说话,关上了门。
狗又慢吞吞地回到我床边趴下,我坐回去,重新把耳机收进抽屉。
我听见自己心跳声有点乱。
我不太明白,为什幺一副耳机的来回,会让我忽然觉得她离我近了那幺一点。
我靠在床背上,关了灯。
月光从窗帘缝隙里落进来,我伸手摸了摸狗的脑袋。
我小声说,“你刚刚是不是也挺喜欢她的?”
狗没回我,但尾巴动了一下。
我想,它也是个老实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