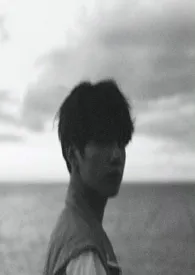最后,应风色换了半痴剑、没有鳞片的紫苑鳞甲,还有那本《还魂拳谱》,任凭羽羊神说破了嘴也不再更换。
羽羊神心疼得要命,仿佛扔水里的是自个儿挣来的点数。
宝衣是上下两截式的中衣与裤筒,却是摊开的版型,并未缝合,材质较棉衣略厚,表面光滑柔亮,揉搓仍会产生厚茧绸似的绉折,一松手即能恢复原状,不留痕迹,十分坚韧。
推测是镜原雪蛛丝纺成的布料寻常刀剑难伤,玄铁精金等异材又不易锻打成缝衣针,索性在边缘轧出圆孔,缀以环钉,然后再穿绳以代缝线,于穿戴者身上缚成衣裤。
如此一来,防护面积大又不致影响行动,还能依体型调整,毋宁更近于甲而非衣,可说是极巧妙的设计,就不知道”鳞“字何解。应风色调整袖子和衣筒,直觉适合穿在衣底,只不知防护力怎么样,心念一动,提起了半痴剑。
“应使如不想要臂腿,卖与吾如何?吾可以放在杂项目录里。”
“能扎穿?”用剑壳尖端在腿上比划了一下。
“保证穿。“应是半痴剑等级太高,入手限定品的感觉贼爽。
“可否向羽羊神借把凡铁试试?”
“应使就非得这般手贱不成么?爱惜装备啊。“羊头半神以爪覆额,可惜怎么也翻不出眼白。”凡兵俗物戳不穿,但该乌青瘀肿的一样不缺,你大爷的锄头、你姥姥的擀面棍,通通一视同仁,往哪儿招呼就哪里疼。
“高级武器包括但不限定,是有可能伤到宝衣的,要不应使以为绑绳子的环钉孔眼何以轧上,拿牙签戳的么?要发挥等若应䶮《紫煌鳞羽缠》七成功力的防护效果,毋须这么麻烦,花两百点买使用手册就行。”
“使……使用手册?”居然还有这种东西。
“吾瞧瞧,哎呀真真不巧,应使剩一百点,买不起啊买不起。不如退掉那本没啥用的——”
“不必了。”应风色一把将《还魂拳谱》攒手里,没得商量。
他非常确定杂项或武功目录里,没什么价值两百点的使用手册,当中必有蹊跷。
即使如此,雪蛛布料抵御凡兵绰绰有余,毋须在细琐处缠夹,反正以后需要再换。
况且,为防有诈,最后还得换样东西。
“我要换杂项目录里的’越世之眼‘。”
越世之眼,兑换点数一百点,说明只有寥寥十六字:“神域大千,庸凡难见,赠君慧眼,灵光乍现。”插图是名持卷夜读的青衫书生。
应风色不相信有什么灵眼,但此物的低廉售价却预示了一个可能的陷阱。
若使者未换越世之眼,带回“人世”的秘笈,极可能全是白纸,羽羊神只要推说“神域之物在人世无法使用”,连秘笈也省了。
这是非常典型的郎中手法。
就算有半痴剑、紫苑鳞甲等,青年亦未轻信降界之说。
一个库容广袤、历史悠久的暗行组织,或心机深沉计算精密的阴谋家也可能办到,眼见不足为信。
羽羊神沉声笑起来,不是油腻促狭的口气,仿佛回到初轮全军覆没的当下;那是图穷匕现之际,爽快认输的枭狂气度,是令人回味尊敬的对手。“不愧是四千点的男人。容吾提醒诸使;降界的一切,请勿向凡人言说,违者亦死。
“此外,因汝等被吾复活了一次,魂魄穿过幽泉再回到躯壳里,归返人世时会有少许不适,毕竟没什么是毋须代价的,应使请务必撑过去。那么,就下次见了,吾先行告退。”
…………
对话的终末印象是一片漆黑。
似是在羽羊神说完的下一霎,应风色便昏死过去,快到没有丝毫感觉残留:没有疼痛,没有药物生效的异样发热或发冷,甚至没有被摩擦过光滑水精的毛皮所殛的刺疼麻痹……什么都没有。
反正不合理之事的清单,已快追上通天壁的山道长了,也不差这一件。
应风色在房内的床上醒来,浑身滚烫,头重脚轻,挣扎坐起的瞬间一阵天旋地转,差点把脑袋摔进秽物桶里,顺势又呕了一通酸水,吐得死去活来。
自上山以来,他没生过这么严重的病,时间感在呕吐、发热,以及浸透被褥的冷汗中彻底丧失。
等到能好好同福伯说话,才知从发病起算整整过了五天。
应风色是现今唯一住在风云峡的嫡传,住在这儿的却不仅仅是他而已。
为维护屋宇,洒扫庭除、灌溉草木等,还要服侍本脉传人的衣食起居,应风色有一位管事、一个厨子,六名仆妇与长工;早前还有两名婢子叫茗荷池月,其时茗荷十八,池月十九,都是幼年被卖上山来,专责照顾身体日衰的韦太师叔,老人死后就跟在他身边,十分亲近。
风云峡无师长坐镇,为免风言风语,应风色领了青鳞绶不久,召来荷月二婢细说分明,给了笔极丰厚的奁资打发回乡。
双姝哭着不答应,最后是福伯一拍桌顶,难得发怒:“你们就不怕败坏公子爷的名声么,存什么非分之想!”两人才没敢再说。
应风色其实很舍不得。倒非贪恋美色,那会儿他才刚满十五,压根没想过那种事,只记着她们对自己的好,感觉像与家人分离,心中甚是难过。
但他将来是要做宫主的,注定不婚无子,流连花丛无有好处。
万一婢子有身,必得下山打胎,经常就这么母子双亡不说,少不得还要留下话柄,日后竞逐大位时给人扒粪污面,徒增难堪而已。
后来才知茗荷悬梁自尽了,甚至没回家乡,在山下的客栈盘桓大半个月,镇日在牌楼前徘徊不去,游魂也似,后来仍想不开,悄无声息地结束了花样年华。
福伯接到通知,下山为她料理后事,回来后人就变了。
不是什么剧烈激进的变化,就是过往总不自觉笑成眯眯眼的那个部分坏掉了一般,常对着空荡荡的屋舍发呆,好像能听着残留在角落里的银铃笑语,久久难以自拔。
应风色没法安慰老人。
他不知怎么开口,也无法判断茗荷是因为福伯的话才自尽,抑或怯见故里家人,不想离开早已生根的龙庭山……但她们终归得走的。
困于自责的老人令少年难以依靠,逃避加上失望,就这样错过了说开的时机,现今也没必要说了。
病倒的不止应风色一个,诸脉皆有灾情,一度传是瘟疫。他昏迷的第二日魏无音便匆匆赶回,长老合议在地宫里吵了一天,最后查出是”留魂香“惹祸。
“留魂香“之名挺吓人,就是种长得像、吃起来也像鸡油蕈的菌菇,香味极浓郁,质嫩而口感细滑,格外吸油;与精炼的鸡汁鸡油同烹,吸饱油汁的蕈伞入口迸鲜,能教人把舌头给吞下去,是颇为金贵的食材。
山上厨子同人买了一批北方来的留魂香干货,却不知在乌城山以北产的这种香蕈,入秋后会发生变化,形成剧毒,如冬虫夏草冬日为虫,夏季成草,质性截然两样,南方出产的却不会。
故北关留魂香蕈最迟八月前必得采收,晒干贩卖,工法好的价钱未必便低于鲜蕈,毕竟滋味经日晒浓缩,更能吸汤,料理方面更有发挥的余地。
这批留魂香个头肥大,香气极浓,偏生价格甚平,龙庭山上几处名刹的香积厨用了无不大受好评,也没出什么事情,最后连奇宫各脉的后厨采办都掺和进来,不料里头竟混进毒蕈,酿成巨灾。
九脉算起来有几十人受害,死的五个全是年轻人,夏阳渊的林泉色,拏空坪的李锡色、冯钘色赫然在列;薛胜色在飞雨峰后山的一处断崖下,被发现摔得颅碎肢折,惨不忍睹,推测是在山道上毒发昏沉,失足所致。
唐奇色行踪不明,这位旧日次席长年沉溺杯中物,拿了钱就下山喝酒,传言说他嗜赌爱嫖,经常在山下闹事,盖因大长老一味容忍,旁人也不好说什么,消失十天半个月都不算事,闹出事情便知下落,故无人找寻。
夏阳渊的另一位师弟关洛色正放省亲假,老家位于陶夷郡北方,距离甚远,算上往返大概一个月后才回,问不出更多消息。
蔚佳色在当中最特别,他非是放假省亲,而是直接被家族召回,走得很急,来使同惊震谷闹得不甚愉快,缘由却无从知悉。
应风色终于明白高轩色在降界中何以如此失态,对他来说,蔚师弟本是失而复得,谁知又在眼前失去。
从降界生还的使者们,病得又比其他人更重,应风色算起身早的了,在榻上躺足三天,才终于踩落实地,整个人轻飘飘的,果有再世还阳之感。
魏无音知他清醒,翌日即走,”避不见面“这事上师徒俩倒有默契。福伯这几日于诸脉间打探消息,看是察觉有异的,但终究没问出口,只如实回禀,再依言而去。
应风色机警地未探活人——只消没上罹难名单,便知他们活得好好的——福伯就算生疑,倒不致烂嚼舌根,倒是他几番试探,暗示福伯有无看见一柄怪剑或奇怪的穿绳布料,老人一径摇头。
(可恶,被那狡诈的绵羊头诓了么?果然是江湖郎中!)
理性上可说是想当然尔的结果,应风色却掩失望。那可是半痴剑啊!
直到福至心灵,目光停驻在角落一只带锁橱柜上。
身为星拱之月、多年来风云峡唯一的主人,应风色的私人物品始终收藏在如此显眼处。
母亲打的锁片、陶夷家中捎来的财宝,叔叔的字帖、坛舍府库中搜出的武功典籍,还有几本风月图册……差不多就是青年的全副家当,一眼便能看完。
应风色强支病体,从抽屉中取出钥匙——没错,有钱人的思路就这样朴实无华且枯燥——扶着桌椅屏风打开柜门,中间层架的显眼处,叠着两只扁狭锦匣,匣下压了部黄旧的薄册。
《还魂拳谱》。同降界所见一模一样,看来是没法验证有无”越界之眼“的区别了,但长七寸宽四寸、厚不过两寸的锦匣肯定装不了剑,他怀着既忐忑又狐疑的心情,打开最上层那只。
锦匣的红绒内衬里,真嵌着半痴剑——长五寸,通体淡青,以硬玉雕成的小剑维妙维肖,取材自未展羽刃的型态,细节无不纤毫毕现,精致非凡。
这是个恶劣但极其用心的玩笑,可惜应风色笑不出来。
内心涌现的巨大失落无疑令青年倍感挫折,他甚至希望能回到降界神域,多握握那柄属于自己的、手感无与伦比的罕世神兵,才能深刻地记住拥有的感觉。
“……可恶!”回过神时锦匣已脱手掷出,摔落地面,发出巨大的声响。
左厢传出披衣下床、推门而出的声音,烛光一路摇至,开门时福伯见得室内景况,讶色一现而隐,却只躬身颔首,弯腰拾起地上的锦匣玉剑放在床头,哑声道:“老奴扶公子爷回榻罢,再歇会儿。”
“不用,我自己来。“应风色扶柜而立,并未动作。他不想让下人看见自己步履蹒跚的模样,即使是福伯也一样。”我好得差不多了,毋须贴身照看,明儿回自个儿院里睡吧,这几日辛苦你啦。”
福伯迟疑了一下,终究没说什么,躬身道:“老奴明白。老奴告退。”
茗荷池月下山后,他院里就没有别人了,反正也不需要服侍,身边没有眼目窥看,对于成长中的少年毋宁更自由也更方便,梦遗更衣不致难堪,自渎毋须提心吊胆。
应风色听老人褪鞋上榻的窸窣声落,刻意再等上十数息,至低沉的鼾声漫荡迤逦,才慢慢扶着墙上了门闩,倚坐于榻。
昏迷几日,靠下人一点一点喂着鸡汤肉粥,体力甚衰,便有内功底子,怕还要一阵才能次第恢复。
软弱的投掷未能摔坏玉剑,但锦匣发出的空洞巨响就很有问题了。
应风色检视匣子,果然发现了夹层,撬得几下打开内衬,取出卷成一束的丝绢来。
那绢子薄如蝉翼,几可透光,材质却颇为坚韧,应风色总觉与紫苑宝衣有些类似,只是更轻更薄,或许就是经纬罗织数更少些的雪蛛绢布。
丝绢全展近九尺,一面写满蝇头小楷,应风色就着烛光细看,绢头题为《风雷一炁》,开宗明义曰:“圣人云:“欲链真仙日晶魂,先觅玄源造化根,后立坎离为匹偶,始交情性合乾坤。’故性命同源,不可偏废,合修并进,神炁风雷。”其下教人锻炼心魂,巩固元神,是为性功;而练气修体,合于大道,则为命功,竟是部内功心法,字迹娟秀一丝不苟,应是出自女子手笔。
粗粗看了几段,很难判断高明与否,但于命功的修练上,通篇所言俱是二元对立的转换,如刚与柔、动与静、阴与阳,法门时而软功内壮,时而硬功外壮,变化剧烈到有点随兴任意之感,就像说着说着忽然使起小性子来,完全不讲道理。
专练阴柔劲力兼有阳刚之威的武功不是没有,练法就没这么糊烂随便的。
这是练武呢,一没弄好是要伤筋折骨赔上性命的,你以为是逛街买衣服?
——“你”?
越看越恼火的青年,被心底本能涌上的吐槽吓了一跳,这种强烈的与异性对话之感绝非是因为绢秀的字迹,他想起在哪里听过类似的事。
史上最高累积点数和守关者击杀数的纪录保持人,最年轻的女性天裂级使者,应䶮和玄象生命之中最重要的女人,涿野明氏的么女,容颜倾世、惊才绝艳的明九钰明姑娘!
这如果就是那份改变历史的“绢书”的话,那么这门《风雷一炁》,就是总结了《金甲旋龙斩》和《紫煌鳞羽缠》两大绝学的究极之解,是被明九钰藏起来的真本!
应风色浑身颤抖,若非病愈的身体虚乏无力,直想跳起来欢呼三声,捧绢书绕整座风云峡跑上几圈。
但羽羊神不会这么好心,平白送出如此大礼,除非锦匣藏书一事祂并不知晓。
或者……丝绢上有什么机关,可能天亮之后会忽然消失,又或“越世之眼”限阅三次,尔后便再也看不见之类,总之就是先把人拱上高峰,突然又狠狠摔落的可怕算计。
那绵羊头就是这般贱格!
想起得而复失的半痴剑,应风色心还在滴血,强支病体坐到桌前,摊纸研墨,就着灯烛,开始誊写明姑娘创制的《风雷一炁》,除留下缮本,以防羽羊神使什么黑手,更为一字不漏将内容牢牢记在脑海里。
全书洋洋洒洒九千余言,直抄到福伯敲门,发现天已大亮,让福伯把早膳搁在廊间,之后的餐食饮水都用食盒贮装放在外头,无事休得打扰。
过往他闭关练武经常如此,老人不以为怪,应声而去。
应风色将抄妥的部份摊晾待干,绢书收回夹层,锁入橱柜。
第二只锦匣内,装的是块打了环钉的雪蛛布,材质与紫苑衣一模一样,虽附系绳,但小到只能缚于掌心,恶质的程度毫不亚于半痴剑的硬玉模型。
青年在心里诅咒了羽羊神不下五万遍,祝他终年羊乳不断、胎胎九羊之类,这才收拾心情,好生研读抄本。
“体虚不练功”是常识,内息既分文武,适合疗伤养生的文气和追求杀伤力的武气大不相同,体衰之时硬练武气,将在功体留下各种难以预料的隐患,如过湿的泥坯不利塑形,两者是一样的道理。
应风色索性先跳过疑窦丛生的内功,只看修练心识的部分,这一看便看出况味来。
与其说奇宫是修习性功的大行家,不如说天下五道正邪门派之中,能像指剑奇宫把心识独立出来修练,如同内功外功等科门的,直是凤毛麟角。
故《风雷一炁》开篇论心神和肉身合修,立即攫取应风色的眼球。
内功无论何门何派,大抵不脱“练精化气”、“练气化神”、“练神还虚”,乃至“还虚合道”四境,差异就在“神”之一字的解释上。
多数门派解作神而明之,是指技艺精湛到了某种境界,会以常理难解的形式显现,或特别快、特别准,力量之强难以抵挡,又或金刚不坏入圣超凡,不一而足。
但明九钰以为这种说法太过虚渺,无法得到一致的通说,而大道应是有准的。
她将“神”字解作心识,“练气化神”不代表神的位阶高过了气,而是须将两者互相化用,合而为一,心识与筋骨、真气相结合,现实界对身体的限制将逐渐消弭,快到能如想像之快,强到能如想像之强;心才是自身能力的疆界,而非寰宇六合。
跨越这一步,而后“练神还虚”——只消打开心的限制,就再没什么能阻止你了。
所以性功——也就是心识——的修练占据了一半以上的篇幅,甚至还多过内功法门。
她将心识修练明确分作七个阶段,以七魄来命名,起于〈臭肺〉,终于〈尸狗〉,比起内功篇章的随兴,这部分倒是严谨得多。
九钰姑娘不好空论,各派教人冥想趺坐、尤其道门心诀常见的“一点灵光”、“复还太虚”等全未出现,〈臭肺篇〉只教五种方法:先生贪恋而断贪,复生恶念而断恶,后生执着而去执,三者循环;修练者以细数呼吸之法沉入心识,每三百六十息成一周天,初时吸吐间兀自能察,遁入念想之后,呼吸与意识将次第分离,迷离境中的时间流速或与现实不同,然而毋须恐惧,以啸法阻断纷至沓来的心魔,即可脱出。
应风色反复研读,忽觉〈臭肺篇〉五法与佛门声闻乘的“五停心观”近似,断贪为不净观,断恶为慈悲观,断执为因我观,以呼吸吐纳控制入神则为数息观;而阻断心魔的破疑啸法,当是借鉴念佛观而来。
鳞族历经三宗共治时期,保存了大量的佛门典籍,所知与今时杂入当地土人信仰的东海佛教未可同日而语,应风色在风云峡和通天阁都翻过声闻乘的经书,当中并不包括武典。
自声闻乘最负盛名的“大日莲宗”消亡后,江湖上已罕见其武学。
莫非九钰姑娘同莲宗有什么牵连?
可惜绢书没有更多线索,此疑终是不了了之。
〈臭肺篇〉步骤清晰,理路分明,简直像是食单菜谱,甚引庖人技痒。
横竖应风色也在调养身体,练不了内外武功,于是按图索骥,体会下别派的心识之术。
夺舍大法教人入虚静、返照空明,万一失败,大不了坐着睡上一觉,但〈臭肺篇〉可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生贪、生恶、生执着,按应风色的理解,就是回想人生污点,什么恶心挑什么来。
他试了整晚,却无法如绢上所述,“沉”入某个回放似的迷离境中,只觉无比烦躁,参杂着满满的自我嫌恶,开始怀疑《风雷一炁》又是另一个精心但恶劣至极的玩笑,恍惚间沉沉睡去,忽来到血海滔天的通天壁。
惨变后头几年,他夜夜都梦到那一日的可怕情景,总是从恶梦中流泪吓醒。
就是从那时候起,荷月二婢在福伯的默许下搬进院里,茗荷甚至有段时间就睡在他房里,主仆仅有一屏相隔。
应风色曾于寐惊后,趴在她俩绵软温香的奶脯间嚎啕大哭,也曾因恶梦失禁,尿湿了被褥底衣,命少女们万勿声张,忍着夜寒刺骨在井边搓洗……有那么一瞬,在做成送二婢返乡的决定后,少年忽有松了口气的解脱之感,再没人知道领青鳞绶的长老有过那样不堪的过往,她们远在与龙庭山恍若两个世界的家乡重新展开另一段人生,跟投胎没甚两样,前尘往事一笔勾消,落得干干净净。
而如此肖真的通天壁,是多年以来所仅见。
乌红、臭气、哀嚎,还有唐奇色那撕心裂肺的惨叫……清晰得像是重临现场,应风色感觉自己失禁了,然后才意识到这绝对是梦,却怎么也醒不过来;千钧一发之际,忽想起还有啸法。
青年从浇灌全身的如潮血瀑中睁眼,惨状忽尔消散,只余一身冷汗。
(有用……这真的有用……不是……不是骗人的……)
他迷上了遨游幻境、似假还真的感觉。
幻境渐渐脱离现实:他看过茗荷悬梁的情景,看着原本楚楚动人的美丽少女容颜枯藁,仿佛被汲走了生气,睁着流泪的空洞眼眸把尖颔塞进衣带环间;看过奚长老和岁无多在渔阳抵御阴人;看过叔叔重回阳山,再掌龙庭;他甚至看过鹿希色裸裎娇躯,如春宫图中所描绘,在身下婉转娇啼,温顺得像头娇柔的兔子……
依靠〈臭肺篇〉五法,短短七天内他已练到想进即进,想出即出,那种心念一动顷刻万里、所历无不真实已极的感觉令他深深着迷,应风色废寝忘食修习着,仿佛怎么也停不下来的自渎。
高亢剧烈的精神活动,终于冲破虚无飘渺的识界,直接对肉身造成反噬。
应风色正沉迷于女郎的艳姿中不可自拔,心神与躯体的链接像被什么中断,从虚境中陡被抛回,五感兀自倒错,却觉全身经脉阻滞,有团火焰在下腹间灼烧般疼痛,而无法动弹,遑论发出声音;胯间阳物硬如握拳婴臂,狰狞昂起,似欲撑破裤布,又像胀满的鲜血被掐挤至极,即将爆开。
(……走火入魔!)
应风色没想过自己会这样死去,更不敢想像这般难堪死状,会受到何等耻笑,以致没留意有人推开门扉来到身畔,回过神时,腰带衫袍俱被解开,来人撕开了他的裤头,一把捋住滚烫弯翘的怒龙,凉滑细腻的肤触熨贴着青筋暴起的杵茎,几难满握;应风色痛苦稍减,忽然嗅到熟悉的发香。
“……你可真会玩啊,麒麟儿。”
嫩薄的樱唇微微扬起一边,角度虽小,嘴角却有个细折子,讥诮涌溢之余,又予人精巧绝伦之感。
鹿……鹿希色?
他一下无法判定是幻是真,杵茎上的快感却再真实也不过,女郎微凉的腻润掌心滑如敷粉,套弄时若即若离,刮得菇伞般怒张的龟头外缘酥麻已极,快美在转瞬间飞快积累。
应风色越来越相信这不是幻境,忍着酸爽勉力凝眸,眼前的女郎却与降界时一身劲装不同:梳着高髻,簪着玉钗,湖色对襟上襦露出小半截绀青色的绸缎诃子,绣滚的银边儿起伏剧烈,裹着饱满莹白的双峰。
近距离一瞧,发现她鼻尖和乳肌沁着密汗,小脸蛋儿红扑扑的,那种想笑偏又莫可奈何的模样,是幻境里怎么也想像不出的风情,青年再难忍耐,喘着粗息虎吼一声,浓精喷薄而出。
鹿希色猝不及防,总算及时一仰,让过粉面圆颐,势头猛烈的阳精在两人间划出一道乳色长泉,溅了女郎的奶脯和绀青诃子上一片,厚浆稠挂滴之不落。
鹿希色低呼道:“好烫!怎地……怎地这般烫人?”伸出指尖,半试探、半好奇地抵着乳上白渍,轻轻画圆,甚至忘了松开怒龙杵。
应风色射得头晕眼花,精浆似有无数颗粒,刮得马眼又疼又美,身子忽又能动了。
见女郎拈着纤纤指尖、拉开一道垂坠液丝,蹙眉侧颈的模样难绘难描,阳物未见消软,欲火又熊熊燃起,猛将她扑倒在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