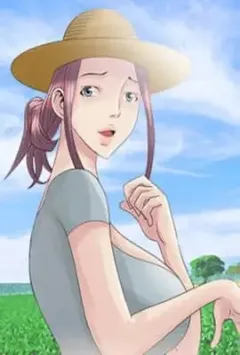被抬离无乘庵不久,应风色便跌入了虚境中。
“韩雪色”毫无疑问是他现时的绝佳护身符,龙方飓色若能将韩小子带回龙庭山,知止观必会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和相应的地位。
死掉的毛族宫主换不了好奖品。
被龙方引为心腹的六名九渊使者里,他只认出了其中一个叫谭剑英的飞雨峰弟子。
透过“开枝散叶”引上龙庭山之人,部分不会冠以奇宫的字辈排行,通常是外派嫡裔乃至继承人,就是来过个水罢了。
谭剑英是嵧西“神功拳”掌门人谭元府之子,在谭氏五子中虽居长,却是谭元府长女的乳母所生。
此事实说不上光彩,谭家大房奶奶约莫被逼得急了,居然诞下二子,连二房和小妾也都各自得男,谭剑英在谭家的地位顿时尴尬起来,才被父亲送上龙庭山,表面上是结盟通好的象征,其实是堂堂嵧西一霸的“绣狮”谭元府,也顶不住妻妾联手的压力。
谭剑英根骨不差,家传《神功拳》练得颇有架式,经飞雨峰几位长老点拨,连内功都进步神速。
当日在玄光道院接过匕首、满院子追着韩雪色跑,最终给泼得一身黄白秽物的倒楣鬼,正是这位谭家大公子。
他上山三年有余,应风色在大比上见过他与一帮色字辈打得有来有去,对他的身手和声音有点印象,这才认了出来,然而露出鬼面眼洞的那双狞恶眸光,却令应风色异常陌生。
不说他在庵前无视满地血污尸骸,黏腻的视线净往莫婷身上巡梭,不住伸舌舐唇,就差没滴落馋涎;离庵后这一路蜿蜒难行间,只有他毫不掩饰频频回头,盯着鹿希色瞧,虽说品味与自己堪称一致,但应风色半点也高兴不起来。
比起临阵背叛,他更想不通鹿希色为什么要跟过来。
鹿希色从一开始就是冰无叶的卧底,一旦任务完成,又迫不及待离开养育她、传授她武艺的冰无叶。
这种反复无常根源于凉薄的天性,无论背叛谁,又或为了什么理由背叛,应风色都不会感到意外。
但龙方飓色这厢有七名四肢俱全、身上无伤的奇宫弟子,就算全是开枝散叶的外姓人,光靠数量优势就能拿下女郎。
她凭什么觉得能全身而退?这种愚蠢到不讲道理的自信,简直快把应风色给逼疯。
他越不敢想像七名饿狼般的男子一拥而上,将她的衣甲撕得粉碎,残暴地淫辱女郎的画面,想像力便越发鲜活起来。
令他难以承受的除了焦急恐惧,还有那毫无来由的心痛心慌——为何会如此?
对背叛者而言,这样的下场岂非罪有应得?
有甚好舍不得的?
“……因为你毕竟是个好人。”冒牌货叔叔抢在他几欲跳起大喊“快逃”之前,将应风色拉进虚境里的田圃小院,谄笑到他拳头都不自觉硬起。
“是不是想听我这样说?别客气啊,再说三遍可好?你是好人,你是好人,你是好人……还有哪里需要加强的?”
“滚开啦。”他没好气道,应无用那身剃头担子的行头化烟散去,又恢复成原本羽衣赤足的飘逸造型,只廊下多了具镌满经络穴位的铜人立像,虽是罗汉般的光头裸身,面孔却是韩雪色的模样。
应风色一凛:“详细的损害报告出来了?”
“先说好消息。
三色龙漦的逸失已经计算出来,我只抓个概数,你心里有底就行。”应无用道:“龙漦之用乃三者比例上的分配,虽有主次之别,却没有哪种是可以独立运作的。
你使用青龙漦加固莫执一的手腕,造成八成的青龙漦离体,连带损失约莫五成的白龙漦,以及两成的赤龙漦。”
“这样……还能再使用‘无界心流’么?”
“发动倒不成问题。”应无用神情严肃。
“但,仅有一半分量的白龙漦,调节的机能不可能不受影响,经过我无数次的模拟推演,大概抓原本三到五成的时间是比较安全的,两次发动间的间隔则要延长至少一倍。
“比较麻烦的是青龙漦,在‘无界心流’发动时负责保护你的心脉,以免加速数倍的血行鼓爆了经络脏腑。
剩余的两成青龙漦将无法提供足够的防护,就算韩家小子的身体壮实得像头牲口,也末必扛得住。“而这居然还算是好消息。
应风色做好了心理准备,蹙眉道:“那坏消息呢?”
“杜妆怜打在韩小子心口的那一掌并不是《小阁藏春手》,是水月一脉不曾出现过的怪异武学;与其说是掌劲,更像是一道剑气,理应在中招时便破体而出,在韩小子的胸膛开出枚血洞。
这掌没让韩雪色死得苦状万分,恐怕杜妆怜自己也觉得奇怪。
“那会儿我差点被关机重开,顾不上应对,三色龙漦自行发动,但残剩的青龙漦只能勉强护住你的心脏,不被剑气洞穿,赤龙漦的‘发散’之能裹住了剑气却无法化消,反而让剑气不断在其中反复激荡,越发凝练压缩。
“此际全靠白龙漦引血髓之气调节,勉强维持住平衡;一旦血髓之气耗尽,又或剑气凝聚到足以突破赤龙漦的禁锢——”
“我的……韩雪色的胸口便会炸开一枚血洞?”这消息简直是糟透了。
“我料数日内便至临界,毕竟你修习《冥王十狱变》的时日还不够长,期间继续修炼血髓之气或可迁延些个,但也拖不了太久。“应无用正色道:“你须尽快做个决断。“应风色知他指的是从莫执一身上回收龙漦,但这会儿已不知无乘庵众姝逃往何处,更遑论脱出龙方的掌握。
“有个糟糕的权宜之计,你姑且听之。“应无用道:“找高手运功为你护住心脉,看你是要牺牲哪只手脚,以青龙漦做成一条引导剑气的通道,从手心或脚心释出。
如此一来,虽不免残废,总比爆体而亡好。“奇宫最不缺的就是高手,或许被龙方带回山上,比无头苍蝇似的找莫执一回收龙漦靠谱。
应风色灵机一动:“若由内功深湛之人,以真气为我化去剑气呢?”异种真气入体,在消除剑气的同时,也会对经脉脏腑造成伤害,毕竟增损相歧,一气不能两全。
但应风色有三色龙漦护体,说白了就是同那道杀人剑气比命长,谁扛得住异种真气的消损,谁就能笑到最后。
以目前赤龙漦犹能裹住杜妆怜的剑气来看,这厢的赢面是要大些。
“也可行。“应无用答得干脆。
“只是此法须耗大量内功,韩小子身负三色龙漦这点也不容易交待清楚。
要各脉长老捐输功力拯救毛族宫主,这真得你叔叔才能办到。
不妨召魏无音上山,让他想想办法。“应风色满心不愿,也明白嘴硬只会害了自己,随口道:“我进来久了,出去透透气,免得龙方起疑。“正欲抽离,冒牌货叔叔脸色忽变,一把拉住他的神识:“慢!这会儿你别醒着,外头……有些不对劲!”外头……不对劲?这不是更该清醒才能应付么?一股异样的波动荡进虚境里,透体而过的瞬间,应风色只觉浑身战栗,难以相对,是会双膝一软、不由自主跪地瘫软的程度,仿佛鬼神倏忽降临,凡人根本无法抵挡。
“这、这是何……何人所发……”他立刻就明白,是冒牌货叔叔将外界的感应传入虚境,这比任何言语都更有说服力。
以”韩雪色“贫弱的内力修为,断难察觉此等高人,但识海内的应无用能分析、统整外在的一切感知,丝毫无漏,与其说察觉异状,更像在海量的情报分析之下,异状自然而然浮现其貌,无所遁形。
“我无法让你‘看见’外头的样子。“应无用罕见地露出凝肃之色,但原因不难想像。
应风色的意识遁入虚境,韩雪色形同昏迷,即使能被动接收听觉、触觉等,但视觉决计无法运作如清醒时。
冒牌货叔叔必是利用类似灵犀感知之类,更虚无难控的非常途径,耗用的资源更多,负担更重。
这对初初恢复的识海来说,毋宁是雪上加霜。
况且调控龙漦压制剑气,也不是轻松活儿,实在匀不出手来,让应风色待在虚境里舒服看戏——还有一个办法。
应风色心念微动,冒牌货叔叔便已获悉他的想法,意识中并无强烈的抵抗,该是允可之意。
应风色深吸一口气,想像身体变得极轻极透,似能随风飞去,无限延长的意识渐渐升起,田圃小院在脚下变得越来越小,只余一线与识海相连,就这么遁出天灵冉冉上升,如烟雾般飘浮在茅屋的梁椽间。
(成功了!)他看见顾挽松攫住龙方之面,拖近身前呲牙威慑,看见伤重的台丞副贰冷不防地出手,捏住龙方胯下之物,鸟爪般的冷硬枯掌绷起青筋,光瞧便觉痛极;看见龙方扶墙丁步,勉力开门说话;看见阖上门扉的一瞬间,忽然出现在门后角落里的无叶和尚——等一下。
魂灵态的感知力是足以超越现实之限的,就像他一凝眸,就能看见挟着鹿希色发足狂奔的冰无叶。
这种感知固然有其极限,但在范围之内,时间、距离等现世之物,对灵体来说其实没什么意义。
冒牌货叔叔甚至说过,等运用得更加精熟,或能预知稍后将发生的事,哪怕只提前个一二息,在战斗中也是极其巨大的优势。
那为什么……他瞧不见是谁,又是如何带来的无叶和尚?惊魂末甫,蓦听顾挽松惨叫跌落,炕沿却多了一名白袜黑履的初老文士,漫声吟道:“谁遣聪明好颜色,事须安置入深笼。
你都知道让杜妆怜赶紧躲去,难道没想过我早已在附近瞧着你,只是尚末现身而已么?挽松啊挽松,作茧自缚,莫甚于此啊。“应风色身魂剧震,差点震脱了与识海相连的一缕牵系,心底一片混乱。
这个身影和声音他无比熟悉,对此人的无端挑衅几乎送掉他的命,所幸在应无用的提醒下扭转局势,得以安然脱身——若说先前老人是以气势震慑,让应风色意识到挑衅他是何其危险的事,此际超越魂灵所感、无声无息现身屋里的藏林先生,其武功之高,身法之难以想像,算是彻底颠覆了应风色的认知。
他为自己的愚蠢狂妄感到羞愧。
问题是:藏林先生与龙方飓色,是怎么勾串在一起的?难道今夜之事,竟是针对顾挽松所设的一个局?这个”故旧重逢“的场景,二十年来在顾挽松心里试演了无数次,只是他万万想不到,先生居然会纡尊降贵,用上龙方飓色这等微不足道的小棋子。
不对。
若非先生拉拔,当年他就只是个混迹于北方的小门派之间,重复着拜师杀师、夺宝冒名的小人物,血甲之传的擘画图谋再怎么宏大,于他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半点也不现实。
是先生发掘了他,教他读经学文,变化气质,最终为他换上了这件平川顾氏的身皮,送进碧蟾王朝澹台氏的朝廷里。
恁谁也想不到,堂堂埋皇剑冢的台丞副贰,望重朝野学冠文武的”天笔点谶“,竟是出身马戏班子、在驯兽鞭子和铁笼槛栏间长大的孤儿罢?这么说来,先生确是偏爱兵卒之流的弱棋的。
执”赤土九逆修“之牛耳、堪称血统纯正的血甲之传吕圻三与自己相争的那会儿,先生最终是信了他的说法,亲手埋葬当世血甲门最强大的土字一系,任由他处置吕圻三遗留下来的研究材料。
但吕圻三是死有余辜,不算太冤,顾挽松只是告发了他而已,并非嫁祸栽赃。
先生平生末有敌人——隐于暗处、事事假手他人者,岂能招至怨恨?谁都不知背后有这么个人在左牵右引,生出如此事端。
先生做这些事时,一贯是没有什么情绪的,如弈棋品茗般,行止若已自带风雅,何须引入喜怒好恶,徒乱心耳?
顾挽松对先生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也是原因之一。
唯有那次,先生是彻彻底底被惹怒了。
奉玄圣教那帮蠢材妄测天机,不知用了什么法子召唤神军,据先生说诸沃之野生机尽绝,原本盘据那片寒地的蛮人被吓得理智全失,遂疯狂南侵,沿途烧杀搜刮以为血祭,祈求上苍收回那人所难敌的恐怖魔物。
澹台家的朽烂朝廷经不起折腾,王脉断绝,五道无主,天下从此陷入动荡。
神军倏忽而来,又倏忽而去,蛮人复归诸沃之野,连奉玄圣教也不知所之,二十多年间不露声息,仿佛凭空消失了似的。
先生对奉玄教的愚行怒不可遏,更令人恼恨的是连个兴师问罪的对象也无,纵以凌云三才之智、五极天峰之能,莫说奉玄圣教的总坛崇武行殿杳如黄鹤,想抓个落单的教徒来拷问亦不可得,那时顾挽松才知道:原来先生不但是有脾气的,且狂怒起来竟是如此骇人。
吕圻三不知何故与奉玄教搭上线,恐怕也是过往的因缘,很难说是真有贰心,或只是呈报慢了,被顾挽松先参一本,安上密谋通敌的罪名。
土字一系在栖亡谷的试验基地没留下半个活口,估计就算吕圻三能预见危险,也料不到正替先生研制刀尸的自己,会遭遇杀猪屠狗般的对待,多少是被”鼎鼐之重不忧谗“的自以为是害了性命。
先生名列”凌云三才“,是天下间公认最最聪明的三位奇人之一,顾挽松明白不可能蒙骗他一世,待先生怒火平息,理智恢复,会明白吕圻三押上血甲门土字一系的身家,为先生投入妖刀祸世的阴谋擘画之中,双方利害一致,没有半途变节的道理;也会知道顾挽松是为了独占莫执一,才利用了他对奉玄圣教那无处宣泄的怒火。
廿年来,顾挽松一直在等这东窗事发的一天。
为了这天他不惜大张旗鼓搞出龙皇降界的荒唐游戏,唯恐不够高调,又让马长声、乔归泉去劫两湖水军大营的饷,把镇东将军府也拖进浑水泥坑。
“先生……先生!”他蜷身匍匐,以额叩地,撞得额头渗血,在夯实的硬土地面砸出一朵朵枣色的花印子,颤声道:“小人……小人该死!小人……小人有罪!请先生高抬贵手,饶……饶了小人一回罢。“藏林先生掸了掸膝腿,神色微愠:“你好歹也是两朝大吏,正道七大门派的魁首之一,这般模样像什么话?看来,这些年是我太纵容你啦。
感时惟责己,在道非怨天!自己说罢,你究竟所犯何事,莫教我冤枉了你。“顾挽松听他颇有见责意,反倒吃了颗定心丸,就怕他温言笑语,那才是动了杀心的意思,赶紧打蛇随棍上,缩颈嚅嗫道:“小人自……自把自为,以先生……先生之名使唤杜妆怜、邵咸尊等,又将主人交付的本门珍宝任意挥霍,小人该死,小人罪该万死!”说着呜咽起来,伏地颤抖不休,丑态毕露。
藏林先生点了点头,忽然起身踱至无叶和尚的尸身畔,右手五指屈成钩爪,袍袖翻飞间”噗“的一声插落无叶的头顶天灵盖,漫声吟道:“血解皮囊残骨肉,争似留神养吾身!”运劲一汲,原本魁悟壮硕的僧尸迸出若有似无的丝丝吸啜声,白惨的四肢躯干蓦地紧缩塌瘪,整个人仿佛小了一圈,风干橘皮似的肌肤表面浮露蚯蚓似的青筋,似乎只有经络没有缩水,故而突显出来。
初老文士的手腕轻旋,揭盅般提起无叶的脑壳儿,只见僧人之脑亦缩小大半,颅中颇有些空洞;浓粥也似微微冒腾的灰质皱折之间,嵌了枚殷红湿濡、活心般的浑圆肉球,约莫荔枝大小,正是先前龙方所说,聚浑身精华于一处的肉芝”血解留神“。
按说无叶和尚断气也有大半个时辰了,血冷身僵,体内绝不该有这般活生生、兀自卜卜跳动,表面布满经络血行的组织。
相较于这枚过分鲜活的肉球,尸身余处格外明显的凋萎蜷缩,益发令人怵目惊心。
顾挽松知上古儒门的《摘魂手》有此异能,但一来他练的是速成的版本,精于慑魂夺魄,而非尸解留神;纵使练得完整功法,以他的修为,也绝不能从已死的尸体上榨出如此丰沛的生元。
而吓人的还在后头。
“你天资聪颖,肯下苦功,也能练到这等境地。“藏林摘下血淋淋的的鲜红肉丹递去,龙方飓色俯身并掌,恭恭敬敬捧过。
文士运功一抖,随手将指掌间的鲜血蒸成血雾,被刮进屋里的山风吹散,踅回原处坐定,怡然道:“循屋后小径行出约莫三十丈,有一隐密洞窟,你按我所传心诀服丹化纳,一刻内尽力将丹内生元转为己用。
连云社诸人的尸体,我已并置于洞外的空地上;有了无叶僧的功力相赞,你可试着从庞白鹃的尸身上取丹。
其余诸人之丹,稍后我再为你拔取。
“(先生竟将《摘魂手》传给了龙方!)龙方飓色无视于顾挽松的诧异之色,躬身领命,退出茅屋前又道:“无乘庵那厢,需不需要晚辈先去一趟,免得走脱了言满霜等?
“藏林先生摆手道:“毋须费事,此际已追之不及。
怜清浅不是摆着好看的花瓶,便即追上,也有教你杀不下手的法子。
他会那么说,只是想支开你们罢了。“下巴朝顾挽松处抬去,微微一哼。
龙方遂不再多言,捧着肉丹倒退而出,脚步声迅速消失在夜风里。
藏林先生垂落视线,淡然道:“你故意提到邵咸尊,是想测试我让他知道了多少,会不会威胁到你的地位。
退万步想,万一他不知道,代表我不想或不该让他知道,如今他既已知晓,我就得做出处置。“然而那小子并不知道。
顾挽松心想。
先生现身于此,那么是谁在通知杜妆怜时做了手脚,已然不言自明——运古色虽末必听龙方的指示,若教海棠在床笫间咬耳朵,挑唆他将”言满霜身份可疑“一事提前泄漏给杜妆怜,说这样便能坏龙大方的事,运古色还不跑断腿脚?龙方飓色的城府在同龄人中堪称深沉,但不惟杜妆怜涉入妖刀阴谋,连青锋照掌门”文舞钧天“邵咸尊也是共犯,肯定大出这小子的意料。
顾挽松从龙方乍现倏隐的一抹诧异中,看出形势还是对自己有利的,可怜兮兮道:“小人这点心思,何时瞒得过先生?我……我就是条癞皮狗,没了主子看管,乐得上窜下跳,忘乎所以,把东西咬破咬烂耍着玩。
但玩耍再乐,总不及瞧见主人乐啊!
龙方是年轻,但说到忠心耿耿,小人这三十多年来只有先生一个天,就算老了,不中用了,也没一刻忘记过先生。
“藏林笑道:“所以我让你交待清楚,自己犯了什么错。
知过才能改,对不?
“他一笑顾挽松心底便发寒,敢情将龙方挤兑出去是着臭棋,先生没了顾忌,不吃这套虚文应付,暗忖:“罢了,说来说去就是吕圻三这条,今儿是躲不过啦。
“此事亦在沙盘推演内,一抹眼泪收了哭声,跪地垂首:“小人贪恋吕圻三他老婆的美色,弄大了婆娘的肚子,恰巧得知那厮勾串奉玄教的龟孙子,想让先生……替我治治他,免得东窗事发,吕圻三惊觉脑门上碧油油的,来找小人算账。
“那厮素来瞧小人不起,又得先生器重,小人……甚是妒忌。
要弄死了他,先生便只倚重我啦——差不多是这般龌龊心思,才告发了他。
但吕圻三与奉玄教之人结交是千真万确的事,若无这条,凭小人也栽不了他的赃。”藏林先生微微一笑。
顾挽松心底益发没谱,看来事隔二十余年,先生听到“奉玄教”三字仍是十二万分的不舒坦。
正自忐忑,忽听藏林先生接口:“吕圻三的死真要计较,你至多出了一成力,你便末告发他,我迟早是会知道的,结果相去不远。
况且你接替吕圻三之后,差使确实办得不错,堪抵土字一系上下。
我不会说吕圻三死得好,他得如此下场,我甚是惋惜,但这并不能算是你的过错。”顾挽松如聆仙乐,连滚带爬扑前,奋力攀住藏林膝头,如忠犬仰望主人般涕泪纵横:“呜呜……先生!”藏林先生抚他手背,状似安慰,缓缓低头凑近:“但有件事,我始终想不明白。”顾挽松愕然抬头。
“什……什么事?”
“证据。”
“证……证据?”
“对,证据。”藏林先生悠然道:“吕圻三咽气前,什么都招了:奉玄教是怎么同他接头、如何约定牵制于我,事后的酬谢等。
研究人身痛楚极限的人,末必比普通人更能忍受痛苦。
“他在崩溃之前,把一切能想到的恶毒字眼都骂完了,我才知他心里竟有忒多不满,血甲门的志业在他来看有多么伟大,乃至屈居人下,是何等负重忍辱,万般无奈。
“我当时太生气了,挽松,我是真赏识他。
直到栖亡谷内再无一名活人,我才想到忘了问他一件事。”初老文士盯着他,目光似欲攫人。
“像‘幽泉鬼医’吕圻三这种人,是无法靠言语说服的。
当然,能将一头神军缚至面前,的确胜过千言万语,但奉玄教与他勾结,远在召唤神军之前,便有独孤弋、武登庸押阵,独孤阀也没能活捉过神军。
奉玄教诸子庸碌,我料无此能耐。
“吕圻三肯定明白背叛我的风险,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又或拿到什么证据,才促使他做出如此决定?我搜遍栖亡谷,没找到这个关键之物,只能认为是被人顺走了。“顾挽松脸色微变,该不该抽手——明知是没用的——只在脑中犹豫了一霎,喀喇数响,伴随撕心裂肺的剧痛,右掌已被藏林先生捏成一团,不比一只女童抛玩的五彩沙包大上多少。
“啊————!”顾挽松整个人几乎蜷作一侧,很难判断是用力过猛或痉挛,惨叫声意外地低沉沙哑,宛如垂死的野兽嘶吼咆啸,与装乖求饶时的尖亢判若两人。
或许这才最接近真正的他也说不定。
“我讨厌苦刑折磨,挽松,你是知道的。
我和你们不一样。“藏林凑近他冷汗如雨的白惨额面,柔声道:“我太生气了。
这些年里我窥视过你无数次,料想至少该拿出来瞧几回,取战利品不就为了这个?
但你一次都不曾拿出过类似的物事,让我几乎以为:原来你一直知道我在瞧你。
这也极令人恼火。“若不明白找的是什么的话,又如何能知找到了,或找不到?所以,你不确定能否从尸身上搜出此物,这才留我一命么?这真是太讽刺了。
顾挽松面孔扭曲汗如雨下,竭力忍住冷笑的冲动,旋即又来的另一阵痛楚令他眼前煞白,几乎晕死过去;回神依稀见得,文士的一只鞋下血肉模糊,间或露出白惨惨的碎骨和粉筋一类。
那被踏得摊平汩溢的,竟是自己的左脚脚掌。
“我需要你亲手拿将出来,挽松。
这只要拇、食二指便能办到,但你还能留住你的右手。“藏林先生循循善诱,仿佛瞧的是舞雩归咏的六七童子,头顶晚霞,徜徉于水风之间。
顾挽松是拷掠折磨的大行家,痛楚几时能令他崩溃不好说,但从逐渐模糊的视线和意识,及剧烈跳动后又迅速沉落的心搏来看,他命征渐去,再拷问下去绝对是死路一条。
先生虽然绝顶聪明,但毕竟也是个人,且没有钻研此道的嗜好,盛怒之下是有可能弄死人的,吕圻三便是血淋淋的例子。
“我……拿……在……别……杀……”眼已不能视物,顾挽松探手入怀,在里衣腰际解下一只绣银的绯锦鱼形囊。
“银鱼袋?”藏林先生哑然失笑。
“你从吕圻三处顺走的是鱼符还是官印?”青鹿朝时,京官上朝须佩鱼符,以丝囊贮之,三品以上是绣金紫囊,称金紫鱼袋,五品以上则是绣银绯囊,也管叫银鱼袋。
金貔朝取消了鱼符的制度,到碧蟾朝才又恢复,白马王朝的典章制度多因袭前朝,但入朝早已改成持笏核名,鱼符鱼袋不过装饰而已。
剑冢的正副台丞虽非京官,因身份特殊,也获赐鱼符,但日常无用,连装饰都称不上。
此物顾挽松有时随身携带,有时便大剌剌置于房中桌顶,藏林曾经潜入探视,发现其中装的是副台丞的金印,以为是顾挽松的权欲心使然,时时念着回京高升,不值一哂。
文士打开银鱼袋,冷蔑的目光忽地一凝,愀然色变。
囊中物通体漆黑,不带一丝光泽,茅屋内若无烛照,黑暗中恐不见轮廓。
形如卵,小于鸡蛋却大于鸽蛋,体积与一枚金印相若;触感很难说是冷硬或温黏,仿佛时时刻刻在两者间任意转换似的。
黑烟、乌云或阴霾凝聚成形,指不定就是这副德性。
“这是……”藏林倒抽一口凉气,喃喃道:“幽魔核!”他曾在死去的神军体内见过这样的东西。
此物似是神军的生元之核,一如人身的心脏,诸沃之野的蛮语音近”勃勃夜喀尔“,译作”龙妻“或”乘臼而来的夜之魔女“,故称幽魔核。
破坏此物才能打倒神军,然而每头部位不尽相同,不能以人畜类比。
毁损的幽魔核将化烟散逸,无法留存,失去幽魔核的神军则成为胡乱雕凿拼凑的畸零死物,无法说服目击者外的任何人,这曾是头活生生的可怕怪物。
所有关于神军的描述,因此不一而同,恍若呓语:有人说它们是风,有人说它们是黑雪,有人说是活过来的沼泽与山岩,更多的则认为是山神或恶鬼,是食人的”勃勃夜喀尔“;是夜的具现,为吞噬一切光明而来——”这可……可不是幽魔核,不是……不是那种低三下四的东西……”顾挽松哑声咕哝着,垂首剧颤。
藏林先生好半天才终于听出,他那混在血咳与粗浓紊乱的吞息间的,居然是笑声。
“这是自……自奉玄教圣物取下的一小部分!吕圻三以为……那物什与召唤神军的异术,必有关连!奉玄教那帮孙子,根本……根本不知自己做了什么,突如其来便开启了末世之门,忽又连同崇武行殿齐齐消失,吕圻三才意外留下这枚受托解密的样本……”藏林望着银鱼袋里的卵核,罕见地蹙眉,似乎正在厘清这当中喷薄而出的巨量信息。
在失去意识之前,顾挽松豁出去也似,睁着迅速失焦的瞳仁豺声厉笑:“先生若是末能从吕圻三那厮口中,拷掠出此一节关窍来,末必便是吕圻三输了!噗哇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