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李凌恒为孟湄舞剑,但见一身红衣,云袖兜摆,行如游龙,亦刚亦柔,衣袂翩跹,若风似云,肩臂挥洒,长剑如芒,传凝清光,天地间寂寂穿梭,庭院里瑟瑟叶落,刹那间,却见公子随秋叶共飞舞。
众人鼓掌皆叫好,孟湄高兴,便赏了李凌恒一块螭云纹玉佩,并两方手帕。
陆子岚笑:“李公子果然名不虚传,我虽不懂剑法,但却看得出比那些徒有功名之辈更见真功夫。”
李凌恒收剑,忙看了一眼旁边的王爷,笑道:“子岚兄谬赞,只不过是耍来解个闷罢了。”
陆子岚举酒不敬,倒冲孟湄讥笑:“这东厢的行不出令来,你倒要赏了,我同庚兄费尽心思猜了半天湄儿的心思,反倒不如,这还说不偏心?”
孟湄笑道:“表哥又要取笑,谁不知你琴艺高超,若能趁此良宵助兴弹奏一曲,我定有嘉赏。”
李凌恒也起哄道:“既是要讨赏,也得露点真才学不是?”
庚修远也道:“早听湄儿说起‘曲有误,子岚顾’的旧事典故,在下也早想倾听子岚赏奏一曲,不如趁王爷寿诞略展琴艺如何?”
陆子岚见不好推辞,便只好命荀安取琴来,当下正值新秋,金风荐爽,孟湄微醺,左依右偎,庚修远喂果子,李凌恒捧琼浆,众人听陆子岚坐在园中抚瑶琴,只觉丝竹绕梁,仙音绵长,李凌恒便也即兴唱道——
“今朝何事烦君问,去年曾见梅花发。况复连宵风雨横,愁他孤馆清如雪。纵有平安报,休教轻负而翁月”
孟湄听罢,不禁看向一旁的周秉卿道:“好一个休教轻负而翁月!这便是要劝王爷一展愁眉,还要今朝有酒今朝醉才好。”
周秉卿便举杯,笑容疏淡,吃过几杯,庚修远劝道:“湄儿身子渐好,这才转了凉的天,休要贪杯,若是醉了,我便扶湄儿回房。”
孟湄笑道:“休要慌张,难得官人们齐聚,今夜不醉不归。”
不多时,孟母那边送了菜来,有白烧笋鸡、酿螃蟹、果仁梅子白糖粥、百宝攒汤,裹馅肉角,春盘小菜等,庚修远便叫住孟母房里的宝贵道:“你且回了主母,小姐和王爷谢过主母心意,只是夜色渐深,兴至将醉,小姐不肯撤席,主母切勿挂念烦神,还要早些歇息。”
宝贵斜睨庚修远,笑道:“亏你有心,得了,我这就回主母去。”
庚修远面上笑喏,拿出两钱银子递与宝贵:“就当我请您吃一遭酒。”
“可使不得,官人这是折损我呢!”宝贵接过银子行个大礼,这才去了。
不大一会儿,孟母房里的宝贵来回孟湄:“主母叮嘱小姐记得吃药,休要贪酒,叮嘱诸位官人吃些饭就早歇去,王爷也休要闹得过晚伤了神。”
众人应诺,这才起身散席,陆子岚和李凌恒皆扶孟湄回房,宝贵便跟来给各位公子行礼唱喏:“主母嘱咐,还请各位官人回去早些歇着,小姐由王爷伺候便是了。”
周秉卿便道:“那是必然,你也回吧,辛苦跑一趟了,螺茗儿,宝瑞,你们拣几个菜,并那壶酒送到宝贵屋里去吃会子罢。”
“是。”一行人退下,庚修远、陆子岚和李凌恒也不得不告辞,各回各房。
庭院阒静,深夜秋凉,周秉卿扶孟湄入床,正见桌上摆一盏精巧的金龟延寿香灯,便拿起细看,不觉记起曾在宫中见过此物,如今睹物思乡,不觉伤感,便顺手取出那支合欢香点了。
孟湄卧于床上未眠,阖眼假寐,听周秉卿合衣入帐,便问:“这可是你带的甚么香?”
“非也,是那桌上的金龟香灯。”
孟湄这才记起寿礼之事,睁目细闻道:“这香倒不比平日香,怪好闻的。”
周秉卿卧于身侧,不语。
孟湄知他未眠,伸足踢他:“我只当你见多识广,这香是什么香?怎地闻起来如此奇异清暖?”
周秉卿哼道:“见过香灯却不曾闻过此香,恐是府上的驱蚊香。”
孟湄翻身,却觉浑身燥热,筋骨酥软,耳根烘烘,沁凉的夜倒睡得不安生,恨不得褪去所有衣裳。
那厢周秉卿也觉异样,心神不宁,燥气上窜下涌,翻身间又觉腿间一物胀起,心下慌张,却听枕边春声哼吟:“王爷……我恐是喝多了酒,竟觉胸口闷热,甚是口渴。”
周秉卿忙起身倒水,却觉每走一步,底下那物都蓬起一分,借灯倒水,周秉卿察觉是那香灯的祸,刚要熄了,那床上佳人便嘤道:“王爷,水……水……”
周秉卿只得转身递水,撩起帘帐一瞧,孟湄早已袒胸露乳,裙衫退尽,两颊通红,星眼迷离,玉手葱指竟游进腿间搅弄,春水溅荡,一点樱桃欲绽急呼——水,水……
此水非彼水。
周秉卿险些掉落茶杯,腹下尘柄急勃昂头,满眼雪肤粉娇牝,酥胸红梅艳,不觉俯身向前,扶起孟湄,就着那红唇点点,嘤咛娇音,吻将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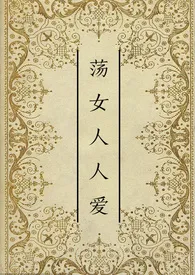

最新章节 污云经典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745181.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