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女眷休息的内寨位于凤鸣群山之后。亥时一过,正是夜阑人静,月暗星稀之际。不过这舒爽秋意之下,却注定有人难眠。
静室内韩元娘稳稳当当趴在铺上,不着寸缕,只有背上搭着一条薄毯,那遭了大难的雪臀便晾在空气中。
这吴头领的手远比掌责余、冯二人的健妇手重,这六十记巴掌换算下来也有三十板子的威力了。
虽然白日受伤回房时屁股便敷治过了,可这到了晚上又是酸痛的睡不着觉,苦忍不过元娘便又唤亲兵秋水为她敷药。
不一会儿房间门嘎吱一响,足音渐近,端着水盆浸湿了凉毛巾敷在韩元娘红肿的屁股上,立时溢出几分舒服的呻吟。
池翎为她敷过毛巾,单手拧开瓷瓶瓶盖,用细竹条蘸了,仔细涂抹在元娘的伤处。均匀涂过臀面,最后着重为青紫杂糅的臀尖上药。
即便已是小心翼翼,元娘还是痛得一颤,忙叫:“秋水,轻点……唉呦!疼……”屁股一动,自然撞在竹条上,立时疼得元娘花枝乱颤。
池翎见韩姨受苦,心里更是自责,一时无法下手。
元娘感到身后那人止了动作,才后知后觉回头一看,见是池翎,又一声“啊”脱口而出:“寨主,怎么是你?”
池翎安抚道:“是我拦下秋水不让她声张的,韩姨您受委屈了。”
元娘这才意识到自己正光着屁股,顿时臊红了脸,竟浮现出几分小女儿般羞愧模样:“大寨主哪里话,是我今日失了分寸,才被柳寨主罚了一顿,现下已经不疼了。”
池翎摇摇头:“韩姨别这么说,还像小时候那样唤我阿翎就是。”
元娘原想起身行礼,可奈何身上一丝不挂,若是回身坐起怕连椒乳私处也要被看全,只好保持着回头的姿势小声道:“是,阿翎昨夜去哪了?若不是知晓你的武功绝不会出事,只怕韩姨要担心死。”
池翎正想如实托出,可忽然察觉韩姨裸着身子坐也不是躺也不是,又不好言明好生尴尬,于是轻轻一咳:“韩姨,我先服侍你继续擦药吧,等下再说。”
“阿翎,这如何使得?”“自然使得,您先趴好。”
也罢,反正今天光屁股的模样已经丑态百出,也不差这一回。于是元娘回身趴好,屁股一撅任她施为。
伤药重新擦在受罚最重的臀峰上。元娘一痛,腚肉骤然收紧,这冰火两重天的滋味真是煎熬酸爽。
彻底抹好了药,池翎忽然起身下床双膝跪倒:“韩姨,有件事我不敢瞒着您,请您听后切莫生气。”
韩元娘忙坐起身,顾不得臀伤上前搀扶,失声道:“阿翎,你这是做什么?”
池翎暗中用内力抵抗,韩元娘自扶她不动,只得任由她跪在地上。
“韩姨。”池翎沉声道:“昨夜,是我点了余盼曼、冯玉竹的昏睡穴,又暗中放走了张鸾英,请您恕罪。”
韩元娘一时只觉晴天霹雳,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哆嗦着嘴唇:“阿翎,你可是在跟韩姨玩笑吗?”
当年自己如何被傅映秋收留的来龙去脉,池翎那时虽小,但也是清清楚楚。她怎么也想不通池翎为什么要放走自己杀夫仇人的女儿。
池翎不敢看她,埋着头:“韩姨,我没开玩笑,的确是我放走的张鸾英。还为她指明下山小路,避开各处岗哨。”
韩元娘气得浑身发抖,嗔怒道:“阿翎,韩姨我何处对不住你,你要这么做!”
池翎双拳握紧,指节霎时崩白,但她却不后悔:“韩姨待我恩重如山,如同亲生母亲一般,我这么做确是另有隐情。”
见池翎提起母亲二字,韩元娘想起了傅映秋的救命再造之恩,火气消了一半:“那好,你说说有何隐情?”
池翎见韩姨并未发作,心中石头暂且放下,跪着道:“韩姨您想,玉门县距此三百余里,张鸾英一行为何来此?”
对此疑点韩元娘本也想不明白,她只当是丈夫在天上保佑将仇人送上门来。
如今池翎提及,也是疑虑颇生:“这……月容对此也是不解,她本只当是普通小贼,却没想到擒获了网大鱼。”
池翎不动声色点点头:“正是,天下岂有如此侥幸之事?今日一早我去截住了一名侥幸逃离的巡捕。盘问之下,原来张鸾英一行,是被人引至寨里的,绝非偶然误闯。”
韩元娘蹙着眉头发问:“那人是谁?又为何会被公差追捕?”显然她回忆起了自己过往。
“这正是问题所在。按巡捕所说,这白影刚一消失,月容便现身出来。斗赢了张鸾英,又送走了他其他同僚性命。至于为何追捕,乃是为十日前那从太原运来的一批粮饷军械。”
这案子总是犯在敦煌郡内,韩元娘也是有所耳闻,不过有这样能力犯案之人总不该是无名鼠辈,她却不曾听说是哪个山头所为。
又想到池翎之言,忙摇头:“你是说月容……不会的,月容我是知晓的,她若真知道内情绝计不会瞒着我。”
池翎也同样不想妄加猜疑,“我也同样相信月容,不过若是真的有人想假借我们之手谋害朝廷命官,在水落石出之前,不可不防。”
韩元娘想了想:“原来你是因为怕我杀了张鸾英才故意放走了她。”听到这脸色稍微缓和,又道:“你这半夜失踪原是去查案了……不过你既然放了张鸾英,为何不直接问她,反而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
池翎抿着唇:“昨晚,张鸾英在主寨大堂受刑之时我就在梁上看着。她身受大刑也不肯叫饶,想来我就是问她案情机密也无答复。所幸那巡捕胆小怕死,一见了我就全招了。只是废了些脚力,倒也不碍事。”
韩元娘幽怨道:“哼,你好像还很欣赏她?她爹可与我有杀夫之仇,我岂能甘心放她?”
池翎听后不为所动,认真道:“韩姨,有句话请您莫怪。当年之事,张忠虽是亲手抓了姨夫,但严刑拷打您的是那县令,害得您与姨夫生死永隔的也是那狗官。您早已取他人头祭奠姨夫在天之灵,那张忠不过是从犯而已,罪不至死啊。”
韩元娘默默听着一言不发,池翎松了口气,继续道:“况且张忠已死,有道是人死债消,当年姨夫去世时张鸾英不过几岁,又怎能把罪孽安在她头上?”
“我……”韩元娘一时语塞,“哼”了一声,“可恨的张忠,竟如此短命,让他得了好死。”
“再来,您当年所受诸多刑罚不是也已加诸在她身上过了?冤冤相报何时了,不如就饶过她一命吧。”池翎真诚相劝。
道理韩元娘自然明白,只是要争口气而已。
“罢了,我就听你的,此事两清了罢。”心结已解又去扶池翎:“阿翎,只要她不再来招惹我我也不会再去害她,你起来吧。”
“还有一事,若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韩元娘登时无奈:“好好,你说罢。”
“刚才我去寻了云姨,云姨与我说是得了线报才突然回来。罚您掌刑也是迫不得已,请您不要怪她,要怪也是怪我一时匆忙,未与您讲明便私放了张鸾英。”池翎低头泣诉。
韩元娘垂下眼眉:“阿翎,是我犯了寨规在先,云姐赏我掌臀也是理所应当,我又怎能不懂事呢?况且我无端迁怒余盼曼、冯玉竹,害得她俩出乖露丑,真是对不住。我的屁股也真是该打,打肿了给我长长记性也好。”
池翎如获大赦:“韩姨放心,我得空便传她俩一套剑法,就当是给她俩的补偿。”
韩元娘一笑:“如此便好,阿翎可以起来了吧,让寨主再跪下去,让我如何自处?”又玩笑道:“若是让云姐瞧见了,怕是要立刻架我到院子里打板子,你是存心要见韩姨丢脸不成?”
池翎脸色一红,终于起身站起坐在床边。
元娘与她拉扯了许久,身后两瓣腚肉酸胀的难受,也坐不住了,重新趴回床上。
也不去看池翎:“阿翎,下个月初十就是你与傅姐姐对头约战的日子了吧。”
池翎看不出表情点点头:“是,再过几日我就启行南下,寨中事务还请韩姨费心。”
韩元娘不置可否:“阿翎,韩姨知道你的武功比起傅姐姐已经青出于蓝,但那贱人的“玄凰诀”变化多端诡谲莫测,我担心你这一去……去……”后面的“不回”二字终究说不出口。
池翎却看着自己纤细修长的右手,眼中腾起一抹深沉的杀意:“韩姨不必担忧,我虽还未堪破“无徽九式”的‘截天’之法,但我经年苦修之下杀那贱人足有七成把握。我一定会报了这血海深仇平安回来的。”
“啊”元娘暗暗心惊。
傅映秋离世后十六年之约便落在池翎头上。
年幼时她尚能代傅姐姐传授池翎武艺,之后便只能由柳云婵传授。
待池翎十七岁后武功大进已超过柳云婵,傅映秋池怀瑾留下的武功秘笈便只能由池翎自学。
自此之后,她便再不知池翎的武功进展到何种地步,如今听到池翎已将“无徽九式”练至‘破海’,那可是已经持平傅映秋当年的境界了,如此一来十六年之约胜算大增,韩元娘可真是又惊又喜。
“阿翎。”元娘欣喜道:“你真的长大了,肩上扛的起山寨的责任,傅姐姐……在天上也必欣慰。”
池翎为她盖上薄毯,遮住了略微消肿的臀部,轻声道:“夜深了,韩姨好好歇息,池翎先告退了。”
元娘微笑道:“多谢寨主挂怀,属下身体不适,便不送了。”
“韩姨保重。”
池翎退出院外,平息起伏的心情。温柔的夜风阵阵吹拂,吹散了身上微微汗意,十分干燥凉快。
池翎回房后简单洗漱一番合衣躺下却睡不着,心中寻思:“韩姨云姨虽不怨我,但此番确实太欠考虑,若不是云姨及时回寨主持大局,指不定还要闹出多大乱子。”
寨中戒律法规大多由傅映秋当年所立,小错则笞大错则杖,若是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轻则废去武功逐出山寨,重责三刀六洞处死。
除了寨主之外全寨上下都要受其约束,堪称金科玉律。
池翎身为寨主戒律虽可豁免,但她心里却过不了这一关。思虑既定,她打开束之高阁的箱子,翻出娘亲传下来的乌木戒尺。
戒尺握在手里,小臂长度足有两斤重,通体黝黑散发出丝丝寒意。池翎在空气中甩了甩,又把熟睡的茹雪喊到屋里。
茹雪睡眼惺忪,被打搅了美梦自然不愿可却又不敢对着池翎发作,打了个哈欠:“寨主,您这么晚唤婢子何事,可是饿了?婢子给您下碗面?”
池翎暗骂一声:“死丫头,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么个贪吃的形象吗?”可面上却丝毫瞧不出,只是将手中戒尺塞进茹雪手里。
这戒尺本是傅映秋传给柳云婵用来管教池翎之用。
幼时柳云婵嫌这戒尺太重,成年后寨主之位让给了池翎,甚至对她又敬又佩,这戒尺自然成了摆设,当做遗物之一还给了池翎。
是以这把乌木戒尺至少是一十六年未亲吻过臀肉了。
茹雪一怔:“您又练什么神功呢?大半夜拿把戒尺晃来晃去做什么?”
饶是池翎成熟稳重的性子也差点笑出声,万幸及时收住:“昨夜张鸾英是我放走的。”
“哦,这样啊……什!什么!”茹雪瞪大了眼睛。
池翎不想与她详细解释:“我身为寨主自不好受戒律,就在这以此自罚,由你执刑。”
茹雪好似吓傻了一般呆立不动,池翎心一慌,摇了摇她:“茹雪,你怎么了,可别吓我。”
“我没事。”茹雪缓了缓,“那寨主是想让婢子打您屁股?”
池翎老脸一红,“是这个意思。”越说越没底气。
静默良久。
茹雪打破沉默:“那寨主想好了罚多少下吗?”
这一下真是问着了池翎,池翎从没挨过打,又心地良善,极少责罚犯错的姐妹,对此真没概念。
池翎心说既然自罚,总不能太少显得心不诚,于是道:“那便罚跟韩统领一样的数目吧。”
茹雪掂了掂戒尺,摇摇头道:“以这戒尺的份量若是笞六十,怕是屁股都要打烂。以婢子经验,便是笞个十下已是够疼的了。”
这茹雪虽然机敏,但做事却有些怠懒,平日里没少误了点卯进军政司受罚。这巴掌、竹篦也是没少挨的,自然经验十足。
池翎却有些不信,还是说:“那就罚二十下吧,你不准徇私留手,不然我必责罚,知道了吗。”
“婢子不敢。”但茹雪又犹豫道:“您真想好了吗?虽然您放了张鸾英,但刑可不上寨主的,别人也不得说什么。”
“自然想好了。”池翎脱了外衣,脑后长辫绕在颈上,在桌案前站好解了腰带,将外裤连带着短跨一褪到底。学着样子,塌腰撅臀俯在案上。
池翎的屁股真是紧致丰盈,烛光打在上面,照映出玉瓷般光滑健美的肌肤。
由于经年习武骑马,这两瓣臀肉更是结实挺翘的外翻,那后庭与私处构成的菱形区域一寸不落的暴露在空气里。
茹雪服侍池翎也有两年之久,身上什么位置没见过?但这般羞耻的姿势可还是头一次见,心里蹦蹦直跳,握着戒尺的手心都沁出了汗。
池翎也是强撑镇定,感受着茹雪的目光正盯着腿心羞处看,下身好似灌着凉风,手脚冰冷,脸颊却红的发烫。
茹雪强压紧张:“我……我要打了。”
池翎羞到说不出话,只是“嗯”了一声。
池翎只听身后一阵劲风,“啪!”得一下正击在圆翘臀丘,一瞬又酥又麻,池翎一个激灵,好似血倒涌上头。
身后停了动作,茹雪细如蚊音:“寨主,您怎么样?”
酥麻感觉一过,一股刺痛蔓延在臀丘上,冷热交接,好像由薄到厚掀掉了层皮下去,好不难受。
池翎谎道:“没事,接着打吧。”
茹雪看着柔柔弱弱,但打起戒尺来却如同女中豪杰,又是一记戒尺叠在那处,这下顿时隆起一道三指阔的肿痕。
池翎闷哼一声,好悬没叫出声来。
平日来她看寨中受刑的姐妹挨打时无不尖声哭叫,总觉得太过做作,有失脸面。
今日亲身挨打尝到了这磨人滋味,才知道姐妹们的哭叫不是装出来的,这般痛楚又如何忍住不叫?
池翎没叫停自然继续责打,茹雪又连挥三次手腕,三下戒尺整整齐齐的印在臀峰上,留下了三道硬肿僵痕,几乎染红了整个臀面。
多年来的仇恨让池翎懂得何为忍耐,习惯了痛楚后一声不吭的咬牙忍着。
凤鸣寨中的规矩,受罚时一律不准运功抵抗只得皮肉硬挨,不然加倍重打。池翎自然不运内力,呼吸渐渐粗重。
茹雪虽是不忍心,但她知道若是轻罚便是辜负池翎一片苦心。于是硬起心肠,十足十的力气狠责。
又是五记乍响,从臀翘打到臀根,将腚肉再次过了一遍。
这戒尺又厚又重,威力大的要命,池翎却只是皱起眉头,一声不吭,绷紧臀腿任由锤楚,分毫不动。
这是她该受的,她不想逃更不愿逃。
臀肉高高肿起,烛光下臀面由红转紫,尺痕交叠处更是有着点点瘀血。
茹雪不忍细看,但也知那臀儿上已经无处可打,索性闭着眼,不管准头肆意打下。
每一记戒尺下去池翎呼吸都是一滞,戒尺起落留下道道烈痛。那凝脂白玉般的雪臀已经紫霞密布,圆臀因肿胀从内而外颤抖着。
最后三下时,池翎腰下腿上都找不到一处完好的肌肤,挨的最重的臀峰肌肤处已经肿胀菲薄,透过淤紫近乎盈然透明。
池翎额上尽是细汗,痛彻心扉的苦楚几乎坚持不住。
第二十下落在臀底,池翎更是竭力的咬牙才咽下叫痛声,额前发丝凌乱,被汗水打湿拧在一起。
茹雪扔下戒尺,忙抱起池翎带着哭腔:“打完了,疼坏了吧!”
其实已经难挨到了极致,池翎却硬撑起笑容宽慰她:“是挺疼,不过我忍得住。”又轻轻推开她:“好啦,别哭了,让我先把裤子穿上好吗,丢死人了都。”
茹雪这才放开她,随意揩了把泪:“打成这样还穿什么裤子?快趴下,给您上药。”说着把池翎按趴在床上。
这上药之痛更是如同炮烙,疼的池翎玉面含痛不住扭曲,好不凄惨。好不容易上好了药,茹雪服侍池翎睡下,就这么在她身旁守着她过了一夜。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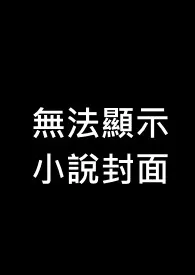



![《[嫉妒的男人系列]不择手段的男人[SD][流花]》完本小说免费阅读 1970最新版本](/d/file/po18/671271.webp)
![星际最受omega[gl] 1970最新连载章节 免费阅读完整版](/d/file/po18/692579.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