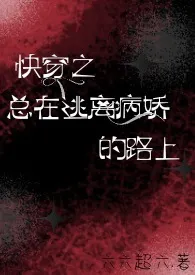那天的袭击,风家死了六个人,包括四名侍卫和一名家臣助理,其余的人都受了或轻或重的伤。
对方死了二十来人,抓了十几个,跑了十几个。
经狼一骁确认,他们属于狼族一个黑狼小部落,不认可狼惑的统治,不承认惑极其子孙有使用狼姓的资格。
经查,那个临时基地存在了约有两年,由于地处荒僻,反侦查设备先进,一直没有被发现。
袭击中风赢朔发现那个方向出现了三次增援,才产生怀疑。
风赢朔这次出行的时间地点路线都是机密,知道的人没几个,甚至同行来参与项目考察以及合作的几个家臣也是临时得到通知就立刻出发的,袭击者准备充分,可见是拿到了确切消息的。
但双方都不希望关于军备研究的合作被拖延,于是一边进行考察和谈判,一边紧锣密鼓审讯俘虏和进行其他调查。
白天渊寒都跟随着风赢朔,寸步不离。
他不信任景川,几次建议风赢朔对其采取一定的限制措施,风赢朔都认为没必要。
他说:“渊寒,有时候不一定需要有形的项圈。”
渊寒听不懂,但他最终还是相信风赢朔的判断。
他十八岁就跟在风赢朔身边,已经十二年了,亲眼看着这位年轻的家主如何一步步往上走,直到坐上家主的位子。
信任这种东西,也许可以凭空产生,毫无理由。
但要保持信任,靠的不是虚无缥缈的直觉,而是利益的交互和各方面的制衡。
风赢朔明白这一点,景川也明白。
袭击发生后第二天开始后风赢朔就很忙。
景川并不知道他的具体行踪,也毫不意外地没有得到命令去作为一个真的近身侍卫或贴身保镖那样跟着他。
同时他不被允许离开驻地,理由是不安全。
他倒也不介意,没事就跟全晖在驻地里溜达。
听说这里驻扎的是风赢朔正在培养的一支新部队,他留心观察了一阵,发现这支部队的士兵的确素质过人,装备也很精良。
从全晖那里,他得知新军士兵的来源几乎都是世家子弟,在陌星属于较高等级的平民。但其实换个角度,也可以说他们属于较高等级的奴隶。
他坐在驻地的操场边上,看着不远处一支小队在操练。
全晖提醒他:“该回去换药了。”——他脸颊上那道伤挺深。
自从全晖知道他现在身份是私奴了,对他的伤,特别是脸上的伤格外在意。
景川自己无所谓,架不住全晖一天到晚盯着。
不在内宅,景川暂时还感受不到私奴和三等奴的明显差别。
昨天晚上带着伤被同样带着伤的风赢朔翻来覆去操了好几遍之后,回到分给他的住处,全晖仍然让他戴着肛塞睡觉。
不过他拿到了一个可以随身带着的个人只能微端,并且给他开了少数权限。
他可以联网看一些公开信息资料等等。
无聊的时候至少可以不那么闷,也多了一个渠道了解这个星球。
军用治疗仪和各种先进外伤药物在驻地应有尽有,加上全晖的特别关注,一天功夫他的伤就明显好了很多。
他一面因为伤痛减轻而高兴,一面为即将到来的夜晚而略有不安。
昨晚回去之后全晖除了给他身上的伤换了药,还拿出一管药膏,说是用于肛管的,问他自己擦还是自己帮他擦。
他很想问全晖,是不是变成私奴之后相当于变成使用频率更高的鸡巴套子了?
所以保养得比过去细致一些。
没真的问出口,因为他心里知道答案。
他不是很明白为什么,但风赢朔好像真的很喜欢操他。
而且那个人真是精力旺盛,还在内宅的时候景川就经常大半夜地被叫过去,现在把他带到驻地来就更不用说了。
果然,晚饭后两个小时,他被叫到风赢朔住处。
驻地内部提供的住房区别不太大,风赢朔住的是个套房,但和酒店相比陈设算是非常简单朴素的了。
景川一走进去就看到风赢朔坐在张小桌旁,上面摆了些水果,这一幕与他们曾在青山庄园时相似,景川不由得有一瞬间恍惚。
他原本是要在门口下跪请安的,鬼使神差就直接走了过去。
风赢朔看着他,也没说什么。
他就拉开风赢朔对面的椅子坐上了上去。
风赢朔披了件长睡袍,带子在腰间松松地系着,露着锁骨和一小片胸膛。那上面还有几道轻微的擦伤和一些瘀痕。桌上都是水果,没有酒。
“不是说这里有最正宗的隐泉和暮光?”景川不客气地问。
“伤没好,不用急。”
“不喝酒,这么对坐有点尴尬啊。”景川摸摸鼻子。
“我没叫你坐。”风赢朔看着他,“跪过来。”
景川:“……”
他只好起身,走了两步,跪在风赢朔脚边。
“你昨天做出了选择,那就认清你的身份,好好服侍我,取悦我。记住,我不是你的‘朋友’,我是你的主人。”风赢朔语气淡淡的,听不出情绪,也听不出感情。
“是,我明白了。是我错了。”景川马上就态度良好地认错。
风赢朔捏着他下巴把他的脸扭到侧面,仔细看他脸颊上的伤。没缝针,贴着透明且透气的医疗贴片。
“手臂呢?”
他把两条手臂都抬起来让风赢朔检查。
这里的伤比较重,缝了针也包扎着,这么看根本看不出什么来。
不过他的动作很利落,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不大。
“您的手怎么样了?”
风赢朔用左手隔着景川的衣服揪住了他的乳头——作为对景川问题的回答。
“嘶……”
“翻车的时候被撞到,暂时性神经麻痹。”他解释了一句,拧着那个小东西。
景川不是不习惯风赢朔的阴晴不定,只是有时候会因为他这种捉摸不透的态度怀疑自己对他有过错觉。
有时候他觉得对方并不是那么不讲理,有时候觉得或许在袭击之后,他主动留下来,他们会有和过去不同的相处方式。但他错了。
他按风赢朔命令脱得一丝不挂,在椅子里无奈地抬起双腿时,对自己留下来这个冲动的决定有了怀疑和动摇。
他的后背靠着椅背,避开小臂前端的伤,用肘部压着膝弯,把大腿压到胸口,像婴儿换尿布时的姿势,露着性器和肛门。
从分开的腿间,他看到风赢朔拿了把木质的发刷站在那里。
厚厚的发刷背面放在他臀尖,贴了一贴,就沉而有力地拍打下来。
疼痛炸开,然后迅速蔓延。
是了,这个人说过,他有权力,所以他从来不忍。
他想打,他就打;他想操,他就操。而自己衡量之后听从直觉选择留下,就不该心存幻想。
更为羞耻的是,他能越过自己的性器,看着那个发刷一下一下地落在他的屁股上。
举高腿的姿势使得屁股的肌肉绷得紧紧的,痛感更为强烈。
风赢朔还是一贯的又快又狠的纯纯发泄式的揍人风格。
累积的疼痛很快就由沉钝变得尖锐起来,腿根也跟着泛起红色。
每次挨揍,景川一开始都能忍着不出声,但迟早会忍不住。呻吟声迟早会随着混乱的喘息一起溢出。有点沙哑,裹着灼热的呼吸。
然后,他惊恐地发现他的阴茎在勃起。
是因为疼痛已经和快感产生了联系吗?还是因为今天这个姿势的羞耻感太过强烈?
他的会阴部早已不长毛发,这是在那个变态的制度下他被物化的象征之一。
他相信风赢朔承诺的报酬早晚会兑现,只是自己留下即默认同意成为对方玩物的状况不会改变。
是赢了还是输了呢?
在他的角度来说,这已经是以他的情况,在最小损失下获得的最大利益了吧。
那么风赢朔想要的利益是什么?
一个没那么乏味,又耐揍耐操的发泄物?
最起码,目前他是比较对得上这位家主口味的。
工作。
他默默给自己洗脑——这是一份工作。这已经不是从前那种单纯被虐打,而是有价码有报酬的了!
既然改变不了“工作”的内容和性质,那么……“工作”中偶尔有一点点快乐,是不是也该抓住不要放,而不必徒劳地抵抗身体的本能?
他闭上了眼睛,不再控制自己的痛叫,也不管那根颤巍巍翘起来的阴茎——反正也管不了。他不确定是不是听到了风赢朔的嗤笑。
拍打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下来,疼痛还在。屁股发麻发胀,肯定肿了。
突然,不知道什么东西麻麻地爬在他性器上,令他差点抱不住腿。
“啊啊啊——”
他惊叫着睁开眼,发现风赢朔正用发刷“梳”他的胯间。
木齿顶端是圆的,但梳在敏感的性器和阴囊上,那种酥麻简直像触电。
阴茎完全硬了,斜向上竖起,马眼汩汩流出透明的腺液。
他控制不住抖了起来。
风赢朔像是发现了有趣的玩法,一路梳到腿根,再梳到肿胀的臀肉。
疼痛未消的肉团被密集的梳齿滑过,像蚂蚁爬又像微电流的刺激,又痒,又有种奇怪的快感。
景川抖得更加厉害,暴露着的穴口很明显地在自行蠕动张合,仿佛在渴望地祈求什么东西的插入。
凉凉的感觉抵住了穴口,慢慢被送进去。是一枚鹌鹑蛋大小的青色的果子。这是陌星特有的果子,籽小,肉厚,皮脆但不软。
“不……”好不容易压下去的耻感再度飙升。
“啪!”发刷又抽了一下屁股。
“你有资格说不?”
又一颗果子被塞进去。
那个洞是为挨操而做好准备的。
昨晚回到住处照例戴着肛塞睡觉,今天过来前在全晖催促下做过扩张,也注入了润滑液。
外皮滑溜溜的果子进入得一点也不困难。
风赢朔似乎发泄完了暴虐的情绪,开始饶有兴趣地用一些稀奇古怪的方式去玩他。
一边塞果子,一边不时拿发刷“梳”他。
他的穴口一口一口地,非常乖顺地吞着果子,甚至显得有点急迫。
肠道被塞得发涨的感觉既熟悉又舒服,又觉得远远不够。
缺了点温度,也缺了点活力。
越不满足,张合得越是急促饥渴。
他不知道那里一共吃下去几个果子,但他知道已经满到再也塞不下了。
最后一个果子已经被挤到穴口,把那个小口撑开了。
他能想象那个湿漉漉的红色肉圈里那一小块青翠的果子颜色。
外围则是被打到肿胀发红的臀肉。
而他还抱着自己的腿,让大腿紧贴着胸腹,展览似的完全暴露着吞吃了果子的肛门和红屁股。
太淫荡了……他一面羞耻着,一面硬得发疼。老A銕缒更七医灵'舞吧吧舞#酒灵
“好吃吗?”
梳齿刷过那个张开的穴口。景川清晰地感觉到敏感的肛口颤抖着收缩,像是连梳齿也想吃下去。
“跪起来。”风赢朔用发刷背面拍打他,调整他的姿势,让他在椅子里跪起来。
他身材很高,尽管椅子不小,但他还是跪得很局促,大半个屁股悬空露在椅子外面。
发刷在又疼又肿的屁股上继续劈里啪啦地拍打了几下,力道比之前轻了很多,算不上太疼。
一边打,风赢朔一边说:“排出来吧。”
景川把头抵在椅背上,连手臂都抖了起来。
每一次他觉得自己到达了底限,就会被逼到更低的那个标尺。
“怎么?舍不得?”
“没有。”他忍住羞耻,收缩肠道肌肉。肠道自然而然开始往外排挤异物。
肛口括约肌被撑开,那个小圆逐渐扩大,露出更多的青色果皮。
发刷的拍打还在继续,又疼又麻的刺激感让穴口下意识收紧,把果子又吞了回去。
“别磨蹭。再不排出来我就多塞几个进去。”风赢朔催促。
景川只好尽量忽略发刷的拍打,控制着肠肉收缩。
终于,最外面的那颗果子“咚”一声掉下去,在地面上小小地蹦了两蹦。
穴口也一瞬间缩紧,又在他的努力下再次慢慢张开。
他下蛋一样,一边被发刷拍打一边把果子一颗一颗排出来。
最后一颗被风赢朔恶劣地往回推了几次,才终于得以彻底离开那个腔道。
随后,三根手指插了进去,粗暴地在里边翻搅,像要查看还有没有遗漏。
手指抽出去之后,换成了粗长硬热的阴茎。
有温度的,有角度明确的动作的,那个甬道所熟悉的阴茎。
“呃啊……”
景川仿佛觉得肠肉在欢呼似的,热烈地吸住了那硬热的肉棒。
昨天晚上才做过几次,风赢朔精力就好像已经完全恢复了,又狠又快地在景川股间进出,游刃有余地摩擦刺激景川的腺体。
景川左手撑着椅背,右手摸索着握住了自己的阴茎。
肉柱上滑腻腻湿淋淋的,全都是腺液,还在失禁似的往下流。
他本能地跟着风赢朔的节奏套弄起来。
风赢朔发现了,把他右臂扭到身后。
景川被操的时候自己摸自己也不是第一次,风赢朔有时候允许,有时候不允许。
景川知道对方的目的——想看到他失控、崩溃、祈求,或者被操射。
他大多数时候会竭力控制着,所以基本上最后的结果是被操射。
但是……
既然是“工作”,不是刑讯……
为什么不把折磨转换成享受?
“主人……”他没有刻意改变声调,但这一声还是显得格外软弱,略微沙哑的绵软语调仿佛示弱的撒娇,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身后的人用力顶了一下:“求也不行。”说得很无情,可语气很愉快。
随后的抽插与之相反,是更加如狼似虎地凶猛。
啪啪的肉体撞击声越来越大,顶得景川声音里无法抑制地带了点呜咽。
是强势地占有和侵略,也像黏湿急促的缠绵。景川分不清,风赢朔也分不清。
但在这样的夜晚,也没有人想要认真地去区分和追究根源。
【作家想说的话:】
抱歉抱歉~~~昨天太忙了,写不完。用手机写着写着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