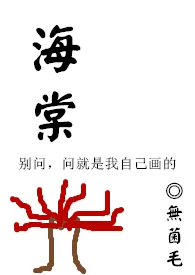又是一年春好处,荣川城外山坡上阳光明媚,视野开阔,宽广的古道由这里向远处延伸。
春风和煦,拂过漫山花草,荡起的春潮渗透着甜美韵律,引得那赏景之人的心尖儿上也荡漾起丝丝涟漪来。
女子优雅起身,素手轻提粉红色百花曳地裙,款款走出车厢,呼吸间尽是青草的芳香,美人不由自主地敞开胸怀,藕臂贴紧玲珑腰身,粉拳轻抬,踮起脚尖,舒服地伸了个懒腰,端的是风姿绰约,美的浑然天成,和这春朝盛景融在一处,不分彼此,看得身旁驾车的女子都愣了愣,眨巴着一双杏眸夸赞道:“云儿总是这般千娇百媚,稍不注意都要被她举手投足间勾了魂去~”那被称作云儿的女子顿时红了脸,转过身,双手叉腰,妩媚天成的桃花眼儿水灵灵,故作恼怒地瞪她。
那驾车女子见状更是夸张地摆摆手,做出躲闪的姿势,嘴里还笑道“啊!你可别!就怕你这个~被你这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看,人家哪受得住呀!要不…”
女子双手护胸,低眉顺眼作羞涩状,“人家从了你吧!噗哈哈哈…”
“玉!长!瑛!”谢淑云实在是受不了这女流氓的自娱自乐,纵身扑过去誓要给她一点颜色瞧瞧,两人嬉笑着打成一团。
“你这云儿,敢这么扑过来,也不怕给你那粉脸蛋儿给摔花!”
“哼我就敢,你不是自称玉女侠么?女侠还接不住我这般千娇百媚的弱女子啊?”
“臭女人,少趁机给自己脸上贴金~”
“彼此彼此!”
“哎。师父~云姨~你俩消停点儿吧!咱们就要进城啦,人多着嘞!”车厢里一个少年探出头,一脸无语地提醒。
这少年随即走出,只见其五官端正,清瘦挺拔,一头黑发乌亮微曲,在额头上打个卷儿,衬着同女儿家一般白嫩的肌肤,唇红齿白,大眼水灵,活脱脱一俊俏小郎君。
只他着一席藏青色布衫,负手而立,神情严肃,又像个小大人一般。
谢淑云立马停止了打闹,美丽起身,朝着少年温柔一笑,“还是我们小夏懂事!云姨这一别呀,以后不知何时才能再吃到小夏做的冬瓜丸子汤!想想都有点惆怅…”
她这话半带调笑,实则也真是有些不舍和伤感。
十六七岁的少年从小同师父相依为命,生活独立又乖巧懂事,察言观色的本领自不必多说,见状立马笑嘻嘻安慰道:“云姨说的哪里话!师父这厢忙完了要事,之后我们师徒俩云游的时间可能就没这么多了,到时候我求师父来这边定居,咱们抬头不见低头见,您看可好?”
“木小夏!你胆子越来越大了,现在都敢替你师父做决定了,再往后不得上房揭瓦啊?”
长瑛实乃女中豪杰,翻身从马背上一跃而下,没注意到听见这话后少年眼里一闪而过的幽深。
“好啦,我的好云儿!”长瑛牵起淑云的手正色道:“等这次事情忙完,我就带这浑小子来荣川相看好地方,准备在这边开个医馆,也就定居这里啦!此一边届时再相聚,你我可要一醉方休啊!”
谢淑云闻言欣喜不已,又感动于师徒俩对这份友情的呵护与重视,两个老朋友又拉着聊了半会儿,才终于依依不舍地分别。
荣川城内。
淑云将各种日常用品购置妥善,提着个小竹篮,悠游自在往家里走,时而想着算过日子,女儿应是明日旬假,这时候回家做点什么好吃的给她呢?
时而又想着这次回青州谢家筹备移居事宜时发生的一些趣事…
时而想着…
时而…
怎么回事!
为何自己一单下来便老是想到那个浑人!
谢淑云突然气急,恨自己不争气,躲了躲脚。
自己明明很努力地去想一些有的没的,可那张臭脸还是避无可避的在脑海里出现,赶都赶不走。
真真是烦死个人!
谢淑云加快了脚步,不知道是跟自己赌气还是跟那混不吝较劲。
然后不知不觉转到熟悉的街角,小女人低着头降低自己存在感,默默往前走,蓦地被一片阴影笼罩,心中暗道不好,抬起头的瞬间,毫无意外和那双深邃犀利的眼眸对视在了一起。
“嘿!这还真是巧了。这是哪里来的小娘子啊?”男人高大威武,横在路中间跟个拦路虎似的,眼神微眯,笑得玩味:“嘿哟,失礼失礼!看这小娘子梳的发髻原来是个有夫之妇,在下唐突,实在是抱歉!”说罢还一本正经作个揖。
谢淑云被他阴阳怪气的话臊的脸儿通红,桃腮鼓起,也不怕他,直溜溜冲着他怼到:“许淮山,你有病不有?有就去治。”说完扭头就走。
“走反了!你家是往那边走的么你就走。”男人逐渐忍俊不禁,“得了吧,进来坐坐呗!昕儿还有一个时辰才散学,早都打点好了,你届时直接回去便可。”
淑云闻言默默转过身来,打定主意不理他,听见他后半句,想他这么些日子以来对女儿一直还算上心,又不忍直接拒他好意。
自己又旷了这么久…
看这浑人期盼的模样,淑云沉默了一会儿,最后在他那灼热幽深的视线中瞪他一眼,莲步轻移,提着东西往那熟悉的铁器铺子里头走去。
黄鼠狼给鸡拜年!
没办法呢…又要上他的圈套了,他真是太狡猾了,才不是自己有什么奇怪的念头。
男人瞅她那纠结别扭,复又顺从的模样实在可爱,宠溺地笑笑,跟着美人走到门口,干脆利落地关了铺子。
“瞧见那女人没有?悄悄跟你说,这娘们好像是个寡妇!看着挺端庄的,守寡没多久就耐不住寂寞了,这会肯定找那铁匠那啥来的!我在这铺子外头见着好几次了。”街角处,一人贼眉鼠眼地瞅着铁器铺子跟旁边的伙计说道。
那伙计嗤笑一声,骂道:“直娘贼!也不瞅瞅你那样,天天杵在这儿干这些偷窥事,人家找男人你也管不着,终究是找不上你这蜡枪头!”珠炮样儿的一串话说得那人红着个脸半天憋不出句话来,又低声凑过去道“且不怕告诉你,哥们在这地儿摆了这么久摊了,那铺子怕是不简单。”
那人闻言心底一惊,忙凑过去问“哥哥可否教我?”
伙计也是个大嘴巴,这才有点得意地跟他说悄悄话:“前两年那铺子易主,接手那铺子的来历闹的不明白的!奇怪的是官府没有派人细查过那家户籍,起初我想着恐是恰巧查串了闹忘记了,直到后来有一回丑时起夜正好瞅见一伙黑衣人施展轻功翻入那家后院又翻出…你还是莫要再悄悄盯那铺子,铁定有猫腻,小心惹火上身!”
说到这里,那人才觉着有些后怕,背后衣裳已经被汗水打湿,忙点头哈腰应是,摆摆手走了。
且说许淮山关了店门,走进正堂亲手给轻车熟路就坐的美人倒了一杯茉莉花茶,凑近她别有意味地说了句“等我”便掀开打铁房的帘子忙碌着收拾打理各式各样的铁器和火具,里面叮叮哐哐响个不停,似是比往常更有干劲。
淑云虽说来这地方许多次,但也从来没仔细看过男人平日里劳作的地方,实在也是有些好奇的,便出声询问:
“淮山,我能进来看一下吗?”
女人轻柔的声音和环境格格不入,像轻飘飘的羽毛拂过心间,闹得人心痒难耐。
男人手头的动作骤然停下,立马回了句“当然”,心想这小娘们还是这般有礼貌,当真是大家闺秀。
心思全在美人身上,也无心再做这些破事,便匆匆熄了火迎她进来,在一旁小心护着。
淑云打量着这个宽敞明亮的房间,看着四面墙上挂着的琳琅满目的器具,多是商单所需的大件铁器样件,也有一些做工更加精巧的、像是手工艺品的玩意,有的看上去又像是官府为官兵定制的武器部件等等。
淑云不懂,但大为震撼,又觉得男人这差事实在是辛苦,也难怪他锻炼的这般身强体壮…停停停!
自己为什么要想这些…
许淮山这厢一直默不作声地观察女人的神情,见她没有要自己稍作讲解的意思,就跟个柱子一样杵在那一动不动。
又看她突然心不在焉,撇撇嘴心想小娘们别是嫌弃自己现在这活计就行。
两人就这般各怀心思,一阵无话。
“那个,要不咱们开…开始吧。”女人突然打破沉默,小手轻抬,纤纤柔荑扯了扯男人衣袖。
“?”
“!”
美人居主动求欢,许淮山始料未及,目瞪口呆在那里。
不过他许淮山什么人,马上思绪回笼,坏笑一声,双眼死死盯着女人,跟看猎物毫无二致,看得淑云有点发怵,暗骂自己万万不该向他发出那难以启齿的邀约。
“这可是你说的,到时候别后悔!”
玩笑!
爷们什么场面没见过。
许淮山伸出粗壮铁臂将女人豪迈揽入怀中,环住女人宛若无骨的玲珑细腰,紧密贴合着那动人的曲线,单手将她抱起,掀开门帘,在女人似喘似吟的娇呼声中一路走到后院,踹开门板,将这勾人的尤物放在榻上,声音粗声粗气。
“小东西今天怎么比爷们儿还急?乖乖等着,等爷洗完就回来干死你!”
淑云吐了吐香舌,心想谁是小东西!
臭男人明明比自己小了好几岁。
又暗自腹诽自己跟这浑人本来也就图这事儿,坐在床沿,素手轻揽曳地裙摆,纤腴适度的一双玉足来回轻蹬,百无聊赖地在男人的卧房到处比划着——
嗯…倒是不像男人自身那般不修篇幅嘛。
屋子里虽然简陋,但是打扫干净,铺设整齐,不仅毫无异味,甚至还有淡淡的檀香?
淑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又暗自好笑,这浑人居然还有熏香的习惯,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哪来的公子哥嘞!
只突然间,淑云似是瞧见了什么与卧房格格不入的事物,循着视线所过,发现是一把挂在角落的长剑。
她一眼觉着不对劲儿,这剑鞘是罕见的深红色,上面有精细雕刻的纹案,且看外形还很秀气,和房主人的气质大相径庭。
即便淑云对刀剑一无所知,亦十分肯定这把剑不是许淮山配与自己用的,那缘何单单要将这把剑挂在卧房中呢?
可能有什么故事在里边吧,真是奇怪。
罢了,横竖与她也无甚关系…只进入身体不入生活便是他二人最大的关系了,淑云没心没肺地想着。
而后,丰满娇躯被赤身裸体闯进来的壮汉高高抱起,两人一起滚落在米黄色的地毯上。
………
良久。
屋内只点亮一盏已有些泛黄的油灯,照出一对男女在大床旁边绵软的卧毯上一丝不挂地缠绵在一处。
两人情事刚起,抱在一处那是你侬我侬,那本不协调的黑白两色此刻却是完美融合,相得益彰,让人觉出些许奇异的美感来。
这一身赤黑腱子肉,威猛雄壮的汉子铁臂环住美人柳腰轻柔爱抚,宽厚的手掌一寸寸地把玩着那玲珑曲线上的滑嫩美肉,粗糙温热的触感闹的人直痒痒,仿佛要痒进了人心里。
男人手上动作温柔体贴,可那幽深的、野狼一般盯紧猎物的眼神却毫不掩饰将面前人儿拆食入腹的欲望。
情欲荡起丝丝涟漪,美人被这赤裸裸的眼神牢牢锁住,羞臊地转过小脸不去与他对视,却是听见男人不怀好意地笑了笑。
“装害羞了?待会儿干你的时候可别又叫得比谁都骚!”
这厮最爱在欢爱之事上逗弄她,无论是言语还是动作,她的一切反应仿佛尽在他掌握之中。
谢淑云有些不服气,斜着她那双标志性的、妩媚天成的桃花眼儿瞪他。
男人眯了眯眼,笑得更加玩味,不说话。
谢淑云陡然感觉到了危险。
“浑…浑人!做什么这样看我…”美人檀口微张,香舌隐现,似怒似嗔,俏脸红彤彤,分明是半老徐娘偏生出几分小女儿姿态,能教人看迷了眼。
她却不想自家生的这般花容月貌,在这昏暗灯光下眼波流转的勾人模样,更是激起男人骨子里的欲与狂。
果不其然,话刚出口,绰约多姿的小美人就在下一刻被这堂堂壮汉护住后脑勺一个猛扑,丰满娇躯仰倒在柔软的卧毯上。
“妖精,几天没肏就拿这骚劲儿勾引男人!”被扑倒的瞬间,耳边传来他暗哑醇厚的嗓音。
………
一个时辰后。
昏暗的卧房里到处都是水渍,肉体击打的啪啪声还在响个不停,夹杂着女人难耐的娇吟和男人闷声粗喘,听得人血脉喷张。
“娇云儿…好心肝儿…老子的肉棒插的深不深?干得你爽不爽…小骚逼,以后这里就是老子专用的地方,知道了吗?”熊一样的男人肌肉成垒,浮动着凶光,喘着粗气,大手扣着女人丰腴光洁的美臀,粗糙硕大的龟头霸道顶开层层肉褶,滚烫坚硬的粗黑肉棒一次一次将泥泞潮湿的粉嫩肉穴贯穿到底。
一次又一次被狠狠塞满,肉棒横冲直撞不给喘息,汹涌而来的快感层层迭起,淑云不由自主地缩紧小穴,湿嫩的穴肉紧紧缠住汉子的粗长肉棒。
男人被夹的一阵舒爽,大掌把玩着她光滑丰嫩的腹肉。
“云儿不愧是大户人家养出来的贵妇人,这白花花的身子哪哪都是美肉,干起来真是爽…”雄壮的腰胯强有力地摆动,在丰腴美臀上狠狠砸出一道道迷人的白浪,浪花荡漾进汉子猩红的眼眸,又仿佛刻印在了他的心尖,要他时时想着念着,挥之不去。
干惯重活的粗糙大手对着就是一巴掌。
“啪啪!”
“哦哦❤️!?”美人突然受袭,尖叫着吸住肉棒,浑身颤抖,吸的男人差点便是去了,当即停下动作辱骂道:
“臭骚逼这么能夹?打打屁股能给你爽成这样,真是个十足的骚货,”
又重重地顶一下,“骚货快说!是不是喜欢被老子打屁股?”
淑云刚刚那一瞬本就冲上了高潮边缘,玉足紧绷,小穴里爽痒难耐,这个节骨眼儿上被男人肆意羞辱,却是仰头抿唇,露出白暂修长的天鹅颈,强撑着不说话。
男人感受着穴道里的微微痉挛,暗笑她嘴硬,两只宽厚有力的大掌把住美臀左摇右摆起来,粗糙的龟头随着摇晃研磨着子宫口,那久旷深闺的敏感之地被肏弄得颤抖不已,一股股湿滑的花液从褶缝流出,把那粗长的肉棒淋得黑亮黑亮。
“啊~❤️啊啊❤️好哥哥,山哥哥❤️别磨那处…快,快给云儿…”淑云终于忍受不住,燥动不安地扭着屁股求饶。
那浑人听了,坏笑一声:“说多少次了?在床上要叫老子夫君!瞧你这骚浪挨操的样儿,你那些大家闺秀的教养都去哪了?”说罢不再磨蹭,拔出湿淋淋的大肉棒,将美人的翘臀高高抬起,“噗呲”一声对准那蜜水潺潺的淫靡穴口狠狠一个猛扎,“啊❤️啊啊啊~哦哦哦❤️~夫…夫君❤️~”
“哈哈!夫君今儿个就给你松松穴,好好疼爱疼爱你这美妻子小穴!”
魁梧壮汉挺起熊腰,大开大合长驱直入起来,入得淑云仰颈吐舌,骚浪喊叫不迭。
许淮山一边猛肏嫩穴,一边啪啪啪用力扇着她的大白屁股,宽厚有力的大掌左右开弓,扇得那雪白丰腴的美臀遍布红印,波浪层起,女人哪里受得了这般刺激,摇着头张着嘴,哇哇哇地浪叫着,桃花眼噙满了泪水,嘴里直呼“不要打了”,“要命了”。
许淮山哪里能轻易放过她,大棍一下一下狠插到底,“不要?你这骚娘们儿,屁股一挨打,骚屄就缩紧一下,不就是喜欢老子打你?嗯?”说着还加大了手头扇打的力度。
“快说!骚货是不是喜欢被打着屁股操骚逼?”
淑云早已在小穴和屁股的双重刺激下爽飞到了天边儿,又受男人赤裸粗俗的脏话羞辱,忍不住肉穴狠狠一绞,美臀一颤一颤再次陷入高潮,春水直流,抛开所有礼义廉耻骚浪地喊叫起来:
“哦哦哦❤️喜欢~❤️云儿喜欢❤️❤️❤️~”
“啪啪啪!!”汉子加大动作:“骚屄去得这么快?喜欢什么?说清楚!”
“哦~哦哦哦❤️~喜…喜欢…❤️云儿的小穴…”
“甚么小穴?文绉绉的老子可听不懂!”男人坏笑着打断道。
“啊啊…哦哦哦❤️~是…是骚屄❤️是小骚货的骚屄喜欢…喜欢淮山夫君的大肉棒❤️~骚货喜欢被…被夫君打屁股❤️边…边打屁股…嗯哦哦❤️~边…边操…边操骚屄❤️………”
………
经历了数轮征伐的美人终于像滩烂泥般跪趴在卧毯上,脸埋在软枕里,轻撅着腚,随余韵喘息一起一伏,布满红掌印的美臀和吧嗒吧嗒往下滴着白浊浓精的私处在昏黄的油灯下一览无遗,尚且扩张的穴口一时合之不上,扇贝一张一缩,无声地宣告着被男人完全地征服。
男人黝黑健壮的身躯冒着热汗,一脸餍足,单手撑地枕在一旁,视线停留在淑云那高撅着的美臀上,饶有兴味地欣赏着酣战过后的绝世美景。
谢淑云觉得许淮山这混不吝平时虽端着一派忠厚沉稳的模样,对自己算是尊重爱护,照顾有加,可一旦上了榻便暴露出恶狼本性,言语上羞辱自己,肆意对她施展调教,手段层出不穷,每次都换着花样弄的她死去活来才肯罢休。
虽然自己每每情到深处也是喜于他雄厚傲人的本钱,一次次在那根粗长滚烫的肉棒下意乱情迷,翻云覆雨后却往往只余惆怅和空落。
淑云其实是个很缺男人爱的人,已故的丈夫是否爱过自己?她说不上来。也许是爱的,但她没感受到。
在淑云看来,从前的丈夫对自己与其说是情爱,倒不如说是单纯的敬重。
他敬她是对他而言高不可攀的谢家千金,却阴差阳错二人结为夫妻;亦是敬她的正妻身份,敬她是他名义上的妻子。
别人夫妻恩爱那是相敬如宾,到了她这反倒真成了相“敬”如“宾”了!
淑云自嘲地想,至少丈夫待养在外面的那名女子与待自己是明显不一样的。
后来丈夫和那个女子之间闹得不明不白,她虽心有怨怼,却也不想过多理会。
她想的很通透,蒋家明媒正娶的是她;家族有地位,有恃无恐的亦是她。
凭她身份尊贵,秀外慧中,得族中长辈们偏爱,又有爹娘舐犊情深,若丈夫真纳了那女人,两人便好聚好散,自己带着唯一心爱的女儿一走了之,自立门户也照样肆意过活,无忧无虑。
那女人终究还是没能进蒋家的门,虽说自己未曾刻意阻挠过,大抵还是碍于自己身份,丈夫没胆量为了她与自己闹掰。
只后来二人是否私下里还有来往便不得而知了。
她知晓些风声,但不愿去管。
说到底,两人并未相爱,再细究下去与否,最后的结局也只是貌合神离和劳燕分飞的区别,没那个必要。
她终究是未曾体会过情爱,无论是肉体还是心灵,未曾被滋润过终是不知晓甘霖之美妙。
直到她遇到身边这个男人。
那个荒唐的夜晚,已是寡妇的她记不清因何事而借酒消愁,鸦羽般的睫毛湿漉漉,一颤一颤,忽闪忽闪,眼角挂着清泪。
但她并未醉去,眼睁睁看着威武如山的男人轻而易举将自己抱起,对着自己笑,丰神俊朗,不外如是,那灿烂笑容更似天上星辰般璀璨夺目。
偏偏是这么个英武男儿,话本里的英雄好汉,说出来的话却令人不寒而栗。
“哪来的美丽伤心人儿,真叫老子一见钟情了!”
浑厚的嗓音顿了下,突然压的很低很低,低的仿佛只能给她听见,他凑到她耳边说,“老子想肏你的小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