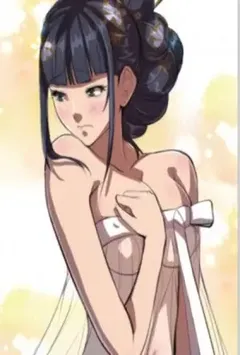这是酒吧最大的一个房间,与毗邻的房间一起,属于酒吧里两个不对外公开的包间。
宽大的房间里摆着铁笼、木架、玻璃箱、各种款式的皮鞭、铁链……还有四张不同型号的情趣床,就像是各种性虐用品的展览。
曲鸣出于好玩布置了这个房间,除了拿温怡试了试鞭子,一直没怎么用过,现在才算派上用场。
房间的角落里摆着一只木马,一个少女骑在马背上,她戴着眼罩,嘴里塞着一颗衔口球。
两条铁链从房顶垂下,夹住她红嫩的乳头,将她漂亮的乳房拉得向上挺起。
她两手背在身后,从肘部开始被一只长皮套绷住,迫使她两肩后张,以一个别扭的挺身姿势骑在木马上。
少女舌头被衔接口球压住,口水从唇角淌下,滴在白嫩的乳房上。
雪白的小腹下面,一根黑色的胶棒从木马背上伸出,深深插进少女下体,随着电机的嗡嗡声,在她体内不断进出。
南月已经在木马上骑了一夜,柔嫩的秘处整个红肿起来,木马背上湿漉漉淌满了淫液,颜色微微发红,似乎有鲜血的痕迹。
“蔡鸡拿来的兴奋剂真好,”苏毓琳摸了摸南月的乳头,笑吟吟说:“小妹妹在木马上骑了一夜,还没有晕倒呢。”
昨天曲鸣把辣素喷到南月体内,强烈的剧痛使她几乎昏迷。
然后蔡鸡给她打了一针,止了痛,又喂了她一颗兴奋剂——曲鸣常用的那种,使她有足够的体力接受一整夜的折磨。
那种新型的防身喷雾剂并不会给人体造成永久性伤害,但剧烈的痛苦足以让任何人痛不欲生,何况还是直接喷在最娇嫩的阴道内。
但南月并没有多少痛楚的表情,脸上反而带着迷离的微笑。
当曲鸣用针头刺进她的阴蒂,南月含着衔口球的嘴中发出一阵闷叫,两腿颤抖着,下腹喷出一股液体。她竟然失禁了。
……………………
景俪已经四天没有见到曲鸣了,甚至连电话也没有。
她越来越不安,上课也屡屡走神。
每次看到那两张空的桌椅,她心头就不由一紧。
景俪开始怀疑,那个男生是不是抛弃了她。
这个念头疯狂地折磨着景俪,使她坐立不安,直到一个电话打来。
“景俪老师,”一个女声温柔地说:“曲鸣同学想让你来酒吧一趟。”
不知什么时候起,苏毓琳成为曲鸣身边最亲近的女人,渐渐的,由她来召唤她们这些属于曲鸣的女人。
景俪顾不得多想,连忙说:“我这就去。”
苏毓琳轻笑了一声,似乎在讥笑她的急切,然后说:“他订了些货,在情趣店,麻烦老师带来。”
景俪已经习惯了情趣店老板淫猥的目光,但老板把那些奇形怪状的物品一样样摆在柜台上,一边冲着她嘿嘿直笑,景俪仍禁不住红了脸。
“小姐,知道这个是怎么用的吗?”
老板拿出一只生满毛发的皮圈,穿在手指上,做了个猥亵的动作,“这叫羊眼圈。配上这个,能让小姐你爽翻天。”
老板把一支女用催情素递给景俪,趁机在她手上捏了一把。
景俪皱了下眉头,货物里除了几样器具,最多的就是各种催情剂,有口服的药丸、药片、溶液,还有外涂的油剂、药膏、药粉。
还有一盒没有贴标签的注射剂,瓶身比一般针剂大了许多,里面透明的药液略显混浊,显得很粗糙。
老板不怀好意地盯着景俪说:“这个很厉害的,用之前要多喝点水。要不然的话……”
景俪没有理他,匆匆付过款,收拾好物品,就离开了情趣店。
老板盯着她的背影,心里阵阵发痒。
那个男生真是狗屎运,竟然弄了这么多美女。
而且玩起来还真狂猛。
那些催情剂,足以令圣女变成娼妓。
“南月?”很少有人会忘了那个女生。
曲鸣点点头,“她在这里。”
景俪隐约明白了一些。
也许曲鸣是把那女孩儿叫到这里,想用强奸药来迷奸她。
景俪知道这样做不好,对南月来说是不公平的。
她肯定曲鸣也很清楚,用药物使女方失去反抗能力,强行发生性关系是犯罪行为。
但既然曲鸣想做,那就没错。
“她不愿意吗?”
曲鸣冷冷说:“她很愿意,都不想回去了。”
“是吗?”景俪不大相信。
曲鸣这间酒吧是提供色情服务的场所,南月作为滨大学生,而且是品貌学业兼优的知名女生,怎么可能留在这里。
曲鸣赤着身体坐在沙发上,右手枕在脑后,“她现在虽然很乐意,但小女生很容易改变主意。说不定过几天她又不想做了——那样会很麻烦。”
不需要再说下去,景俪已经明白了,曲鸣是想让南月没办法再回头。想到那个风姿脱俗的古装少女,景俪微微觉得惋惜。这样做,有些可惜呢。
“景俪老师。”一个女声打破了房间的沉默。
苏毓琳穿着一身粉红的护士装,还戴了护士帽,只是那条短裙短得夸张,只勉强盖住臀部,露出两条白光光的修长美腿。
她拿着一只白色的医用瓷盘,里面放着一支注射器,一把长柄镊子,还有一瓶消毒用的酒精。
“这么早就来了啊。”苏毓琳打量着她,含笑说:“景俪老师越来越漂亮了。呢”景俪有些窘迫地掩住裙底,苏毓琳还是个未毕业的女生,但那双带着几分妖媚气质的眼睛,却让她显得比真实年龄更成熟。
苏毓琳笑着说:“今天晚上的针,老师给她打吧。”
景俪怔了一下,“谁病了吗?”
“蔡鸡。”曲鸣说:“昨天感冒了。”
苏毓琳笑了笑,领着景俪来到蔡鸡和巴山住的房间。
巴山一个人坐在床上,正用哑铃锻炼手臂的肌肉。随着他粗重的呼吸,健壮的肩膀上肌肉不住隆起,上面是一层发亮的汗水。
看到景俪,巴山扔下哑铃,毫不客气地抱住她,在她圆翘的屁股上用力捏了一把。
红狼社的几个女人中,巴山对景俪最感兴趣,因为她肉体更成熟,也更能承受他的重压。
至于杨芸,倒是和蔡鸡更合适。
“鸡哥呢?”苏毓琳拿着托盘问。
巴山搂住景俪狠狠亲了一口,又捏了捏她的乳房,弄得景俪脸上发红,身子发软才松手,“在卫生间。”
楼下是酒吧的公用卫生间,一进去就听到蔡鸡连串的喷嚏声,“啊嚏!啊——嚏!”
蔡鸡扯下一团卫生纸,用力揉着鼻子说:“这是男厕,你们进来干吗?”
蔡鸡对苏毓琳一直没好感,这个女人太妖了,他不喜欢。
苏毓琳笑吟吟说:“我找南月,该打针了。”
景俪这才注意到蔡鸡手边翘着一只又白又嫩的屁股。
一个女生趴在马桶旁边狭小的空间里,撅着臀,臀沟下方柔嫩的阴唇朝两边软软张开,露出一个小小的肉孔,那圆孔红红的向外鼓起,彷佛有些充血肿胀。
蔡鸡大力擤着鼻涕,然后把用过的卫生纸捏成一团,随手按到少女的肉穴里面。
那女生撅起屁股,就像一只处理废弃物的垃圾筒,蔡鸡粗鲁地撑开她红而柔嫩的蜜穴,将那团沾满鼻涕的卫生纸塞进她体内。
景俪情不自禁地掩住口,脸上露出作呕的表情。而更令人恶心的还在后面。
蔡鸡把她们赶出去,然后说:“出来吧。”
隔板内传来一阵响动,接着门被推开,露出一张娇羞的面孔。
南月四肢着地趴在卫生间肮脏的地面上,白滑的身体赤裸着,只在腰间系了一条鲜红的绸带,像一件漂亮的礼物。
她半具身体露在门外,含笑挺起腰,将白嫩的屁股翘到那个坐在马桶上的男生面前。
苏毓琳啐了一口,“鸡哥最坏了,把女生当马桶。让南月妹妹的小肉洞吃你的大便纸。”
蔡鸡让南月撅起屁股,把用过的手纸塞到她白嫩的屁股里面,“骚女就喜欢用小肉洞舔我的大便纸,是不是?”
南月漂亮的脸上露出红晕,腻声说:说:“人家是贱母狗,被鸡哥这样玩,好兴奋呢。”
蔡鸡塞完,随手拿起旁边的马桶塞,把木柄插到她阴道里面,用力捅了捅。
南月一手掩住下体,眉头拧紧,发出一声含羞带痛的媚叫。
景俪发现她两只乳头像被人捏肿一样,红红的向上翘起。她的表情也非常奇怪,被人这样虐待,她似乎并不反感,而是很满足的样子。
蔡鸡提起裤子,在南月屁股上踢了一脚,“爬几圈。”
南月已习惯了被人这样玩弄,她赤裸着身子在卫生间里爬着,不时翘起屁股来回扭动。
她白嫩的圆臀间插着一根肮兮兮的马桶塞,夹着木柄的嫩穴湿湿的,似乎在滴着水。
景俪心头一阵发紧,扭过脸不忍再看。苏毓琳含笑说:“老师别担心,南月小妹妹最喜欢这种游戏了。”
她把托盘放在洗手台上,一边戴上医用的橡胶手套,一边对南月说:“小骚女,一边手淫,一边告诉景俪老师你的性幻想是什么。”
南月伏在地上,一手摸住乳尖,一手伸到腹下,揉弄着红肿的阴户,低喘着说:“我是个最低等的畜奴……每天都要被主人们使用,主人会很变态地折磨我,越变态,我就越兴奋……像这样把异物塞到我阴道里面,把我的小肉洞当成又脏又臭的垃圾筒……我觉得自己好贱……呀——”苏毓琳戴好手套,笑吟吟拿住马桶塞,用木柄戳弄着少女溢血的嫩穴。
南月“呀呀”的痛叫着,颦紧弯长的眉毛,那只白嫩的雪臀在木棍捅弄下颤抖着,她捧着屁股哀求说:“主人,贱奴再也不敢了……”
蔡鸡把手掌伸到景俪裙下,摸弄着她大腿间光滑的皮肤,朝南月呶了呶嘴,“怎么样?够贱吧。”
景俪惊讶地扬起眉毛。
她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滨大有名的才艺女生,潇洒脱俗的美貌少女,竟然还有着这样不为人知的一面。
在她骄傲而华丽的外衣下面,却在渴望被人用最粗暴最下流的手段虐待。
杨芸已经足够令她惊异,但即使那个滥交的小女生,也不会喜欢用阴道装纳用过的手纸。
蔡鸡嘿嘿笑了起来,“大美女,把骚女的屄洞清空。”
苏毓琳拔出木柄,让南月爬到洗手台上,张开腿。
南月下体的毛发已经被清理干净,露出白嫩的阴阜,微肿的穴口像婴儿的小嘴一样张开,里面淌着鲜红的血迹。
苏毓琳戴着橡胶手套的手指伸进南月圆张的穴口,在她肉洞里掏摸着,拿出那团带血的手纸,放在金属托盘里,接着从少女体内里掏出一只手套,然后是吸过的雪茄烟头,吃剩的果核,几团塑料的包装纸,揉扁的烟盒……
少女娇嫩的阴道被当成一只垃圾筒,塞满了肮脏的废弃物。那些物体一样一样放在白色的医用瓷盘中,上面带着湿黏的体液和零乱的血迹。
在男生戏谑的目光下,南月阴道慢慢被掏空,苏毓琳撑开她的穴口,把镊子伸到她穴内,镊出塞到阴道深处的肮脏物品。
从撑开的穴口,可以清楚看到她阴道受过严重的创伤。
景俪无法想象,那样一个优雅美丽,而又骄傲的古典少女,怎么可能会把那些肮脏的垃圾塞进自己阴道里?
但南月却是媚眼如丝,撅着臀,不时发出柔媚的低叫。
最后从阴内取出的是几团药棉,那是用过后塞到南月身体里的,白色的棉絮已经被鲜血浸透,变得发黑,彷佛一团团滚落的血肉。
景俪侧过脸,几乎不敢去看。
苏毓琳笑着说:“那么脏的东西,好恶心呢。”
景俪心头一阵发麻,忍不住说:“不怕感染么?”
“老师忘了,南月妹妹是学医的。”苏毓琳笑吟吟说:“每天都要消毒,还要打消炎针。”
苏毓琳熟练地拿起注射器,在南月腹下打了一针。然后用药棉蘸过医用酒精,把镊子递给南月,让她自己清理阴道。
南月把带着酒精的药棉放在穴口,顿时痛得身体抽紧。
连旁边的景俪也情不自禁地颤抖了一下。
她当然知道那是女人最柔嫩的器官,平时洗浴时都很小心。
何况是直接用酒精擦洗受伤的阴道里,那种痛楚是任何一个女人都无法承受的。
那团湿湿的药棉夹在南月红肿的穴口,她抬起眼,央求说:“给小母狗打一针好吗?”
苏毓琳看了蔡鸡一眼。蔡鸡耸了耸肩,从口袋里拿出一只小小的药瓶。
白色的粉末混入水中,随即溶解消失。
苏毓琳用酒精棉球在南月大腿根部消过毒,然后吸了溶液的把注射器,刺进她腿根。
从景俪的角度,能看到她腿根还有两个细小的针孔,显然已经不是第一次注射了。
南月明亮的大眼睛蒙上一层水雾,变得朦胧起来。
她低低喘息着,把镊子伸到阴内,清理着阴道里的污物。
那足以令人疯狂的疼痛彷佛消失了,酒精在伤痕累累的阴道内擦拭着,血液像火一样奔突,传来阵阵无法言说的激感。
蔡鸡伸手抚弄着南月白嫩的阴阜,嘲笑说:“感觉是不是很HIGH?”
南月露出迷离的笑容。
蔡鸡扯住少女的阴唇拽了拽,对景俪说:“你现在砍她一刀,她都不知道痛呢。”
南月洗净阴道内的污物,然后拿药棉把下体擦拭干净。
擦洗过后,她美妙的阴部又显得娇美可爱,柔嫩的阴唇微微张开,湿淋淋带着酒精的味道,在灯光下散发着红嫩的光泽。
景俪用力掐着自己的手腕,想到这个洁净不染纤尘的女生撅着白嫩的雪臀,让人把用过的垃圾塞到她受伤的阴道里面,心头不禁阵阵战栗。
但看到曲鸣龟头的伤势,景俪对南月那点同情和怜悯顿时化为乌有。无论如何,南月都不该踢伤他。
“怎么会这样?”景俪惊讶地说。
曲鸣不耐烦地推开她,心里彷佛有团火在烧。
两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曲鸣开始服用禁药。
最初只是助长肌肉,增强体力的类固醇,使他迅速变得强悍有力。
在高中球员里,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紧接着,曲鸣又接触到一种比赛型的兴奋剂。
这种兴奋剂可以最大限度的延长体力,使运动员在整场比赛中都保持充沛的体能。
对于篮球这种高强度对抗的运动来说,体能甚至比技巧更重要。
所以曲鸣能够一对一在球场上击败周东华。
但兴奋剂同时也导致性欲亢奋,和景俪在一起时,他每天都需要性交三次才能满足。
这些天曲鸣倒是结结实实禁了四天欲,算是他从十五岁以来最长的一次。
“老妈让我找个女朋友。”曲鸣说。
景俪已经听他说过一次,这会儿听到心里还是一沉,酸酸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我今天晚上要带女朋友回家吃饭。”
景俪眼睛亮了起来。
“已经答应过,推不掉。”曲鸣有些不乐意地说:“我带苏毓琳回去。”
景俪怔了一会儿,“那我呢?”
“你在这里陪蔡鸡和大屌。”
景俪眼中的光亮黯淡下来。
曲鸣没有看到她的眼神,即使看到也不会在意。对他而言,这个女教师就和一个应召女郎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在于她是免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