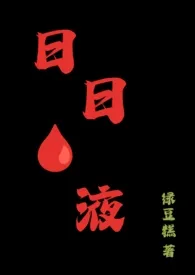“是她吗?”
方季峰瑟缩地点了点头。他嘴角肿了起来,手背上有电击过的伤痕。显然那些警察对他不是很客气。
“赵太太,”警察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有人指控你唆使犯罪,希望你能配合警方。”
宫韶兰仪态万方地站在门前,还没有开口,那名警察就拿出手铐,铐在她动人的手腕上。
听到手铐声,方季峰身体反射般地一抖。尽管宫韶兰一万遍告诉自己要镇静,此时也不禁颤抖起来。
“你们找错人了。”宫韶兰说:“我不认识他。”
一直不敢接触她目光的方季峰抬起头,难以置信地看着她。
宫韶兰尽力装出冷漠的表情,傲慢地扬起下巴,看向他的眼神就像看着一只肮脏的流浪狗。
方季峰发青的面孔猛然涨得通红。
警察并没有理睬她的辩解,他们闯进室内,在里面四处翻检,追查赃物的下落。
宫韶兰闭上眼,庆幸自己在警察到来之前,已经用掉了最后一点安琪儿。
警方并没有找到他们想要的结果。
在警局的质询中,宫韶兰一口咬定自己与方季峰素不相识,更不知道什么戒指。
审讯持续了三个小时,最后宫韶兰作为嫌犯被暂时拘禁。
冰冷的铁栅,充满肮脏气息的座垫,狭小的空间……还有压抑不住的恐惧和忐忑。这场经历让她永生难忘。
黎明时,一名警察打开铁门,对她说:“你可以走了。”
宫韶兰将信将疑地离开拘禁室,一名律师起身说:“赵太太你好。我是林先生私人律师。”
宫韶兰紧悬的心微微安宁一些,她脱口说出已经重复过无数遍的话:“我不认识他!”
“是的。”林俊生的律师面无表情地说:“这只是一场误会,我已经向警方已经解释清楚了。”
宫韶兰紧绷的身体终于松驰下来,如果她被定罪……她简直不敢想像自己被投入监狱。
宫韶兰露出一个苍白的微笑,“俊生呢?”
律师擦了擦眼镜,重新戴好,“林先生奉老先生的委托,已经在昨天午夜飞赴国外。”
宫韶兰仿佛听到体内传来瓷器碎裂的声音,“什么?”
“同行的还有林太太。老先生希望林先生能与林太太相处一段时间,大概一年。”律师含蓄地说。
宫韶兰突然明白过来,“是因为今天的事吗?”
律师没有否认,“陈太太对自己的被窃很生气。林先生也很难做。幸好现在误会已经消除。俱乐部的一名侍应生承认是他盗窃了物品。退还了赃款之后,大概要面临三到七年的刑期。”
宫韶兰心知肚明,方季峰根本没有能力偿还那只戒指的款项。
虽然从一开始,她就筹划过这样的结局,但想到方季峰那被污辱和欺骗的怨毒眼神,她还是禁不住心里一颤。
“我该告辞了,赵太太。”律师向她点了点头,忽然像又想起了什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只盒子递给她,“这是林先生给你的。”然后转身离开。
那是林俊生曾用来向她求婚的戒指盒。盒子里,装着陈太太那只失窃的戒指。
……………………
“赵太太,”飞哥直起腰,揶揄说:“真是稀客啊。”
宫韶兰从手袋里拿出钞票,一言不发地放在桌球台上。
“有钱了?”飞哥看了一眼,嘲弄说:“不会是用别人戒指换来的吧?”
宫韶兰手指僵了一下。
“你以为有什么能瞒过我吗?”飞哥用球杆挑起她的下巴,“还真行啊。一边诱奸小男生,让他偷东西还替你坐牢,一边还下钩钓金龟,真是好手段啊……怎么样?现在鸡飞蛋打,又来找我飞哥了吧?”
宫韶兰矜持的伪装被他残忍地撕开,泪水顿时涌了出来。她就像一只陷入泥淖的蝴蝶,一次次竭力飞起,却被沾了泥水的翅膀重新坠入泥中。
飞哥欣赏着她梨花带雨的艳态,一边把她推到桌球台上,扯下她的内裤,把她长而白滑的双腿架在肩上,狠狠干入。
宫韶兰凄痛地哭泣着,赵晋安的失踪,毒瘾的发作,冷眼,饥饿,遭受的淫辱,被粉碎的希望……瞬时间涌上心头。
如果死亡能让这一切解脱,她宁愿立刻去死。
一股异样的热感从下体升起,宫韶兰仍是泪眼婆娑,肉体却已经在她意识来临前变得兴奋。
七彩的圆球从天而降,内心的酸楚、伤痛被潮水般涌来的欣喜所淹没。
刚才种种使她痛哭的往事变得像烟一样轻淡。
没有什么再值得她在意,除了身体无比美好的感觉……
那具美艳的肉体在桌球台上扭动着,白腻的肌肤白艳令人心动。
理着寸头的男子架起她光洁的双腿,粗暴地在她体内狠狠抽送。
那艳妇兴奋地迎合着他的进出,娇艳的脸上犹有泪痕,眉梢眼角却尽是无法掩饰的狂喜和淫媚。
……………………
宫韶兰没有获知方季峰的刑期。她再次搬了家,并重新换了号码。仅有的希望已经失去,她仍想重新开始。
陈太太、林太太、姚小姐……和赵晋安一样,都在她生命中消失了。始终,林俊生是与她无缘的。同样宫韶兰没有再得到他的任何消息。
那些人,那些事,从她身边匆匆走过,没有停下来看她一眼。
宫韶兰再次变卖了那只戒指,拿到的款项并没有让她支持太久。那些纯白的安琪儿就像一只无情的吸血鬼,榨干了她仅有钱款。
泣丧,羞辱和无力感不时充塞心头。只有安琪儿的羽翼才能带给她渴望的温暖和满足感。
就在这样的循环中,宫韶兰在安琪儿的梦幻中越陷越深,直到她手里的钱款再次告罄。
飞哥对她的态度越来越恶劣,也越来越冷漠。
即使此刻她跪在地上哀求,飞哥也没有动一动眉毛。
而平时还能给她一点折扣的阿威,这回也一言不发,摆明了要看她好看。
宫韶兰沉浸在无比的恐惧中,她最怕自己的身体对飞哥丧失了吸引力。
这一天到来时,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惶恐中,宫韶兰甚至没有意识到宋狗进来的声音。
“飞哥,你找我?”宋狗并不吸毒,但看上去就像重度成瘾的吸毒者一样干瘦而猥琐。那张又黑又黄的脸,宫韶兰第一次见就觉得恶心。
飞哥拿球杆敲着桌台,对宋狗说:“这位你认识吧。赵老板的太太,有钱人家的阔夫人。可惜赵老板跑了,除了口粉瘾,什么都没给她留。”
宋狗打量着那一身名牌的美艳妇人,不知道飞哥是什么意思。
“这会儿赵太太想要粉,手里又没有钱。你要有呢,就当做好事给她一口,没有就算了。”飞哥说完,又埋头打球。
宫韶兰唇角蠕动了一下,喉咙却干得却说不出话来。
宋狗自然是认识宫韶兰的,只是他没想到飞哥会这么大方,上次飞哥也这么说过,后来却没了动静。他有些拿不准地说:“飞哥——”
飞哥摆了摆手,“出去商量吧。”
宋狗大喜过望,连忙出去。到了门口,不见宫韶兰出来,他回头说:“走啊!”
宫韶兰又看了面无表情的飞哥一眼,只好垂下头,跟在宋狗身后。
宫韶兰以前都是从后门进出,还是第一次见到前面的景象。这是一个陈旧的老式院子,前面几间裸露着水泥的房子透出昏暗的灯光。
房间里弥漫着呛人的烟味,灯光很暗,几名光着背脊的小混混正在灯下打牌。
隔壁,一扇被人踹坏门锁的门半开着,油漆脱落,露出发黑的门板。
宋狗没有进房去打招呼,领着宫韶兰到了隔壁。
房里扔了一排破旧的沙发,不知有多少人坐过,上面沾满污渍。
宋狗打开灯,脚下忽然一跘,差点儿摔倒。
“肏你妈的死婊子!”宋狗破口大骂。
地上趴着一个半裸的女子,她似乎刚跟人做过爱,白白的屁股上还沾着精液。
她头发散乱,那张苍白而瘦弱的脸看上去还很年轻。她打了个呵欠,口齿不清地说:“宋狗哥……”
“快滚!”宋狗连踢带推地把她赶出去,骂咧咧地说:“这死烂泥妹,打了针就躺在这儿。”
虽然知道要发生什么,宫韶兰还是有些紧张。宋狗回头看着他,丑陋的脸上露出一个猥亵的笑容。
“知道什么是烂泥妹吗?就是谁给她粉,她就跟谁睡觉,圈子里谁想上就能上,比鸡还贱。”宋狗说着呸了一口。
宫韶兰喉头哽了一下。
宋狗坐在沙发上,打量着宫韶兰,阴阳怪气地说:“赵太太,飞哥说你有事跟我商量?”
宫韶兰有些吃力地说:“我……我想借点粉用。明天就还钱给你。”
宋狗掏着鼻孔说:“这可不好办啊。货都是有数的,给了你我就得垫钱。赵太太,咱们没什么交情吧?况且……”
宫韶兰放下贵妇的架子,软语央求说:“宋狗哥,那次是我的不是,请你原谅。”
宋狗贼兮兮地伸出手,“还没摸到,就挨了你一耳光。什么奶子这么金贵?”
这会儿已经到了用药的时间,宫韶兰一阵一阵心悸,她顾不得矜持,连忙拉起衣服,角下乳罩,那对傲人的乳球立刻弹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