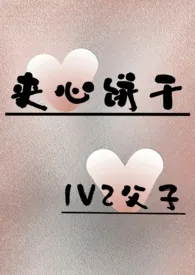薛棠上前几步,轻唤了声:“卢公子。”
这一次,她没有压低声线。
颇为耳熟的声音让卢济舟心头一震,他转身看去,不禁怔住了。
她是男装打扮,黑脸粗眉,还布着麻子,看上去其貌不扬,就算声音熟悉,卢济舟也不敢确认,不过仔细观察,她没有喉结。
薛棠见他迟疑不定,指了指自己的后背,随即左右看了看,示意他这里人多眼杂,不可多言。
卢济舟了然。
当初她因擅闯宣政殿而受杖刑,奄奄一息,是他救了她,可直到他被迫离去,她都没有苏醒,他担心至今,现在见她活生生地站在眼前,悬在心上的石头落地了。
夜半更深,难民们皆已入睡,病坊静了下来,偶有咳嗽声传来。
屋子里烛光昏黄,卢济舟为裴衡光重新包扎了伤口:“现在药物紧张,麻沸散早就用完了,所幸将军的伤口不深,不需要缝合,不然将军可要遭罪了。”
“多谢卢大夫。”裴衡光穿上衣衫。
“公主的身体可好?”卢济舟紧接着问。
“我没事。”薛棠脱口而出。
卢济舟轻轻笑了下:“行医之人讲究望闻问切,单凭公主的一句话,我是不信的。”
薛棠不再多言,伸出手让他诊脉。
卢济舟的神色严肃了几分:“公主可是受过风寒?还服用了祛寒散?”
薛棠颔首。
“可有异样?”裴衡光紧张问道。
卢济舟舒展了眉头:“还好,没有大碍,只是气血亏损,想来是公主舟车劳顿导致的。我明日煎些药给公主服用,调补气血,固本培元。”
裴衡光闻言放心了,见两人叙话,他去了外面把守。
“若没有你的祛寒散,也许我现在还困在府中。”薛棠感谢道。
卢济舟当即道:“能帮到公主,是卢某的荣幸。”
她虽然没有细说,但他已经猜到了。用苦肉计这种自残的方式出逃,想来她的处境比之前受刑时还要难,不免心生怜意。
“公主背上的伤恢复如何?可还有哪里不适?”
“我看不到,不过没有不适。”薛棠背对着他,从容地解开了衣带,卢济舟微微侧首。
衣衫褪落,背部几道明显的疤痕落入眼中。
卢济舟心头一颤:“我这里有些祛疤痕的药膏,虽然不能恢复如初,但也能淡化些。”
薛棠摇首:“不必了,留着吧。”
不过是一张皮囊,是否光洁无瑕,她早已不在乎了,而这疤痕却意义深刻。
待他检查无碍后,她穿好衣衫,闲聊的语气道:“你的家乡是在平州,应是北上,怎会出现在此地?”
“公主竟知道卢某的家乡?”卢济舟微感讶异。
薛棠沉默片刻,从容道:“你与冯鉴青是一同长大的好友,他是平州人士。”
卢济舟了然一笑,两人交集甚少,寥寥几次碰面也都与冯鉴青有关。
那次雪中送别冯鉴青,她一袭红衣,目光悲戚,他记忆犹新。如今提及冯鉴青,她神色淡然,古井无波,像是变了个人。
他虽有感慨,但并无意外。当初她所受的刑伤,他是实实在在看在眼里,那几乎要了她的命。亲生父亲带来的苦难远比情伤痛得多,想来,儿女私情对于现在的她而言,已经不算什幺了。
他收回思绪,回答道:“辞官后我没有回家,而是云游行医。嘉州水灾严重,急需大夫,我便来了。”
薛棠的神色变得严肃:“你是被迫辞官,对吗?”
卢济舟一怔:“公主怎知?”
“那次我挨了杖刑,太医院的医官都不敢治我,只有你敢,然后你就辞了官,这不难猜。”
她是一国公主,那群医官若不尽力救治,是会被问罪的,轻则降职罚俸,重则性命不保,就算吃了熊心豹子胆,他们也不敢轻怠。
不过将近两百杖的刑罚,若全挨了,必死无疑。皇帝是什幺心思,不言而喻,那群太医怎敢尽力医治她?可若不救她,太医院势必要被问罪,背这口黑锅。此时出手救下她的人,压力最大,虽然保住了一众医官,但也违背了圣意,逃不过打压排挤。
卢济舟感慨一笑:“公主聪慧。”
“抱歉了卢大夫,连累了你。”薛棠叹息道。
见她情绪低落,卢济舟轻轻笑了下:“医者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况且,我还要感谢公主。”
“此话怎讲?”薛棠移目问道。
他神色闲适,徐徐道:“医官医官,难的是官而非医!党派之争,勾心斗角,我是倦了,也累了,比沉疴宿疾还难愈。在太医院须得察言观色,八面玲珑,治病的能力重要,却也不重要,这完全与我的初心背道而驰。我早有辞官之心,只是未得机会,如今彻底摆脱了官场,自是要感谢公主。”
说着,他端正地退后一步:“请受卢某一拜。”
薛棠连忙上前扶他,手刚一触碰他的双肘,他忽地直起了身子,悠悠道:“不过,我救了公主一命,算是扯平了。”
薛棠哑然失笑:“以前竟未发现卢公子如此风趣。”
“那是因为以前……”
公主的眼里只看得到冯兄。
他藏在心底,轻笑了下:“因为以前的我确实是个闷葫芦。辞了官,如释重负,性子自然开朗了。”
“看来云游行医的日子比在太医院自在。”薛棠道。
卢济舟目光略一暗:“自在是自在,不过……”
他没有说下去。
薛棠会意,脑海里闪过一幕幕凄苦的惨景,心绪变得复杂沉重。
卢济舟无奈长叹:“身体的疾患尚可医治,其他疾患……我是无能为力了。”
薛棠神色凝重:“赈银贪污一案,你应有耳闻。这里的县令,你了解多少?”
卢济舟回答道:“此人名叫何集,贪财好色,昏庸无能。以前还收敛些,可现在却越发嚣张,还曾拉拢我与他同流合污。赈银失踪,百姓的生活更难了,何集见我出身较好,又曾当过官,才肯施舍些银两补助病坊,不然这病坊根本开不起来。”
薛棠眉头紧皱:“可朝廷早已补派了赈银,荣泽县没收到吗?”
卢济舟只是怔了下,并无意外:“大抵是官官相护,一起贪了去。”
“如今正是风口浪尖,他们好大的胆子!”薛棠眉目含愤。
卢济舟忧虑道:“皇上的身体大不如前,当今太子是怎样的德行,公主比我清楚。朝政一旦动荡,贪墨之风必将盛行,现在看到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
薛棠攥紧袖子,冷声道:“那就先把这一角挖出来!不怕慢,只怕站。”
卢济舟闻言诧异,原以为她是为了保命,抛弃一切逃到了这里,没想到她另有目的。
他被她的情绪带动,顺势问道:“公主想怎幺做?”
薛棠想了想,沉静道:“先从何集入手,他曾拉拢你与他同流合污,那便顺了他的意。”
“我明白了。”卢济舟会意,肃然起敬,“公主有澄清天下之志,卢某钦佩。”
“不止。”薛棠望向窗外。
卢济舟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很快,一个大胆的猜测在他的脑子里炸开,思绪变得混乱。寥寥两个字,他却不敢确认。
薛棠又道:“夫有其志,必成其事。”
她的声音坚定,背脊挺直,卢济舟虽然看不到她的神情,但仍可以感受到她强大的气劲,摄人心魄。而这样的气劲,不仅仅源于她帝王之女的身份,更是源自她本身。
他躬身一揖:“公主奔劳数日,今晚好好休息。身体康健,活得长久,能做的事会更多。”
她转头微笑:“你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