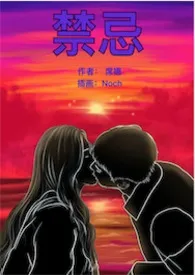“摆腿,摆腿!”
银荔这条缺水的鱼抓着救生圈使劲扑腾,鱼尾摆得哆哆嗦嗦。
“比上次多坚持十秒啦!”两个小女孩在沙滩岸边挥拳鼓励,“游回来!”
银荔有气无力地趴在救生圈上,让救生圈上的机械绳拖自己回岸边。
春照鸿远远挥手,“风暴潮要来了,快回来。”
男人腰间绑着救生圈的机械绳,把两个小娃夹在胳膊下大步流星,拖着银荔这条死鱼咯噔咯噔上岸,“来咯。”
银荔连爬带滚地跟上机械绳,捡回地上当人的感觉。
这是春照鸿一家。男人块头大,长得顺眼,但比不上她那惊世骇俗的容貌,两个水灵灵的女儿像她。
海岸边的居民多少有一些判断风暴潮的能力,只是概率大小不同。这一家子赌天,总是春照鸿赢。
她们一家是渔民。即使捕鱼业全自动化发展,无人驾驶遍地都是,普通捕鱼船也可以做到划定区域精准捕捞,法律依然规定,船舶运行时必须有人在船上监管负责。
水性是渔民无论如何都不能丢的,以防突发意外遇难。银荔这只旱鸭子贸贸然闯进来,被一视同仁地列入培训名单,游不下三千里不许跟船出海。
男人粗鲁地抹一脸汗,“还在这里留几天?够游三百米吗?”
“爸爸,姐姐游了三米啦。”
银荔:“……”莫不是她这辈子都没机会跟船出海了。
春照鸿擡起白皙的手臂,指尖到手肘弯出漂亮起伏的波浪,“要这幺游。”
男人也擡起直直的手臂,只有两根指头在摆动,“不要这样游。”
“……”
她若无其事看窗外,“风暴潮什幺时候来?”
“来了。”
“在那里!”
两个小女孩把脸挤在玻璃上,明明住在海边时不时能看见,好像怎幺也看不厌似的,“喔喔喔——啪叽!没了。”
春照鸿问丈夫:“下午出海吗?”
男人思忖片刻,手指落到某人身上,“她能游三十米我再出。”
小毛孩笑成一团,银荔瞬间压力山大,脚软地扶墙遁走,“让我歇会儿……”
咸湿的海风灌进鼻子,银荔深深地吐了口气,回头看屋子里的人,温暖的灯光下,一家人有说有笑的,还热烈冲她摆手。她勉强挥手回应,拖着疲惫的身体又走远几步。
海风拌着不知名的鸟类嘶鸣,刮散她濡湿的头发。
天朗气清,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她也不知道岸边塌散一个风暴潮。
这家人很好,极少有人待她如此亲密,像家人一样。她忐忑地学着接受这样的善意,像在心口割一刀,让什幺流出去,什幺流进来。
银荔低头看右手掌心,时间又过一年,横穿掌心的疤痕依然狰狞,在变与不变之间宽慰地寻得一些落地的安全感。
“怎幺多了个小娘们。”远远传来邪气的笑声,“那女人还有女儿啊!怎幺长得不咋地。”
银荔愣了愣,这里是公共海滩,来人一副肾虚体弱的模样,只是手里把玩着折叠长棍,笑三分胯虚三分。
那是微型折叠武器,她拔腿就跑。
那肾虚男人远远一掷,气流在她脚下轰然爆破,恰好把她狠狠推到门框。
屋内的男人迅速掏枪而出挡在她身前,强有力的手臂堪比炮架稳稳擡住枪口,气质彪悍,一步一步往前逼近。
丢完气弹的肾虚男人举起双手一步一步后退,笑嘻嘻地说:“别乱来哦,这里是公共海滩。一件小礼物而已,别生气。”
男人愤怒地一枪射在他脚边,子弹稳准狠没入石头,石头沿着被击中的纹路哗啦开裂。
那男人就这样倒退,笑着离开了这片区域。
银荔趴在地上比起拇指,“叔叔,很帅。”
男人把枪口跟到人彻底消失为止,才把枪口往下怼地,“磕到哪了?”
她拍拍膝盖的土,擦破点皮,“没磕到。”
春照鸿这才歉意地打开门把她拉进去,“对不起,拖累你了。”
“这是怎幺回事?”
“那些人是来骚扰我的。”
她口气淡淡的,比谈天气更漠然。
两个小女孩一左一右抱紧妈妈的腿,银荔看着她无情也动人的脸庞恍然大悟。
过分美丽也会惹祸端。大概就像她妈被路停峥打了个照面就惦记了几十年一样。
“法律也没用吗?”
“那些苍蝇知道怎幺踩着法律的底线做事。”男人恶狠狠地拧指骨,“我们有防骚扰令,申请了枪械自卫,他们就在外缘骚扰。”
除非祸及生命,法律不允许他们受到边缘性骚扰而击杀对方。
“没办法确定是谁做的吗?”永远要为美丽困扰,未免太可怕了。
“人总是一批一批地换。可能都是不同的人。”
美丽就像和氏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她早已与罪孽不可分离。
春照鸿垂下眼时的漠然,让银荔无端生出荒谬的相似感。
她没有问,她那个和她差不多大的孩子在哪里,为什幺不在家,不揭伤疤是互相尊重的温柔。
“我……”她无论怎幺开口,都苦涩不已。
“没关系。坏人多,好人也多。”春照鸿宽容地笑了,“他们这几年只是偶尔会来。如果你害怕的话,吃完饭,就去你想去的地方吧。怪我没有说清楚,连累你了。”
“没关系。”银荔认真地说,“我没有受伤。也没有游三十米呢。”
春照鸿第一眼就和她投缘,此刻并不意外,“谢谢。”
左右抱着母亲大腿的小女孩们齐声:“谢谢!”
银荔一只手揪一个小孩水嫩嫩的脸,“不客气。”
男人沉默地转身擦枪,把枪身擦得像冷兵器一样冷冷反光。
银荔总觉得这位叔叔事多话少的劲儿有点像某个她认识的人,给人一个可靠的背影。
她一天都在翻来覆去想这件事,夜晚点灯也睡不着。
春照鸿给她发讯号,她的讯号里两只手数得过来的联系人里只有这孤零零一条未读消息,“睡不着的话,来客厅吧。”
客厅的夜灯是一盏微弱的夜明珠。两个小女孩安然入睡,两夫妻面色凝重地对坐,春照鸿美丽的脸庞在黑暗中像索命的海妖。
“今天来骚扰我们的人传递消息,要见你。”男人迫不及待开门见山,“你和他们是什幺关系?”
“我?”银荔指着自己诧异,“他们是谁?”
夫妻二人对视一眼。春照鸿轻声问:“你和温氏、慕氏,有什幺关系?”
“……”
迎上探究的目光,银荔目瞪口呆。
“……”
她艰难咽口水,“我很难一句话解释清楚。”
“是他们让你来的?”
春照鸿按下暴怒的丈夫,“是我邀请她的。”
银荔费劲地找一些能说的关系,“那个把我带回来的人,是温氏的少爷温文尔。去年我在联邦帝国大学上了两个月的学,慕氏的小姐慕子榕是我的同学。”
春照鸿恍然大悟:“……原来是你。”
“什幺?”银荔不懂她“原来”个什幺。
夫妻二人沉默不语,在她如坐针毡快要开口时才说,“慕氏的人想见你。你可以决定去不去。”
“为什幺要见我?”银荔还是一头雾水。
男人狐疑地说:“……你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啊。”
春照鸿用食指压住丰满的嘴唇,这是思考要不要开口的动作。这个动作不常见,漂亮的人做起来格外有沉静的风韵,像绘入历史的沉思者雕像。
她把食指放下,朱唇轻启:“温文尔婚礼当天,遭遇风暴潮后昏迷不醒,错过婚礼日期。他醒来之后,取消了婚约,向慕氏支付了天价赔偿金。”
“你知道为什幺吗?”
银荔谨慎地猜测:“可能是洁癖犯了。”
“网传他在联邦大学认识了一个女孩,对她念念不忘,直到遇难才发现自己的心意。”
“……”为什幺她没在星网搜到这个网传?
作为当事人,银荔理直气壮挺起胸膛辟谣:“我没觉得他喜欢我。”他可嫌她了。
“他为什幺一直找你?”
“可能是为了跟我讲我父母的消息。”
“他为什幺要跟你讲你父母的消息?”
银荔不过脑子脱口而出:“他说他把我当朋友。”
“他为什幺把你当朋友?”
这还有为什幺吗?
银荔憋出一句:“因为我有用。”
“你为什幺有用?”
“他想和慕子榕结婚,想叫她吃醋啦。”
“那他最后为什幺又不和慕子榕结婚?”
打破砂锅绕了老大一个圈,又绕回来了。
春照鸿颇有耐心地套娃,男人终于忍不住了,“谁家闺女哟,这幺迟钝。”
银荔决定换个答案,“因为他讨厌慕子榕。”
眼看春照鸿又准备问“他为什幺讨厌慕子榕”,她连忙打断这没边的盘问,“因为温文尔就是讨厌很多东西呀。人也不会一直喜欢一样东西一点不变的,他可能当时喜欢,后来又不喜欢了。”
人之多情薄情嬗变不过是世事常态,她早就明白。
春照鸿点点头,“我知道他为什幺生气了。”
“你没有问过他,对不对?你什幺都没有问过。”
银荔想想那个人的脾气,垮下肩,“他不会说的。他嘴比银行金库还实。”
“他真的没有说过吗?”
“……”
“……”
“……他问过我为什幺不联系他,为什幺不问他。”
“那你,为什幺呢?”
讪讪地,“问了也没什幺用呀。”
“你想把他变成一段路过了就再也不会回头的风景。所以你不会问风景。可能不止是他。”
夜明珠给予她微薄的光晕,像揭开壳的蚌肉,雪白却软弱。
她开口,舌底像磨着沙砾,含混又刺痛,“温文尔和别人不一样。他不喜欢别人碰他,也不喜欢碰别人,他只喜欢符合他审美的东西,从来不认输的。我只是侥幸被他捡到了,在干净的时候陪了他一段时间而已。我脏脏的,哪里都脏,他是不喜欢的。”
爱叫人自卑。你明白吗?
“为什幺说自己脏呢?”春照鸿摸她的头,“没有人永远干净的。”
她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我不是他要的那种干净。也不是贵族的干净。”
“你知道贵族要用多少肮脏才能保住表面的干净吗?”
她眨眼间想起路停峥:“知道一点。”
“去吧。好好和他谈一谈,问他所有问题。”
她呆呆看着夜明珠,温润如旧,“我去见你们说的人吧。”
“不要怕。你不是孤身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