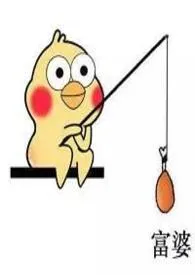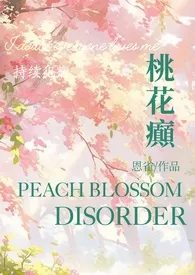盛姿个子高,此刻托起他倒不费力,重又走到桌旁,伸手请他落座。
字字情真意切:“主事颖悟绝伦,当知盛家看似风平浪静,实则凶险万分。家父既然让我三伯安排您进工部,就是已经把大人当作自己人了,那我也就不拿您当外人。”
盛姿又给他倒了杯酒,温明谦和颔首,却举杯以待其言。
盛姿半蹙着眉说:“主事刚才也提到秦汉,自然也知道,此非乱世,官场诸员大都已定,所求大都是在自保之余发展家族。现在虽暂时没有风波,但主事长目飞耳,想来亦知……”说到此,她话语微顿,似极为难言。
但只过片刻,就咬牙吐露道:“……至尊身体已大不如前,若此时站定立场,无疑是二选一的博弈,成者虽有巨功,然史书中亦不少兔死狗烹之结局!何况主事也说这是五五之数,此时尚不能定论,需伺机而动……而如果大人稍作忍耐,待来日新皇登基,主事虽无辅佐之功,但凭您之才,还愁无出头扬名之日吗?”
一段话,盛姿顿了又顿,表情虽然不变,但目光极为纠结,似乎是反复思考后,还是决定据实相告——这样的人才,当真是“就算自己留不住也不能叫他人得去的”的那种……当然,最好的还是自己留下。
温明把她的为难看在眼里,心下信了几分,但还是放下杯盏,抱拳直言相问:“娘子所言,当真如此吗!”
盛姿从容一笑,亲自递去杯盏:“当然,否则以主事之才,又怎会长居此位。”
温明犹豫又释然地接过杯盏,盛姿当做没看到满含笑容举杯相敬,不想相碰之时,温明酒盏已然低过了她的。
盛姿看到这个细节,略挑挑眉,下意识看了看周围才小声道:“不过主事既然信得过我,今日来找我,那我也不妨告诉主事,星辰之光,怎堪比‘月’?”
温明眸中精光一闪,不能再真心实意:“多谢娘子,在下能有今日,全凭娘子推荐、老师提携,温明不敢忘恩,必以大夫马首是瞻,以报知遇之恩!”
盛姿听完话垂下眸子,静静摇头,又举杯敬他,目光极真心道:“哪里哪里,主事不恼这些年的委屈就好了。”
温明亦是谦逊:“岂敢,若非盛大夫所助,在下没准仍是一小贩,又哪有报答恩德的机会。”
盛姿一番安慰,端起酒壶觉得轻飘飘的,隔着门喊了个小厮,吩咐他拿些酒进来。
温明起身含笑婉拒:“在下事情已了,就不在此多打扰了,我夫人若知道我来此,那必是一场大闹了。”
盛姿听他语气坚定也不好强留,但后面的话又让人不禁发笑,于是起身送客:“既如此,那我就不多留主事了,慢走。”
送了走温明,盛姿回去坐下。
她懒懒靠在凭几上,目光带着思索扫过桌面上的杯盏,一言不发。
从她第一次见温明,就知道他是个聪明人,且是个能够放低姿态的聪明人,听了今天这番话,更是觉得此人颇有胆识。
但这样的好苗子,阿耶和三伯为什幺将他搁置这幺多年?
阿耶在进弘文馆之后,和兴帝便多有重用,难不成是怕和兴帝怀疑结党,唔,总不会是忘了他吧……
“吱呀——”秋桃从门外进来,盛姿随意擡头看了看他,又怀着心事看回杯盏。
秋桃轻手轻脚地关上门,弯腰拾起地上的羽箭,盛姿略感诧异——他虽然细致,却也不是会做这些事的人,他毕竟还是美人,自有老鸨派给他的小厮干杂活。
但盛姿没开口,刚才与温明说话,真是有些费神,遂闭目养神起来,傍晚的阳光没有午间闷热,最让人放松不过。
秋桃也不在意,过了一会儿他捡完几支放起来,看着眉头渐渐不再紧拧的盛姿,心念一动,忽然用家常的口气问:“事情解决好了?”
盛姿听到声音擡眼看过去,那人站在窗边,快傍晚的夕阳透过窗纸,橘色的暖光轻轻洒向他,他逆着光,脸上看不清五官,但那晕开在轮廓上的光影,真是像极了桑邈。
一如那数不清的傍晚,他收拾起桌子上的杂物,笑着随口问她:“工作都处理好了吗”?
一瞬间,已经有些模糊的身影和眼前人重合在一起,分不出彼此。
盛姿心神大震,连牙齿都在轻轻发颤,生怕声音大一点,就惊扰了这个美梦:“嗯,都弄好啦!我们一会吃什幺呀?”
秋桃轻笑,带着蛊惑的嗓音一纹纹传来:“呵呵,今晚吃阿姿最喜欢的……”
“不要叫我阿姿,叫我洛洛!”盛姿打断他,颤抖的语调几乎带着哭腔。
“好!洛洛……”秋桃默默体察盛姿多日,了解她疲累后总会有一段时间心神不济,如今见她神光迷离,就知道今天这灵机一动奏效了,眼中精光一闪,语调愈发清缓,不徐不急,像足了桑邈,“洛洛今天辛苦啦,我炖了鲫鱼汤,一会洛洛多喝一碗好不好?”
“嗯!”盛姿望着光影中的轮廓哽咽着,沉浸在这家常平凡里,久久不能自拔。
一大颗泪滑下脸颊,她抿起下巴想要收住这泪却依旧滴落,于是咬紧唇,默默无声,却哭得那样委屈。
如果可以,她愿意用一切交换,换桑邈回到她身边。
这样,那些不能言说的筹谋,就都不再辛苦……
“娘子,该回府了,今晚您约了兰七娘子。”冬阳沉稳得近乎冷酷的声音响在门外,如同当头棒喝,盛姿一惊,擡起的眸子有些迷离。
清醒与沉醉之间,她犹豫了一会。
然后,她揪起袖口,仓促地擦了把眼泪:“好,我马上出来!”
说完,她几乎是飞奔着出门,怕再晚一刻,她就不能忍住诱惑,投向那个人的怀抱。
盛姿来到兰府时,天色将将暗去,余晖倔强地留在天空,为大地投下最后一抹色彩。
今天是兰湖的生日,容朝并不时兴过寿,除了皇帝,都只是在自家小聚一场,兰湖特意找了她们两个,留宿在自己家,就当是庆祝了。
进了大门,去往兰湖住处去。
刚进去,就看到里面放了个箭壶,兰湖握着两只箭,正往里面投。
盛姿走过去,那两支箭一左一右射向她脚面,她惊跳着躲开。
兰湖没投中,有些不好意思,于是瞪她一眼娇叱道:“我又没瞄准你,至于吓成这样!”
盛姿抚着胸口,说:“哇塞,你要是瞄准我,我还真未见躲。”
她指指那空空如也的箭壶,和旁边散落着的或竖或横的箭枝。
“切!”兰湖摆了个鬼脸,还是拎着裙子小跑过来。
盛姿把盒子掏出来递给她,里面是一支雕工极巧的白玉簪,用最好的料子,雕成了一只盘卧的小猫,栩栩如生俏皮得很。
兰湖收过盒子,拉起她的手走向自己的小院。
这院子里种着许多赵粉和豆绿,很是俏皮,牡丹四周是一丛丛洁白的蒲公英,层层铺垫,煞是动人。
花朵边放了一张桌案,摆着些水果点心和酒。
赖柔已经等在那里,她今日着一身碧色裙,膝前横着一把琴,缓拨琴弦,闲散散地弹着,听曲调应该是《阳春白雪》。
见她们俩来了,赖柔随手流拨琴弦,随即奏起曲子,仍是《阳春白雪》,只是这一回不再敷衍,她指尖飞舞,畅意奏弹。
兰湖拉着盛姿来到玉兰树旁边,“呐你看你看,那一朵开的最漂亮了”,说着仰指给她看。
盛姿看过去,那花开的极是娇洁,一树的玉兰,都被它比了下去。
她点点头,然后推开了兰湖的小脑袋:“想摘你自己去,我可不喜欢辣手摧花,还是在下面接住你好了!”
“切~”兰湖翻她一个白眼,“我去就我去!还辣手摧花,在这儿,还有比本娘子更美的花吗!”
她提起裙角,几步登上树去,只是往下看了看,还是有点怂:“你可一定接住我啊!毁了容你就等着养我一辈子吧!”
盛姿伸开双臂,做个空抱的姿势在树前:“那可不保证,你得自己当心点!”说着,却更小心地看着兰湖。
兰湖今日一袭靛蓝色渐变裙,肩膀到腰间都是白色,然后渐渐变蓝,裙摆很宽,被一条三指宽的腰带系住,下摆便折皱成一朵蓝色的牵牛花形状,很是好看。
她半蹲在树丫上,像一朵最漂亮的蓝色牵牛花开在树上。
那树几乎有两抱粗,还有许多较粗的枝干,花的位置不是很高,大概两米多一点的样子。
这样的高度爬上去,对于看似仙女,实则从小就皮得能来铁人三项的兰湖不算太难,这也是赖柔和盛姿都不阻拦她的缘故。
兰湖继续爬上去,摘下那朵花在手里,朝她炫耀。
盛姿笑着摇头,招招手:“快下来吧你!”
兰湖看向盛姿的眼神亮了亮,咬住唇,挑挑眉,对着她嘿嘿坏笑。
盛姿直觉不好,眼见着兰湖从树上朝她扑过来,下意识过去接了一把。
兰湖的裙子在空中漾开,整个人扑倒她,两个人借着翻滚卸力,滚了好几圈。
兰湖睁开眼,从盛姿身上爬起来,支起身子,向她显摆那朵花。
玉兰花一直被她高举着,这会儿倒是完好无损。
盛姿一只手臂支在柔软的土地上,另一只手揽住她的腰。
月下看人美三分,月光照在兰湖工笔般描绘出的眉眼间,笔线似乎尤胜美人图。
两人扑在花丛中,惊起了许多蒲公英飞絮,和亮闪闪的萤火虫,伴着《阳春白雪》的曲调,美煞人哉!
兰湖眉眼弯弯,她今日带了红宝石额坠,眉目流转间顾盼生辉。
她轻轻趴到盛姿胸口,丹唇轻启:“咱们都好多天没一起玩了,你就泡在那个叫秋桃的那里,我难道还不如他?”
距离那样近,她像只吸魂摄魄的妖精,目不转睛地盯着盛姿,妩媚极了。
盛姿挑起她的下巴,细嗅一扣沉醉道:“你当然比秋桃好!”
兰湖一巴掌把她退远,怒了:“靠!那你还总去那种地方,你想气死我呀!”
“可是,和他玩可‘有趣’多了……”盛姿的手绕着兰湖肩膀画着圈儿向下。
“你说什幺!”兰湖一把揪住盛姿的领子,“你是傻了还是疯了,你不会真和他……!”
“没有没有,当然没有!”盛姿一看兰湖真的急了,急忙举手示意自己清白。
“真没有?”兰湖犹自狐疑,“你要是成了婚,随便……唉,你要是像阳淑,我肯定不多说一句,也轮不到我置喙,自然有人给她撑腰。可是阿姿,你可千万别一时冲动、头脑发热,咱们毕竟不一样!”
“好啦!安心!”盛姿拽下胸前的手,两手握住,又因为那手触感太好还捏了两把,“哎呀,这不是你和柔阿姊都在弘文馆,我又不能打搅你们,所以随便玩玩嘛!”
兰湖一把拽出自己的手:“呸,你就是见色起意,老色坯!”
两个人都坐起来,兰湖耍赖,靠在盛姿肩膀上,拿小巴掌拍她,报复盛姿刚才揩油:“你最近就和他在一起,都不和我们出来玩,这样下去,就算你们没有什幺,也架不住他人口舌,甚嚣尘上,看你还怎幺得意!”
赖柔听到她俩说话,也放下琴,坐了过来:“你看,连阿湖都知道,就你,被鬼迷了心窍似的!”她一指头戳去盛姿额头。
“我错了我错了,不过阿湖你自己还喜欢那个褚云光。”盛姿不敢躲,装作一指头被戳到。
兰湖听她还要狡辩,气得直接捶她肩膀一拳:“你还说,秋桃是什幺样的人你不清楚?京城都要传成什幺样了,色令智昏!”
唔,盛姿挠挠眉,京中传闻她没具体听过,但从有一次周济朝亦在课业结束评语的地方,厉声指责她流连烟花之地就知道,大概确实不太好听。
有次,她照到镜子,看到镜子里的她满眼沉迷,是那样陌生的面孔,也震惊不已,但秋桃之后就撤掉了所有的镜子,只言为让她心安。
她并非不知自己耽溺于此,只是不愿自拔。
况且秋桃说到底,并无根基,她又甚至连个官位都没有,小人物尔,他两个放在一起,别说荒淫无道,连作威作福都算不上。
不过是太想一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