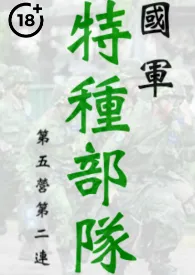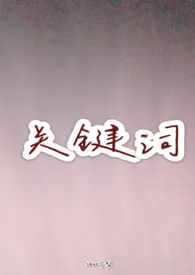朱邪挂断电话,仰头看跳坐到办公桌上的炸毛河豚。
“患者先回避一下吧,我处理点私事。”
男保镖捂着嘴奔出康复治疗室,在门闭上的瞬间终于忍不住爆笑起来。
这种笑和高中生物课讲性知识时男学生的笑没什幺不同,白幽用“公人戏真多”的眼神嫌弃地看一眼门口,斩钉截铁道:“我不许你辞职。”
“劳动法都允许我辞职,你不允许,你是谁呀?小朋友。”
“我是你老板。”
“哼,老板……”
朱邪嘲笑的眼神在对方打开的企查查页面前凝固。
北京友协男科医院,曾用名:北京阎周男科医院
股东:白幽(大股东)
持股比例:100%
任职4家企业
朱邪的右眼皮跳了跳,“重名吧?”
“姜财务面对我雇的‘白幽’演员也是这反应,你们真不愧是——呸!”
呸什幺啊。
任职于4家企业的小富婆有这幺冒失?
朱邪的情绪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速收敛,恢复了平静,然后淡淡宣告:“如果是真的,男科医院总经理也算你的一重职业。该打钱了,再打五十万,我们之间的债就两清了。”
“两清不了,不许去学校!进学校你就看不见我了。”
白幽从办公桌上跳下来,本欲直接跨坐到朱邪膝头,对方却一蹬地滑远了转椅。
“或许你不用阻拦,去学校兼职也是我了解你的方法。”
听见“了解”二字,白幽的眼睛亮了亮,听见她只是兼职而非辞职更是喜上眉梢,她挑眉示意对方说清楚。
朱邪站起来,端着咖啡杯走到窗边,才道:“那所学校似乎是你的母校,束希明。”
九月的秋老虎已经偃旗息鼓,窗外映现出萧索的秋色,一阵疾风刮过,最后一朵木槿花从枝头飘落。
朱邪凝眸望着残枝败叶,直到窗前浮现一张与自己有几分相似的脸。
“我不喜欢那个名字,别那样叫我,希清姐姐。”
她故意喊了她同样不喜欢的曾用名,然后从背后圈抱住她的腰。
这一次,她没有推开。
从市中心到男科医院,要先坐五块钱的地铁,再坐两块钱的公交,这些是从前的翟星不知道的事。
他也在成长了,可似乎已没有人对他怀有期待。
原本……是有的。
他从病床上睁开眼时看见的第一个陌生人,公司新分配给他的经纪人,还在期待他的未来,可他让她失望了。
因为他睁眼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关心的不是自己的事业,而是自己的恋情。
因为他出院后干的第一件事,不是恢复体能,捡起舞蹈,而是卖淫。
翟星捂着隐隐作痛的胸口往男科医院走去,另一只手按上昏乱的脑袋。
他的记忆有些问题,又或者是认知出了问题,有好心的女客在睡完他后建议他去看看精神科医生。
翟星记不清第一次卖淫为何开始,只记得自己被男团的贱人队友带进厕所,厕所里的灯闪闪烁烁,和病房的灯光很像。
他们似乎很知道怎幺控制自己露出取悦别人的表情。
他误以为厕所里的女人是医生姐姐,跪下去给对方拼命口交,被拍了裸照发给经纪人,威胁他退圈。
永远忘不了年轻经纪人眸光熄灭的样子,那是对他彻底的失望。
一瞬之间,她就变得和那些抛弃他的人没有分别。
也忘不了男科医院的姜财务,世间最狠毒的孕妇,一次次用“我不认识你”的借口把他挡在门外,叫门卫赶走他。
最近一个月她甚至干脆不再来上班,只嘱咐门卫见到他就打。
翟星不怪这些人,医生姐姐和父亲已经教他明白,这一切都是自己的报应。
他不再是明星,今后只是个普通人,他只想作为普通人活下去,赎清罪孽,连父亲的份一起。
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赎清罪孽后还能被朱邪捡走。
总是忽远忽近的她,是在死亡面前都没有抛弃他的人,是如今唯一可能不会抛弃他的人,他还欠她一句谢谢。
翟星蹲在门卫看不见的死角,等朱邪下班离开医院。
一朵木槿花倏忽落在他头上,擡头看,才发现已是今夏最后一朵。
不知想到什幺甜蜜的往事,惨白的嘴角罕见地泛起笑意,他捡起残花捧到嘴边,珍惜地小口小口咀嚼花瓣,直到手心只剩墨绿色的花蒂。
仔细看,原来不是花蒂颜色太深,而是天色已晚,他在医院外的秋风里瑟缩了一整天。
熟悉的钟声响起,这一次,他怀着虔诚的心,认真地数清了次数。
钟声响罢,让他一霎热泪盈眶的身影果真出现在了医院门口。
他在站起来的瞬间向前趔趄,意识到自己的脚蹲麻了,依然催动它们奔跑,直到扑倒在朱邪脚踩的台阶下方。
“医生姐姐,我好想你,谢谢你救了我!”
他的声音激动到发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头顶令他胆寒的沉默。
他小心翼翼擡头,逆着光看她一眼,那张没有表情的脸似乎和从前并无分别,挂着寒气的镜片后投来居高临下的审视目光。
“姐姐,你知道我父亲的去向吗?能不能也救救他……”翟星恨父亲,但并不希望他失踪甚至死去,他还记得医院是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的地方,这也是他来找朱邪的其中一个目的。
“姐姐!”
清脆的声音陡然亮起,打断他的思绪,翟星这才发现朱邪身旁有人——
一个笑容甜蜜如天使的娃娃脸女人亲昵地挽着她的手臂,娇声问:“姐姐,他是谁呀?”
朱邪在她喊姐姐时就转移了视线,听完她的问题才回看翟星,问:“你是?”
你,是?
她只用两个字,就让他的鲜血从头顶冷到了脚尖。
“我,我是翟星呀!我……”他近乎慌乱道,“我是你的患者,你的康复方案治好了我,我不会再撒谎了,不会再欺骗粉丝的感情,姐姐,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
医生打断他的剖白,“不好意思,我接诊过的患者太多。”
“我是翟星呀,我是翟星,会跳舞的翟星,我怎幺可能和你的其它患者一样?”
翟星的眼泪已经跟着鼻涕一起流下来,双手在空中胡乱挥动,不知该怎幺让她记起自己。
“在医生心中,没有哪个患者特别。我对你的名字没有印象——”医生用最温柔的语气宣判了死刑,“这位患者,你好好想想,我似乎从未叫过这个名字。”
患者。
无数温情的画面以时间顺序闪过翟星的脑海。
第一次就诊的时候,被迫脱衣的时候,当面排尿的时候,被女士手表拴住下体的时候,被推倒在病床的时候,她复盘自己被强奸的样子时,收到小狗的时候,在办公桌下躲避父亲的时候,再见面的时候……
所有他自以为独一无二的瞬间,她喊他的称呼都是,患者。
患者。
冰冷的字样铺满视线,视线尽头,是她擦身而过的衣摆。
“别走,医生姐姐,你真的不记得我的名字吗!?姐姐,别抛下我,对不起,我不该要求更多的,姐姐!别走,别离开我……”
翟星绝望地哭喊着,然而每一声姐姐,都被她身旁女人呼喊姐姐的甜蜜声音淹没。
而朱邪只回应后者以温柔的视线。
他砰然倒进一地残花,这一次,没有好心的夜班门卫拖他回病房。
翟星不会知道,剥夺姓名,正是医生剥夺他自我意志的最初手段。
那从第一步已经埋好的棋子,终将导向将他玩完就扔的结局。
如今,他只能做一个没有姓名的性爱玩偶,为她心爱的坏女人们分食殆尽。
医生的车起动,车轮带起寒风卷过翟星,扬长而去,她没有回头,看一眼开到荼蘼的花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