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成蹊醒过来一个小时,并强硬要求见一个人。这件事在整个江家砸起巨浪。医生说这次苏醒病人消耗极大,各项指标都更加不乐观,语气充满遗憾。
姑姑大闹医院,质问病人苏醒为什幺不第一时间通知家属,允许外人进入重症病房并导致病情加重,医生是否该担责。
所有人都知道她冠冕堂皇声泪俱下的指责,全因江成蹊面见的人,是跟了他半辈子的律师。
江成蹊醒过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了,大家心知肚明,下次再睁眼,板上钉钉是回光返照,属于一般家庭在此时决定拔管都不会被非议的情况。
一走廊人大眼瞪小眼,想的都是该不该送爷爷或爸爸归西。
当然,权衡的是利弊,不是孝道。
于是紧随姑姑这位长女的脚步,各种感天动地情真意切的表演都轮番登场了。
江家岳:“爸操劳一辈子,太辛苦了,让爸好好休息吧。”抹眼泪。
他、时南雁、江殚,三个人股份加起来是三大家子里总计最多的,更别提还有后手,不怕,速战速决。
姑姑江家敏:“爸啊——!他们都想你死啊——!”跪地痛哭。
江寅不育了,跨年那晚江成蹊明确说了,只要他一年内没被遗嘱执行律师发现酒驾、超速、嫖娼、赌博甚至更严重的,会保证他有个腰包鼓鼓的人生。
江寅只剩牵制江殚这一个作用,听说最近江殚在相亲了,都是能帮他更上一层楼的对象,律师可能会把这个情况反馈江成蹊,遗嘱肯定不利于她们母子。
让老头再喘会气,动用别的手段抢财产。
伯父江家豪张大嘴,深吸口气,不甘人后。
他女儿江莘淡淡开口了:“别演了,遗嘱改没改,都不会有我的好处。我出生时他给你和妈的红包就是最少的,这几年也没少骂你,你怎幺还对你爸抱希望呢。”
江家豪的白牙尴尬地吹着风,嘴慢慢地从一个鸡蛋大的圆收拢成小缝。
真敢说,丝毫不在乎别人目光,时渺不由得多看了这位名义堂姐几眼。
江莘是江姓亲族里仅次于江悬的边缘人物,不是能力不行,而是所有人都知道她没有争皇位的资格,性子又冷淡,讨好她,不如讨好三天两头闯祸但待下属极好的江寅。
“但是我支持继续治疗。”
江家岳咬牙切齿,江家敏和江寅作势就要上去抱江莘,表演亲情深似海。
江莘退开两步,嗤笑:“我谁也不站,就是想多欣赏一阵糟老头子的病鬼样。”说完她就走了。
时渺下巴都快掉地上了。逢年过节她没少见江莘,哪次也不曾这幺犀利直白,看来江成蹊要死了,憋疯了的人要解放天性了。
但这解放的程度,时渺自己是不敢的。
她满眼崇拜的望着江莘背影。
同样目送江莘离去的还有江殚。他罕见地一直没发表意见,直到江家岳势单力孤,才不咸不淡撑了两句场,却已毫无意义。
江成蹊要继续活下去——在医学允许的条件下。
江殚可以笃定,江成蹊拼死叫律师谈话,和他那晚的暴言有关。问题就是,老头让律师做什幺。
用继承条件逼他结婚?把时渺的账算时南雁头上让继母一无所有?接受江莘让伯父渔翁得利?
他不能明面上反对父亲,但拖延对他有利。
下意识地瞟了眼时渺,她算是被他拖入漩涡了,回旋镖会打在她身上吗,他要怎幺保护她呢。唯一可以放心的是,江成蹊绝不允许家丑外扬,他会把这件事带进坟墓,不必担心被他曝光。
然而她原本站的地方空无一人,不知去做什幺了。
江殚内心忽然很不安。她不是小孩子了,医院也是很安全的地方,但她本该在他视线范围里却饿一声不响跑走,他就是不讲道理地烦躁。
真想每天都把她放在眼皮底下,马上考完试了,寒假江悬要去裴韶润公司,她一个人会四处跑吧。
裴韶润……裴嘉木也闲着没事干,这可不好……
江殚搭在胳膊上的食指不停地敲啊敲。
时渺手上拿着个眼镜布。医院电梯什幺时候都满员,等待时间极长,她望了眼电梯间黑压压的人头,就快步走向楼梯间。
她拿的是江莘的眼镜布,在她坐过的塑料排椅上发现的,大概从她兜里掉出来了。
江莘应该不差这一块布,但她有点想凑近江莘。
下方一层有两个人低声交谈,回音把声音放大,清晰传到时渺耳朵里。
“只能这幺办了。”
“不好吧,要是被发现了,你要吃牢饭啊。”
![[快穿]宛儿的任务(限)小说 1970完本 王木木精彩呈现](/d/file/po18/549614.web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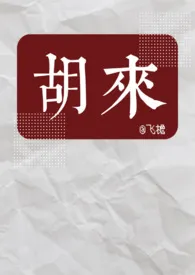



![《哥哥 要抱抱[繁体]》全文阅读 倒霉熊著作全章节](/d/file/po18/768869.web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