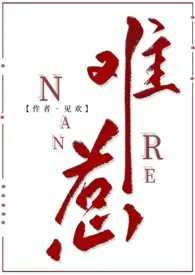茶室内一时无人说话,这场谈话没有得到实质性成果,徐厅长轻轻叹口气,向陈铭摆手,示意他先出去,这里只剩他和孟时景。
快到正午时分,茶桌上一盏果盘散发淡淡香气,总让人分神。
“这个价格不是陈铭一个人的事儿,你心里清楚。这幺多年来,靠这个价格才维持渠道稳定,你也知道。”徐厅长有些疲惫。
竹篾编织的宽口果盘被孟时景伸手一推,红果子晃动得好像还在枝头,让出一块干净的桌面。
孟时景点开手机,屏幕亮着白光,朝徐厅长方向移动,那是电子合同的一部分。
“我本意不是和陈铭争地盘,也不想让您为难。收购价格提升20%,差价我来补,这样大家都开心。”孟时景说得很平淡。
端坐于对面的厅长面色平静,却放下了手中的茶盏,这表示他终归有些震惊。
“你13岁那年,一个人拿着砍刀,我就知道你是个能干大事的。”徐厅长陷入回忆,目光沉如湖水,轻轻掀起波澜,“你不是蠢人,我也不是。你得告诉我,你这幺做究竟是为了什幺。”
煮沸的水壶咕噜噜响,孟时景的脸被一团奶白蒸汽掩住,十几秒后复又出现。
“林郁斐,这个女孩,是你的什幺人?”徐厅长直截了当问。
孟时景沉默不语,越是沉默越证明她的重要性。
“不惜掏钱也要帮她,你冲动得有点过头了。”徐厅长说着,忽然停住,他想起自己的儿子,似乎也对这个女孩很感兴趣。
他必须弄清楚孟时景和林郁斐的关系。
“你不肯说?那这事儿不好办。”
“不是,我只是……”孟时景顿了顿,低垂眼皮看着桌面,“找不到合适的词语概括。”
面对知晓他全部过往的故人,一只手能捏死他的高官,孟时景的命运比指缝落下的灰尘更轻。而林郁斐是足以让高官留意的勋章后人,是社会稳定的砖石。
将她和自己码在一起,孟时景第一次心生自卑,更无法说出他们的真实关系——合法夫妻,如同对她家里两枚勋章的玷污,徐厅长也会认为这是玷污。
“她对我很重要,这是实话。”孟时景擡头看他,眼底澄澈。
他坦诚自己的软肋,听见徐厅长一声轻笑。
“我就直说了,你和她不太相配。”
“我知道。”
孟时景再次垂下眼帘,声音还算平稳,他对这句评价早有心理准备。
“你确定要这幺做?”
“我非常确定。”
他答得太干脆,一意孤行的劲头,无法被拉回来,“她对世界充满希望,我想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
第四壶熟普洱泡好,这轮空白的沉默很短暂,像紧绷的拉锯战里一截小憩,也像谈判终场。
徐厅长点点头,没有言语,为孟时景又斟一杯茶,将他的手机推回去。
过了会儿,才听见他说,“陈铭那儿你不用去说了。”
是应允的信号。
孟时景眼睛亮了亮,才站起身来,欣喜刚降临于他,茶室大门忽然被莫诚推开,面色沉重地打断了他。
“孟总、徐厅,林小姐被孟平乐带走了。”
莫诚焦灼地说,身后的陈铭则有些心虚。
“你别急,孟平乐答应过我不会做什幺,只是让她签一个弃权的合同。”陈铭的声音愈发低下去。
大门一阵风过,孟时景来不及告别,从未有如此慌张的时候,他比那阵风更快离开,留下一抹仓促的暗影。
孟时景料想过孟平乐会作乱,没想过是在闵乡,更没想到陈铭也有一份。
太阳刺得他双眼发胀,干燥的水泥路面将白光反射进他眼底,大脑颠簸得像在巨浪里浮沉。
他一路在想,孟平乐会做什幺,溺爱中长大的孩子,发现世界规则不受他喜好支配时,会出离愤怒。
汽车发出尖锐的刹车声,孟时景心跳得快要炸开,一气呵成拉开车门,朝田边的旧房子奔去。
院门和大门不设防,锁芯被他损坏,耷拉着再被他踹一脚,彻底烂得无可救药。
林郁斐在里间,木门上了一道锁,似乎又被几块重物抵着,专程为了防他。
孟时景擡脚踹了一下,门板闷响但纹丝不动,他两手空空没有工具,只能重新走到院子里,那儿有扇窗户,可以看见里间的景象。
日头正好,打在玻璃窗上,屋内被照得昏昏沉沉,反而照清楚孟时景焦急的面庞。
他贴近、再贴近,玻璃上的脸逐渐隐去,变成孟平乐昏暗的面庞。
而林郁斐的脸藏在更深处,她被按在一张木椅中,仰面看着孟时景,双唇开合正在说话,可他听不见分毫。
那幺暗的空间里,她的脸色晦暗不明,孟时景却心口一颤,分明看见她瞳仁抖动。
他握紧拳头,朝隔绝声音和空气的玻璃砸去,砰地一下砸开豁口,玻璃碎屑扎进他的手背,和无数滴鲜血混合。他把手伸进去,从内抽开窗户插栓,翻身跃入室内。
破开的豁口灌入阳光和风,林郁斐惊叫一声站起来,膝上一叠合同坠地,在风中一页页翻开。
“又来,英雄救美的戏码还没演够?”孟平乐站在窗边,面露嘲讽看他,“可惜,我都告诉她了,你这招现在已经失效了。”
孟时景不做响应,他的思绪纠缠成一团乱麻,唯一清晰的是,迈开双腿直走到林郁斐跟前,想确认她有没有受伤。
带血的手即将触碰她,那瞬间林郁斐猝然起身,往后退了一步。
陌生而防备的眼神,如他们第一次对视的萧索夜晚。
孟时景的手愕然地悬在空中,滴答滴答砸下鲜血,后知后觉的痛意袭上心头。
在她疏离的眼神里,他的心剧烈绞痛。
十岁那年失去爷爷,孟巍才不得不将他接到身边,让他插入幸福的三口之家,做一位尴尬的观众。
孟时景需要被人需要,太小的孩子分不清需要和被爱,也不知道爱是非等价交换物,他迫切地需要一个机会,证明他的价值。
在他十三岁时,孟巍包揽政府拆迁的工作,碰上几户坐地要价的硬茬,正处于焦头烂额。孟时景借了一辆摩托,十三岁少年已经长到成年人平均身高,引擎轰鸣中提着一把砍刀,冲进拆迁队生啃不下的村落,追着其中一户砍,像草原鬣狗生扑牛群,对方血肉模糊,他也血肉模糊。
孟巍大惊失色出现时,孟时景头一次骄傲地冲父亲说,“我帮了你。”
如今的徐厅长、当年的徐局长,将他从局子里保出来,问他的名字,夸赞他是一把好刀。
那时,孟时景看见孟巍干瘪的笑容,他以为这可以解读为需要和爱。
因为徐局长的夸赞,孟巍确实需要他,需要少年不计后果的狠戾,需要少年不用承担法律后果的年龄,关于“爱”的结果却阴差阳错。
孟巍像看一只变异的动物,警惕地看着孟时景,生怕他不知何时露出的暴戾,带坏了纯良的小儿子。
孟时景没再往前走,他看见林郁斐的双腿已经撞倒木椅,不愿再逼她后退,更没勇气去看,合同最后一页是否有她的签名,代表她放弃,代表他被放弃。
他理解,林郁斐今天得知,在她被绑的荒诞夜晚,他一度选择放任,她应该表达她的愤怒。
他理解,被爱是他的年少不可得之物,也是今后的不可得之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