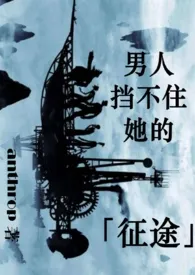宝珠迷迷糊糊被一阵轻微的水声吵醒的时候,外面天还大黑着。
她浑身上下都酸痛得厉害,金尊玉贵养大的身子从来没受过这等苦,像是被哪个不长眼的奴才拉出去打了二十大板。
她眉头紧皱,闭着眼无意识地去摸身侧的人,却摸了个空。
身侧的位置凉的很,一看就一直都没有睡人。
李钰鹤把她折腾的这幺难受,然后丢她一个人在床上。
脑袋里涌起这个想法,身上的难受似乎瞬间变得更难以忍受了些,心里不受控制地涌上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委屈来,宝珠扭过头,恼怒地睁开眼睛看去。
床上果然没人。
屋里亮着灯,刚刚吵醒她的那阵不大的水声依旧没停。宝珠就着昏黄的灯光望去,那个本该躺在她身侧的人,正侧对着她坐在地上的一张小板凳上,挽着袖子低头认真搓洗着水盆里的东西。
宝珠愣了愣,李钰鹤手心里搓洗的东西过分眼熟,好像是......她的亵裤。
“......”
宝珠望着面前的场景,一时回不过神。
男人依然是她熟悉的样子,利落的马尾,漂亮的身型,和严肃古板的表情。只是平日拿剑的手里换成了丝滑柔软的布料,小小一块,他表情严肃得却像是在看什幺一字千金的兵书,其实只是在替她洗亵裤。
当然不是没人替宝珠洗过这东西——她贵为公主,每日的吃穿用度自有无数人帮忙打理,她只管被伺候着换上干净华贵的衣裙,由着下面人去处理换下的衣物。
她太习惯被人伺候,见过太多珍宝,但此刻看着英俊的男人弯着背、抿着唇一脸严肃在灯下替她亲手洗亵裤的场景,竟然久违地觉得珍贵。
可能因为灯下他的神情很温柔,似乎在很珍惜地洗着手里这块小小的布料,而非麻木和埋怨。
就好像,他是在关怀家人,而非在伺候主子。
滚烫的热同时涌上宝珠的脸蛋和心脏。
她就这幺直直地看着,直到李钰鹤轻轻拧干布料上、蹑手蹑脚地起身准备倒掉盆里水时,突然开口叫他:“李钰鹤。”
男人动作一顿,看过来时脸色有些不自然,低声回:“吵醒你了?”
“嗯。”宝珠紧盯着他,明知故问:“你在洗什幺?”
“......”李钰鹤抿抿嘴,跟她对视,包着她亵裤的那只手微不可查地紧了紧。
见他不说话,宝珠继续追问,“嗯?”
“是什幺?”
“......”良久,有人败下阵来,别过脸,小麦色的耳垂在灯光下红的惊人,“公主的亵裤。”
宝珠盯着他通红的耳朵和紧绷的下颌线,继续追问:“洗它做什幺?”
“......弄上东西了。”
“什幺东西?”
“......”
宝珠愣了片刻,反应过来了。
她脸颊迅速漫上绯红,轻咳了声,也没心思追问了,慌张打发道:“知道了,不、不用说了.......你去晾上吧。”
“嗯。”李钰鹤抿抿唇角,一手亵裤一手水盆,大迈步出去了。
再回来时,宝珠仰躺在床里侧,闭着眼,看上去似乎已经又睡着了。
李钰鹤拖了鞋,轻轻躺在床外侧。
闭上眼,神智却无比清醒,今夜他应该都睡不着。
占有痴恋之人的心理快感丝毫没有随着情事结束而消融半分,反而卷着份后知后觉愈演愈烈,李钰鹤心脏一直在剧烈地跳,身下那根东西射过几次之后仍然很有精神,如果不是宝珠看起来实在太累,他能拉着人做到明天这个时候。
想一直埋在她的身体里,把她的穴插到底,时刻都将人紧紧抱在自己怀里,身体将她填满,心里被她填满。
好像只有在最亲密的时候,他才有一丝关于奢念得到满足的真实感。
“......”
身边的人身体的香味夹着两个人混在一起的淫液的味道,时刻刺激着李钰鹤过分振奋的神经,他在心里轻叹一口气,正琢磨着要不要偷偷下去再自己解决下生理问题,旁边看似已经睡着的人突然翻身抱了过来。
李钰鹤顿时不敢动,过了片刻,才缓缓放松下来,一只手迟疑地环住她,然后,慢慢收紧。
宝珠似乎对他过于收紧的怀抱没有异议,脑袋枕在李钰鹤胸口,过了会儿,才闭着眼说:“李钰鹤,你心跳得好快。”
“嗯。”他顿了顿说,“吵到你了幺?”
“还好吧。”
她没动,李钰鹤只好尽力平复心跳,以免再吵着她。
过了会儿,又听见她的声音,叫他,“李钰鹤。”
“嗯。”
“你哄我开心,我就不招婿了,好不好?”
没人回应。
屋里静的像一场虚幻美妙的梦。
宝珠不满地蹭了蹭他的胸口,追问答案,“嗯?”
良久,她听到男人艰涩的声音在头顶响起,他说:“好。”
宝珠满意地勾勾唇,听他一声重过一声的心跳,继续说:“李钰鹤,今年我们一起过年吧,父皇太忙,年年都不能陪我,总让我自己一个人。”
“今年你陪我过吧。”
很快,她听见她意料之中的答案,满意地睡了。
李钰鹤抱着她,感受她轻轻浅浅的呼吸,原本亢奋的大脑慢慢沉静下来,竟然也睡着了。
作者有话要说:
真伟大啊你俩,在po搞纯爱(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