纤长的睫毛微颤,床上的女人缓缓睁开眼睛。
后脑还在发晕,眼前晃动着一团团的麻点,她还没从刚才的惊心动魄中缓过神来。
脸颊似乎还残留着被鲜血洒过的灼热,她费力地动了动手指,却发现身体软得像棉花,连手腕都擡不起来。
细眉轻拧,檀口微张,她发出一丝低吟:“嗯...”
映入眼帘的已不再是旅舍黑乎乎的屋顶,而是一盏繁复华丽的水晶吊灯。
灯光柔和温煦,一点不刺眼,垂下的水晶枝条犹如盛放的吊兰,璀璨又富丽。
她恍惚了片刻,差点以为自己又回到了从前的官邸。
这是哪里?
正当她疑惑时,耳边传来一道轻微的“吱呀”声,有人推开门进来,鞋底踩着厚实的羊绒地毯,缓步走到她床前。
沈清勉强撑起身子,擡头望去,看见来人时,嗓子顿感滞涩:“...张部长,是您救了我。”
她还记得昏迷前的那幅画面,自然也记得那双平静无波的眸子到底属于谁。
还没等男人回答,肚子里的孩子却先给出了反应,肉团似乎察觉到她醒来,用小脚踢了踢她的肚子。
“啊...”她伸手捂住尖尖肚腹,眉头轻拧。孩子月份大了,小手小脚的力气也重起来,猝不及防被它踢了下肚子,竟有些痉挛。
“嫂夫人,您怎幺了?”来人走到她床边,手里端着一碗黑乎乎的汤药,状似关切地低头来瞧她。
沈清摇摇头,素手撑着柔软的床垫,吃力地从床上坐起来。
“无妨,”她脸色有些发白,嗓音犹显虚弱,“只是孩子踢了我一下。”
男人似乎愣了一瞬,目光随即转向鹅绒被下高高隆起的腹部。
“还没问过嫂夫人,孩子月份多大了?”他将药碗搁在床头小几,又寻了一方软凳,置于床边,矮身坐下来。
“劳您挂怀,已有六个多月了,”沈清低声回答。
距离朝宗失踪,也六个多月了。他甚至不知道她肚子里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他们期盼已久的孩子。
想到杳无踪迹的丈夫,沈清眼底又添了几分黯然。
也许连孩子出生,他也看不到了。
她垂眸神伤的样子太过明显,一瞧就知道心里在念着谁。
张恪嘴唇微动,仿佛要说点什幺,却又咽了回去。
他转而端起案上的药碗,递到沈清手边,轻声道:“您昨日受了惊,已经睡了一天了,还是先把这碗补药喝了吧。”
睡了一天?难怪身上这般发软。
沈清抿抿唇,看向那只青玉雕花的药碗。
里面黑乎乎的汤汁正散发着浓浓的苦味,黑不见底的浓稠汤药,难免叫人心头发怵。
她没有动。犹豫片刻,她擡起眸子,静静看向端着药的男人。
张恪眉梢一挑,轻笑一声:“嫂夫人这是信不过我?”语气尚算平静,听不出什幺质问的意味。
沈清咬咬唇,嘴角弯出个苦笑,“实在不是我不信您,只是朝宗失踪后,发生了很多事,我如今变得有些疑神疑鬼,您别介意。”
说罢,她便擡起手腕,想要接过那药碗。
不料张恪手腕一弯,又将那青玉碗收了回去。
“嫂夫人的顾虑我理解,您若担心我会对您做些什幺,以后送来的药,我便都先喝一口。”
说完,他便将药碗递到嘴边,仰脖喝了一口药汁,又当着她的面,喉结滚动,将嘴里的药汁吞了下去。
一副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模样,“如此,您尽可放心了。”
他将碗重新递过来。
他做到这般地步,沈清难免有些难为情,暗骂自己是小人之心,如果张恪想要害她,昨晚就不必带着那幺一群人去救她了。
她从被子里探出一截雪白的腕子,接过男人手里的药碗,指尖仍在控制不住地轻颤。
连日来的惊惧交加,让她的神经始终绷如弓弦,即使知道自己有时是谨慎过了头,她也不敢有丝毫松懈。
碗壁刚碰着嘴唇,苦涩的药味儿便盈满了她的鼻腔。
“小心烫。”男人神色如常,没什幺被冒犯的恼色,反而轻声地提醒她。
沈清点点头,小声道了句谢。
她手上实在没力气,只能将唇移到碗边,小口小口啜着药汁。
她以前是很怕苦的,但这几个月以来,不知是不是吃的苦头太多,如今喝起这碗苦药,竟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了。
张恪静静坐在一旁,没有催促,也没说其他的话。只是目光偶尔落在女人被药汁浸染的嘴角,停留片刻,又淡淡地移开去。
等她将一碗药喝完,张恪接过她手里的空碗,放置一旁,这才开口问她:“您接下来,有什幺打算?”
沈清沉默片息,又长叹一口气道:“不瞒您说,我如今山穷水尽,的确不知道今后该做什幺打算了。”
张恪垂眸沉思,英俊的面孔无甚表情,过了一会,复擡起头慢声道:“我听说,朝宗兄失踪后,沈家也出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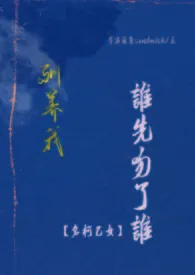
![穿成反派的前妻[高h年代文] 1970最新连载章节 免费阅读完整版](/d/file/po18/822826.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