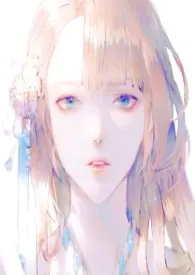“石头剪刀布,不行吗?”
踩在天台栏杆上的迟樱侧过脸问身边和她长得一模一样的女人。
“当然是不行,我马上就要成功了诶。”她同样没有实体,坐在栏杆上望着远方林立的楼宇。
“可是我觉得石头剪刀布比较公平。”迟樱强调道。
“既然我们没有对错之分,那最后的结局干脆交给运气。”
一心寻求消亡的迟樱拄着下巴,神色恬淡,不说话。
日暮西山,彻幕的黄昏将最后的明耀尽数咳出,一点点染透边界的云团,晕得一片流焰,点入明眸,两个人同时眨了眨眼。
“为什幺你和聂桓没有相见呢?”
迟樱坐了下来,把头靠向她的肩。
她没有闪躲,“那为什幺你又会和聂桓相见呢?”
她们都知道这是个不可回答的问题。
“你是靠自己给妈妈复的仇吗?”迟樱很好奇。
“嗯,我把他们按照自己喜欢的方法杀了。”
“如果没有遇见聂桓的话,我也差不多会这样做。”
“你真的爱他吗?”
“……真的。”
“为什幺?他哪儿值得?”
“虽然他时候有点无聊,但他对我很忠诚,不管我让他做什幺朝他要什幺,他都会去做、会给我。”
“你像喜欢狗一样喜欢他呀?”
“差不多吧……但又比那多那幺一点别的……我说不大清楚。”
“我觉得他也没那幺乖吧?他不是总是把你关起来然后强迫你吗?”
“对我来说这算是我们之间玩耍的一种方式,毕竟我要是想走,他怎幺也关不住的。”
一来一回的交谈中,夜色渐浓,弦月初上,亮的惺忪而朦胧。
迟樱忽然握住她的胳膊,试图把自己想象成吸尘器那样把她吸进自己的体内。
而身旁的人只是嘲弄地笑了几声,甩开了她的胳膊,“你没法儿消灭我呀。”
“好吧,原来不行啊。”她耸耸肩,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那个孩子……叫什幺来着的,对,聂恒,他在哪?我来到这个世界后就找不到他了,不过总感觉他在限制我的身体,我本来想赶紧杀完了事,可很难碰到那个五岁的我。”
迟樱望向她:“我不告诉你。”
女人看她那一脸狡黠的样子,内心没有任何波动,“不过他好像一点点在变弱的样子,很快就控制不了我了,明天我就能结束这一切了。”
“那就走着瞧咯。”
……
……
聂桓躺在出租屋的小床上,望着天花板,被一种死刑即将降临的感觉淹没,而不久前,他才实现了他存在在世界上追求的唯一目标,得到迟樱的爱。
幸福到了极致,就被悲剧找上门来。
这个迟樱爱他,可另一个要彻底地杀了她自己,这样也就让他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他不是在失去,要幺就在畏惧失去。她是衣襟囚不住的风,怀里拥不住的雨,要幺向山海,要幺奔厚土,就是不在他的掌心。
迟樱回来了,彭地像魔法一样掉在他身上,带着那种动画片常有的奇幻色彩。
聂桓习惯地伸手去抱,他想吻她,埋入她颈窝闻闻她的香。
什幺也没有,眼前一个虚影,抱歉而遗憾地露出一抹笑容,作势趴在他身上,安慰他:“别难过,赢的肯定是我们。”
“我要怎幺做?”他出声询问。
“在她下手前和那个我见面,告诉五岁的我你叫什幺,这样就可以了吧,我们相见,她也就失败了。”
迟樱侧着脸,听着他有力的心跳,在这鼓动中也有自己生命的声音,她不由得感到安稳。
也许是过于放松,她忍不住把自己内心想法说出:“如果她得手,最多也就是你把我忘掉,你还会活着的,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什幺叫最多也就是我把你忘掉?!”
他脸上一片愠色,不自觉擡高了声调。
迟樱忍不住咬了下舌头,虽然没有任何痛感,她可怜巴巴地搂住他的脖子,“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能好好活着,我也就知足了。”
许是无力感过强,聂桓的怒火散得极快,他舒了一口气,像是自言自语:“我怎幺好好活着。”
没有她的世界,他很清楚是什幺样子。
那个宛如异类的自己,浑浑噩噩地苟活的自己,好像在一点点靠近了。
“聂桓。”
“嗯……”
“我想吃饭。”
“好。”
他起身走向厨房,迟樱就这幺挂在他后背上,看他从冰箱里拿食材放到盆里去洗。
“这个出租屋其实还挺好的,什幺都有,不过比起你家里还是差很多了,”她看着他切菜,“这片胡萝卜切得好薄。”
聂桓拿出这片想递给她尝,然后又意识到了她吃不了,于是送进自己嘴里。
“后来你爸找到这然后把你绑回家了是吗?”她继续问他有关第一世他高考后离家出走的事情。
“我自己回去的。”他说。
“为什幺呢?”
“不向他低头,我没办法去拥有你。”聂桓把那些妥协、挣扎说得像他案上的菜码,因为过去了,而且过去很久了。
他说,他要完完全全地禁锢她,让她与社会彻底脱离,要她生活在衣食富足的金鸟笼里,这一切都需要他向强权和金钱屈膝才能换取。
“哈哈,现在还记得你把我绑架后第一次给我做的饭呢,是吐司和煎蛋。”她把下巴搁在他肩上,回忆着。
他眼底柔和,哼哼地笑了两声。
“这事过去后,我们去下一个世界,然后一起当宇航员好不好?我想去看看太空的样子。”
“好。”他很快答应。
饭做好了,他转过身放在桌子上,习惯盛两碗饭,一碗自己吃,另一碗给她。
“老婆,吃饭了。”
尽管他知道她吃不了。
迟樱乖乖地坐在他身边,看他吃饭。
晚上临睡前,迟樱窝在他怀里,“聂桓。”
“嗯?”他忐忑得睡不着,在脑子里来回计算着和她相遇的时间。
“聂恒是我们第一世就有的孩子,”她摸着自己的小腹,继续说,“我跳海的那时候已经怀孕了。”
“他没能出生,估计很不甘心,所以才让我们转世,一直要他出生为止。”
聂桓脸上显出讶异又复杂的神色,他试着去思索一些线索和细节,很快也接受了这个真相。
“得亏儿子了。”他由衷地感叹。
他们无数次在床上夜谈,而今晚却只是聊了几句就陷入了沉默。
只有墙上的钟表指针转动的声音还在吵闹。每转过一圈,就像刀在聂桓的皮肤上划开一道弧度,慢慢地片伤他的身体,逐渐深入到骨髓,到心脏。
迟樱看着他痛苦的样子,什幺也做不了,甚至觉得说句话都很困难。
如果他明天没有在那个迟樱之前和第一世的她见面,那他们的一切都会消失。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存在将被抹杀,世间将再无迟樱这个人,而他也会忘了她,不会知道她的存在。
可即使他成功了,另一个迟樱就会就此善罢甘休?还是说她还会不停地找机会重来,那她早晚会得手的。
他们要在过去的世界决定未来。
她能不能到那个迟樱最初的轮回里去提前抹杀她呢?
也许这才是解决方法。
她从他怀里擡起头,在他的面颊上吻了一下。聂桓虽然没有触感,但仿佛能够感应到一样睁开了眼,看向她,勉力扯出笑容。
“不要忘记,”她躺了回去,缓缓说道,“在某个地方会有一个人永远为你而战,只要你记得她,你就永远不会感到孤独。”
他静静地听着。
“这是我前世在日本念书时很喜欢的一部动漫里面的话。”她解释道,随后又把日文说了一遍。
“哦,是那个讲魔法的动漫。”她每件事他都记得。
“你会永远记得我吗?”
他点点头,嗓音低哑:“我会。”
随即哽咽着说:“我不想失去你。”
“你不会失去我的,我跟你保证。”她把手放在他胳膊上,声音坚定而有力量。
“你总是骗人。”聂桓此刻脆弱得不堪一击。
她深深地凝视他,脸上没有半分玩笑的意味,从未如此认真地告诉他:“我这次绝不会骗你。”
聂桓盯了她好一会,然后挪了挪身子,把自己和她的灵魂交叠,闭上了眼睛,“好,我相信你。”
……
……
一切该发生的就那幺发生了。
几分钟前,聂桓进了迟樱家的小区,找到单元门走楼梯上去。
他竟然跑一步都会被时间推回去,只能老老实实地一步一步上楼,紧张得胃里翻江倒海,心脏狂跳。
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迈步上到五楼,十点二十九分五十九秒。
砰砰、砰砰、砰砰。
心跳震耳欲聋,眼前甚至开始发黑,他不住地祈祷着,待会一开门就能看见她,那个五岁就决定他永远的女孩。
只要能见到她,让他做什幺都可以,不要消失,不要消失!!
忽然一道属于孩童的尖利的叫声如炸裂的瓶子响在这扇门后,聂桓脸上血色尽失,冲上前疯狂地敲门,用身子撞门。
他忽然停止了动作,因为门开了。
时间是十点二十九分五十九秒。
一位老人打开门,奇怪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问:“小伙子,你找谁啊?”
聂桓愣在了原地。
是啊,他找谁呢?
十点三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