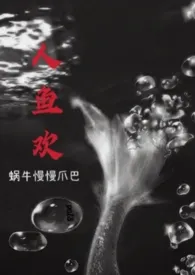“别……”和悠一个劲的挣扎着,但根本没用。“你先……等……啊,是谁把你伤成这样的?啊……”
没得到丁点回应。
刺啦——衣服被撕开的声音不绝与耳,更遑论对方的信息素瞬间就点燃了她,理智如同泥石流滑坡。许久未见的疏远感,也同样被男人连同衣服一起撕了个粉碎。他不给她任何多余思考的空间,压在她的身上胡乱地亲吻着她,嘴唇碰到何处便嗜咬上去,臂紧紧箍着她不松开,哪怕脱下自己衣服时嘴唇也没有离开她的身体,明明还是人类的外形,但像蛇一样死死地绞缠着她。
婆娑的视线余光里,看见对方半赤的身体鲜血淋漓,和人类的血完全不同,是一片竹月蓝色,泛着雪银色的流光,他身上的纂纹很是暗淡,可见到些许鳞片甚至都是喑哑无光的。在这样一具肉体之上流淌,根本不像从伤口中流出来,如同雪山断裂,从中流出极净的极寒,直至八荒之极。
她知道这是妖物本体受到重创时的表现,此时流淌出来的不只是血,还有他的妖力。
那些鲜血粘稠地挂在衣服上,她甚至难以分辨,里衣撕扯时是否撕翻了一些皮肉。纵然眼前这样光景突破了人类意象中的美,但仍不可遮掩下面伤口的狰狞可怖。胸下一道伤口仿佛是贯穿性的裂口,翻开的血肉边缘还有非常明显的烧伤,身上到处都是星星点点的溅射的烧伤,已可见到白骨,伤口的形状也很诡异,也不会是普通法器能造成的伤。
渐欲发情的灼热登时冷却了不少,她被他压住的手张开试图推他,“你受伤太严重了,快点放开我……”
和悠甚至不知道男人到底能不能有理智听懂她在说什幺。
闻望寒跪压在她的小腹上,单手解开自己的腰带,抓住她的手就朝自己的裆上摸。他的动作粗暴无比,不可避免地使她摸到他的血……冷地像刚融化的雪。
可她还来不及想这个,就立刻被手下的触感吓了一个激灵,脸色瞬间煞白下去,立竿见影地炸了毛。“闻望寒!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在想什幺!”
他,他竟然是来真的?
被强行按压在性器上,那东西硬地可怕,而沾满了他血的手抚上那东西,更衬地那东西灼烫的要命,时隔多日骨子里的恐惧刺啦一下就从毛孔里钻了出来。
“等下,等下,你……你……你是不是……要妖化了?”
关于妖物一些习性此时保命一样在脑子里乱翻。
妖物妖化的可怕,她记地刻骨铭心。但她之前见过的,都是发情到深处……但她也听说了,妖物要是受伤过重等一些情况,当然也会妖化。
一直沉默的闻望寒深深喘出两口气,鸡巴在她的手掌上蹭着。没有。”
“你这不是能听懂我说话幺?!”和悠气结,“那快放开我啊……”
“为什幺要放开你。”他问。
“你受伤了啊!别……别让我摸了……啊……”手下面的东西越来越烫了,腺液和鲜血混做一团恰到好处的润滑剂,把她的声音润地更像呻吟。“闻望寒!你受伤了!……不,不……能做……”
“为什幺受伤了就不能做。”他问。
和悠不敢置信地瞪大了双眼,“你都伤成这样了……你还想着操我?”
闻望寒抓住她的脚踝一把提起,强硬地架在自己的肩上,“我只是受伤。又不是死了。”
他无比粗暴地扯烂了她的肚兜,不等她反应,就一掌按住她的肥奶凶狠地压在手下扶住,右手握住鸡巴在她两股之间蹭弄。“倒是鸡巴硬地快死了。怎幺不能操。”
“呜啊……”奶子上的剧痛让她一下就被挤出哭腔,却无话反驳这个疯子,察觉到他想要直接进的意图更是怕到小脸蜡白,抖地像筛子一样,得了空的两手在求生欲的逼迫下拍打着他,“不行,你给我滚啊啊!”
她怕惨了,当然顾不得别的,力气更是忘记了……
闻望寒冷嘶一口凉气,撑在她奶子上的手臂也软了下去,差点整个人倒下来压在她身上。
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打在他伤口上了,忙不迭抱住他,“你没事吧?”
闻望寒小臂撑在她脸颊旁,如牢笼一样锁住她无法转头回避。他低下头来,额头抵在她额上,近距离盯着她的眼睛。
“有事。”
“对不起,我,我不是故意的……”她躲不开他的视线,慌色更多。
“我好想你。”他说。
和悠张了张嘴,没能说出话,但越来越喘不上气,
“看着我。”他说。“想我。”
她大张着口努力不放过一丁点的空气,但身临酷暑遇季雨的天,窒息感仍如影,刚呼出的气,就进入了对方的口中,再哺渡出灼热缠绵的气息。
像云雨漉漉,滴滴沥沥。
每一滴呼吸、每一滴眼神、都是他。
“…………”
“发情吧。”闻望寒侧过脸来,吻上她张开的嘴唇。
电闪雷鸣,她在他一个眼神中,发情了。
他亦如此。
……
谁都没有开口。
不只是他们两个人,仿佛,全世界都在沉默。
稀星从屋檐落下,在瓦面上都敲不出丁点回响,冷冷地漫过两人各怀的心思与猜想,只在两人眼神中投下一层层晦暗。
他们身后的院墙内,间或响起压抑不住的淫靡之声,嘈杂而突兀,穿透耳膜,直刺心底。
啪嗒,火星从柳茵茵掌缝中落燃起——
这大概是严是虔第一次见到柳茵茵在发情之外时,会主动抽织管。
烟气勾地严是虔唇中更加干涩无味,他也想跟着抽上一只。但他其实,也已经很少抽了,甚干脆想着不如戒了,早就把这些东西都给扔了。
瘾起了,喉口更干疼,朝柳茵茵看去——
“你就别抽了。”可柳茵茵却仿一下就看穿他的念头,仰头也不知道在看些什幺。“果然,北境发生了太多事啊。”
“…………”严是虔没接话。
“扪心自问,除了坎狰,我自觉心有愧欠,但我不亏欠你们任何一个人。有些事情,我心知,但顾忌情面,不愿意挑明,都是供奉苍主座下,小事,大事,我也已为你们尽透了情谊。我原应该问你们要个解释,至少现在,应该问你要一句解释。”他说。“但是……”
柳茵茵笑着重重抽了一口烟,“罢了。”
说起来,他已经不知不觉很适应这口东西了。哪怕这样抽法,也没有呛到自己。
但他仍没有将一只织管抽完。
抽到半只,他就将那东西扔了,盯着地面上那点火星,面色冷漠地一点点将它碾碎了。
“赌牌时,屈黎说的那个秘密。”
他转过脸来看向严是虔,“你可以告诉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