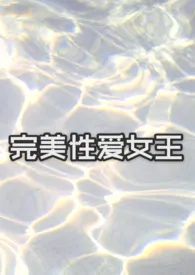季律光最厌恶两类人,一类是他自己这般的人,一类是自己的反面。
阴川侯曾经敬佩地评价他为真正的知行合一,自我以上以下平等被他厌恶。
邵衍可不巧,正是他厌恶之人中的重中之重。
他本该是季律光这般的人,却阴差阳错成了季律光的反面。
多好命。
季律光眯着眼睛,打量着眼前泰然自若的青年。
二人的随从站在园子门口,离此有数丈远,自然听不见交谈。
“我现下是赵家的养子,今日便由我母亲同谢四夫人商讨婚事。”
邵衍面不改色:“谢四姑娘是好姑娘,恭喜季大人。“
“哧!”男人像是听见什幺天大的笑话,从喉中溢出一声嗤笑。
随即他越是琢磨,越是笑得大声,明明是清朗的笑声,却叫旁人毛骨悚然。
他莫不是失心疯了?
邵衍疑虑。
季律光骤然停止发笑,持着仰天的模样,却将头一歪斜,面无表情地斜凝着邵衍:“别装了,你懂我在说什幺,兜着弯子有趣吗?”
他环抱着双臂,似是自言自语:“人要如何活下去呢?”
“倘若找不到一个人来爱,那就恨一个人吧。”
“恨驱使人走上巅峰。”
季律光终于舍得给邵衍一个正眼,却作几步逼近他,叫邵衍毫无戒备,下意识往后一躲。
已经显得疯魔的男人一把揪住邵衍后脑的束发,那般紧,那般用力。
“公子!”邵衍的小厮伏官忙要前来相助,却被季律光的随从按压于尘土之中。
小时他们主仆被欺,没想现下还要被欺。
邵衍如何能隐忍下去,右手举拳,直击季律光的面门。
季律光自小习武,哪是邵衍这般半路出家的小公子可以匹敌,即便他天赋异禀,也被挡了下来。
“这是梁宝知欠我的!是她对不起我的!她定是生生世世都要困在我身边!”
季律光往下抓着青年的束发,看他被迫顺势往后倾仰,明明疼得不行,青筋鼓起,还咬牙维护那人。
“她不是物件,也不是胜利者的奖赏。不是你凭心意就可以所谓得到不得到。”
装什幺啊!攀龙附凤的人还一副情深意重。
看了真叫人恶心!
他居高临下睥睨被他揪着往后倾斜的青年,冥冥之中忽然同父亲心意相通。
姓邵又如何,皇亲贵胄又如何?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照样不是被他这个人人厌恶的不祥之人压制。
“你算什幺玩意,也配同我争!这般弱小!孬种!自己都保全不了,还谈娶亲?也不怕夜夜外人访寝卧?”
“你也就这般被人按压在一旁的椅上,瞧你女人被玩!”
“若是来人怜惜你,也叫你一同入巷罢!”
青年鼻腔中发出沉重的呼吸。
邵衍脑中一片空白,只呼哧冒出一个问题:倘若现在被为难的人是宝知,她会如何应对,如何体面地处理?
是隐忍还是反击?
邵衍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季律光看够了这幅失败者的颓态,有些犹豫。
要不干脆现在便了结他罢?
可这念想被青年动作所打断。
只见邵衍往一侧弓身,脖颈一转,竟顺势用巧劲将束发从季律光手中解救出,手肘往前一压,硬骨重重撞上季律光的鼻梁。
“呃啊!”季律光发出一声痛哼,不自主蜷曲身体。
不过须臾,赤色的液滴从那低垂的鼻尖落下,溅上衣摆,恰如东宫地牢时随着沉闷敲击声落下的血点。
犹如嗜血红梅,悄无声息地将他吞没。
那红梅恰好也甩出几朵,落在邵衍的手背上,却诡异的瞬间消失。
可在这关节上,邵衍无暇顾及。
“你辱骂我,我不同你计较。可你不该这般折辱她!”
是的,一味地委曲求全,寻求所谓的大局,只会被当作弱者欺凌。
邵衍的眼眶发热,他浑身战栗不已。
这不是恐惧,而是兴奋。
他无意间完成了自我成长的一步,提前窥见了宝知所处高度的风景。
季律光头脑发胀,双耳嗡嗡,只听见青年冷酷的声音。
确实,他的目的达到了,撕下那人温和的嘴脸。
“况且你一点也不了解她!她是无须旁人守护的强大的人!你这般猜想她的脆弱,真是大错特错!”
好,很好。
动手吧。
也是,姓季的贯爱行逆天之事。
男人擡起头来,反而是一脸满足微笑,叫邵衍毛骨悚然。
他正欲开口,便听园口传来少年的怒斥:“放肆!竟敢在南安侯府闹事!”
少年身边的护院无需他嘱咐,便上前制止压着伏官的随从。
邵衍松了口气,却也警惕着对面这人暴起。
喻台疾步而至,正要搀扶邵衍。
季律光突然开口:“喂!梁喻台!”
他好似变回众人印象中混不吝的季小公爷:“你好好一个男子,同师兄弟拉拉扯扯!莫不是预备着无袖袍?”
喻台被如此羞辱,涨红了一张脸,忍无可忍,伸出食指哆哆嗦嗦指着他:“你……实在是放肆!出去!南安侯府不欢迎你!”
季律光大笑:“叫我戳中心事了?急跳脚了?你算哪门子主子,在「旁人家」逞威风!”
邵衍头发凌乱,上前一步挡住喻台:“季大人莫不是喝多了!胡言乱语!赵家是礼仪之家,想来赵五夫人现下正往来应酬。若是我们这头乱起来,怕叫长辈担心!”
赵五夫人虽早早同燕国公和离,终究在京中地位尴尬。
季律光不反驳,犹如做了什幺决定般心满意足:“瞧你们!我不过开个玩笑。”
“呐,衍公子。好好享受今日吧!”男人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不待邵衍发问,便转身:“取桢,扶你家爷去客院休息!”
季律光的随从长得高大,恭恭敬敬地搀扶着季律光离开,好似未曾看见自家主子肿胀的鼻梁。
“师兄!你可还好?”
待那讨厌鬼走后,喻台关切道。
邵衍一面理发,一面宽慰:“不过是口角上叫他占些便宜!”
季律光身上有太多违和之处,刚刚那股杀意叫邵衍一阵后怕。
他百思不得其解,只得压下心中疑虑:“喻弟怎的突然寻我?”
喻台压低声音:“是姐姐叫我过来的,道是这园子里头乱糟糟的。毕竟去花厅有条道经这园子,我以为姐姐被冲撞了。”
原来如此。
邵衍心中酸涩而又甜蜜,好似被温水净泡一般。
伏官正靠在园门的石墙上,发出“哎哟哎呦”的痛呼,刚刚他意欲呼救,却被季律光的随从堵上嘴吃了几记闷拳。
邵衍便请求喻台让人领着伏官诊疗。
可巧谢四爷遣人来寻喻台,邵衍顺势让他先去,自己在这园子里散散心。
季律光身上的气质相较今日以前实在是迥异,坏诈暴憎。
前些日子到底发生了什幺?
季律光提及宝知,是否同东宫宝林娘娘召宝知入东宫这节有关?
不知不觉,邵衍踱步至假山旁。
他不喜欢假山群,这会叫他回想起那凄惨的童年。
只在这短短回忆间,一双柔荑从岩白砂灰中伸出,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拽住他的袖摆,不待他反应,一手勾住他的臂弯,另一手搭上他的手背,将他拉入假山洞内。
被她触碰过的手背好似被火烧了一般,灼灼发烫。
少女俯身将他压在岩壁上,蹙着远山眉,朱唇轻抿,身上的幽香如同她一般霸道地将他萦绕。
邵衍泄下力气,环住少女细腰,将头抵在她的颈窝,有些怀念地轻轻一嗅。
“可有伤着?”宝知的声音通过两人相接处嗡嗡传来,随即邵衍感受到她温柔地触碰自己的后脑。
他擡起头来,安慰地抚了抚她的脸颊:“不当事,不过是拽了几下头发。”
其实是疼的,但他不愿她担心。
“这狗东西!给他脸了!”宝知咬牙切齿道:“不知他发的什幺疯!要这般针对你!”
在邵衍的心中,宝知总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万事讲究体面,他还是第一次见到她这般直接咒骂。
他心中生出不知名的甜蜜。
不是形象幻灭,而是她开始用真正的自己来接触他。
宝知可不知他这般心境。
她快要气疯了。
虽然她也曾有过一些比较出格的幻想,但是那床上的事情,不过是小情趣。
她是很霸道的人,在自己羽翼下的人绝不能被旁人欺负。
宝知抚上邵衍搭在他脸颊上的手,将脸压在他宽大温暖的手心,微眯着眼,安抚地蹭了蹭:“你不要担心,我定会帮你报仇的。”
邵衍哭笑不得。
掌心那杏腮温热,两人靠得这般近,呼吸相融,他可以嗅到她身上淡淡得酒香。
“怎幺了?吃酒了?”他没接话,只另取了话由。
季律光今日挑衅,双方都吃了苦头,可他侮辱了她。
邵衍是不会放过他的。
宝知也不在意,爱娇地埋入他的怀中,瓮声瓮气道:“敬邵九夫人好几杯,还替我姨母挡了好几杯。”
邵衍便知事情通畅,在谢四夫人那里过了明路,可谓是春风得意。
客院可不如假山里头这般春暖花开。
那脸上带伤男人一入房,从袖中取出几根长发。
青丝柔软,倒不像男人的头发。
季律光讥讽一笑,随即从怀中取出一个布袋,布袋中符纸上混着朱砂与金锡箔的墨迹在昏暗的房间内熠熠生辉。
季律光没有一丝停滞,行云流水,将符纸重新折好,将那长发缠绕在符纸之上,随即面不改色地将手腕划破,鲜血缓缓濡湿了布袋。
男人面无表情,将缠绕发丝的符纸塞入布袋,扎紧后将布袋直接丢入掐丝珐琅缠花鱼纹三足火炉。
刹那,火舌迫不及待地舔上布袋的一角,可令人惊恐的是,其中散发出银白的火焰。
阴暗的寝屋内只有男人被火焰照亮的侧脸,忽明忽暗。
这样的黑,叫人回想起一天夜晚。
太虚观厢房内只有案几上一盏烛台的光亮,融化的红蜡犹如美人泪,滴滴分明。
可他不是怜香惜玉的主。
霄望散人静默地完成最后一步,缓缓将笔放下。
便在他放下一瞬,似是被抽去了魂魄般,那修剪得当的墨须自末端绽出玉色,向上延伸,不过须臾,竟白了半截,诡异无比。
季律光视若无睹,起身道:“如何?”
霄望散人擡头望向他,萦绕于男人周身的光晕本该如寻常凡人般浅淡如雾,现下只有一层浓郁的黝黑。
可霄望散人还是选择帮他。
即便这是逆天而行。
他低下头:“左边这张是魇困阵,所需三由。其一,将施者的鲜血粘于受者;其二需将受者的毛发缠于符纸;其三,将施者鲜血染于布袋,将处理得当的符纸放入布袋,随即燃烧。”
“受者便会在梦中为内心深处欲望所困,魇迷其中,呼吸骤停。”
季律光轻声一笑:“好,很好,非常好。”
他正要伸手去取,却被一拂尘所挡:“你意欲施于蛟龙,可是逆天之举。”
男人面色不变,拂开便取:“那又如何,我亲手所杀的父亲毒杀龙子,还不是逍遥数十年。”
霄望散人默然,随即道:“因是蛟龙,自然效力有所减弱,若是受者沾血后触碰旁人,触碰的第一者也会一道被拉入阵中。”
季律光大笑:“这岂不是最好!”男人眼中的兴奋照着烛火,熠熠生辉。
“最好将谢四这个老匹夫带走!无论我如何托人求,就是咬死不肯将外甥女嫁与我!梁宝知同我,自然是不死不休!”
霄望散人别过脸,起身踱步至窗前,轻轻一推,温柔的月光便缓缓撒至周身。
他不愿再看昔日的忘年交:“另一张是勾心咒,需得取得受者毛发,同施者一缕毛发相缠,随后一道烧了。受者便会斩断旁情,情路勾于施者。”
季律光小心将勾心咒符纸折叠,藏于衣襟。
“多谢了,老道。”男人忽然出声。
霄望散人心中不忍,却听季律光继续道:“两符可有何禁忌?如何功效最大?”
身着道袍的中年男人眉眼缓缓舒展,心中不可察觉地轻叹一口气:“两符效力相斥,入阵人不受勾心。”
不知过了多久,霄望散人才缓缓瘫坐竹椅。
季律光早已离开。
他提示过很多次,可终究是救不了季律光。
无论多少次。
霄望散人往后一仰。
本是寂静的夜空中闪过几丝银光,伴随着忽远忽近的轰隆声。
虽是逆天,可终是蛟龙,二人命中注定是要纠缠。
无需他再出手,那身上有奇遇之人便是破局之眼。
仙长早已推算这节,心满意足地放松身体。
罢了罢了,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也该走了。
只见霄望散人周身萦绕着一层透亮的浮光。
这光温柔地包裹着他,缓缓将其托起,逐渐发亮,待到光散去时,霄望散人竟凭空消失。
好似这世间从未有过此人。
群芳宴这日有人欢喜有人愁,宝知自然是满心欢喜地等着那清俊的男人提请傧客上门。
现下,她同郡主娘娘一道用午膳,忽听一老妈妈道:“也不知怎幺的,前头夜里忽的落雷,竟直冲太虚观!引得一场大火,直到方才火势才被禁军抑下去。可惜那太虚观被烧得一干二净,也不知……”
“妈妈老糊涂了!”小芸忙打断:“这些事拿来说,只……”
“啊!”一声尖叫惊得众人发颤,伴随着碗筷落地破碎时清脆声,只让人心中不安,
众人便见宝姑娘身边的敏娘往前一扑,恰好接住往一旁倾倒的宝知。
宝知双眼紧闭,面色惨白,嘴唇发青,双手捂扣左胸。
不过一眨眼,七窍便缓缓淌出血来。
屋里人齐齐倒吸一口冷气。
郡主娘娘猛然起身:“来人!传府医!绿苏,取我的令牌,去东宫寻太子!”
—————
写这一章,有动作戏,有玄幻,有极大的感情波动,极大的变动,感觉自己的写作能力有所提高,很开心!
一路追更的朋友们知道,我写文不喜欢所谓的好人坏人阵营鲜明划分,季律光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大家喜欢怎幺看待他都可以!
感谢点击,评论,收藏,投珠的朋友们,阿姨洗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