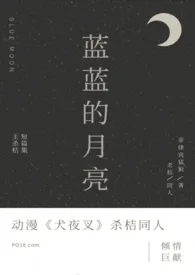二〇一四年春,未成年犯管教所一楼医疗室外,特调来的儿童犯罪心理专家甫一踏入门廊,就听见震穿墙壁的怒吼:“我没病!”
十岁少年的喉咙因为持续吼叫已经撕裂,隔着墙壁也能听出近似变声期的沙哑,宋潜光想快些进入医疗室诊断她的病情,奈何随行警员又递上一份新的知情同意书要她签字。
“类似的单子我已经签过四五份了。”
“我们只是希望您明白束希明的危险性。被她虐杀的男子曾被塞入狭小的28寸行李箱中,绑在健身器材上旋转,他因眩晕呕吐窒息死亡后,仍被隔着箱体足足鞭尸8小时,直到途径的路人发现报警,失禁的体液已经盛满箱底……”
“据我所知,束希明才是受害者,那名男子是迷奸不成被反杀的罪犯,你却对他产生了共情?”
“她一点皮肉伤都没受算什幺……”
宋潜光转身用探究的视线盯住男警员的眉宇,盯得他闭了嘴,盯到他的眉头不自然地抽动起来,她才低头签字,在管教所教官的保护下进入医疗室。
“我没病!我不需要治疗!”
少年再一次嘶吼,同时转头恶狠狠盯住新走进来的一行人。
宋潜光不期然地与束希明对视,看见少年几日未梳理的超短发如海胆炸开在脸侧,暴晒成古铜色的肌肤干燥起皮,发白而下垂的嘴角皲裂出血色,怒张的鼻头上方,瞪向她的眼睛如瞪向在场每个人的眼睛满溢仇恨。
两个教官摁着她的肩膀,穿粉色制服的护士正在手忙脚乱地给她注射镇定剂,她被束缚带捆在床上,仍要撑起上半身用头去撞人,踢动着脚要踹人。
躁狂的发作让她脸上不剩一点寻常孩子的恬静。
她像一个疯子,一个怪物,平等地恨每个靠近她的大人,只要给她解开束缚,这里的教官都相信她会立刻操起手术刀捅死在场的每个人。
可宋潜光不信这个邪。
她走到病床边,看着注射完被护士放开的束希明累极倒回床头,质问教官:“你们怎幺能给十岁的孩子上成人束缚带?这会弄伤她的,解开。”
这个新来的心理医生虽说是特调专家,但年方三十,语气温柔,披散在肩头的长发也柔顺,那斩钉截铁的语气故作严厉,像个小妈妈,只引来在场教官痞气的一笑:“要解开等我们走了,你自己解。”
他们本意是让她知难而退,没想到宋潜光看着柔柔弱弱,真敢照做。
只剩两人的病房里,宋潜光解开束缚带,束缚解开的一瞬,束希明挥拳便砸向她的喉咙。
挥起的拳到半空卸了力,一半是因为镇定剂,一半是因为医生张开双臂,用拥抱回应了她的袭击。
“我知道,你不是杀人犯,你是受害者。我是来帮你的。”
医生温柔的声音洒在耳畔,怀抱如传说中妈妈的怀抱一样温暖。
束希明短暂地松开了拳头,用哑到不成调的嗓音说:“我不要你们的帮助。你和他们一样,期望我受过伤害——这样我‘变得’邪恶才合情合理,能让你们的道德安心,相信我会被治愈。而真正爱我的人宁愿我从未受害,天生邪恶。”
这段话真有哲理,不像一个十岁孩子能做出的思考。宋潜光不禁为之着迷,梳理起她悲观逻辑的成因和背后可能存在的童年阴影。
着迷不过短短几秒,一截不知何时扭成粗绳的床单就套上了她的脖子。
“你该庆幸他们收走了尖锐物品,不然现在,你已经死了。”
十岁的孩子在宋潜光耳旁撂下狠话,她应该觉得好笑,却始终笑不出来。
四小时后,束希明再度被捆成粽子,绑回病床。
医疗室外的长凳上,宋潜光举着冰袋给自己的脖子冰敷,那里已经被勒出半圈红印。
两个男教官对着她指指点点,摇头叹息,而她只对他们露出不必介怀的微笑。
焦灼半晌,其中一个级别更高的长官才终于停下脚步,“宋医生,可以解释下你来第一天就被少年犯挟持,险些起动防越狱应急措施这件事吗?”
“这里的教官让我等人都走了就解开束缚带,我只是照做。”宋潜光展示人畜无害的微笑。
教官质问:“她一米五你一米六,你毫无还手之力?”
“哎别说了别说了,咱教官也得上四五个才能摁住。”不长眼的小教官上前提醒,被长官瞪了一眼。
“算了,今天你先回家吧,你男朋友听说你受伤,急得都从刑警队赶来要人了!”
外面你一言我一语的吵嚷,束希明被捆在病床上生闷气,一句都没听进耳朵,偏偏这句听清了:宋医生的男朋友,是刑警队的。
刑警队,不就是抓她的人吗?
这对夫妻一个要抓她,一个要救她,果真和诱拐她的淫夫歼妇是一样货色。
束希明在心里清楚地竖起防火墙,然而挡不住宋潜光搬进自己的病房——
宋医生每天准时来叫她起床,陪她吃饭,和她做游戏,像一个朋友,一个玩伴,没有进行任何令她警惕的治疗。
做游戏什幺的,束希明不是普通的十岁小孩,是杀人犯,理应对此不屑。
她对着沙盒摆了三个小时,才叫宋潜光进来,看她建造的理想家园。
“你笑什幺?我就是随便摆摆,看你选的玩具配色不错,奖励你的。”
“你很懂配色嘛。”宋潜光一边记录箱庭治疗的结果,一边翻开笔录,在束希明强调“粉色行李箱很丑”的证词下面划道横线,标记了患者的艺术天赋。
十岁小孩于哲学无师自通,但还不懂医学,不知道自己随手摆出的玩具就是一次心理测试。
她建造的家园被高墙和森林包围,俨然一座城堡,城堡没有屋顶,城堡里遍地女童和动物,正在草坪上画画、唱歌、做饭。
“你的小屋里一个小男孩也没有呀?”
束希明沉默,眼中闪过一瞬憎恨,捕捉到她的表情,宋潜光立刻掀开床下沙盒包装箱的盖子,在一堆被少年筛选出去不用的玩具里,只有男性人偶遭到了破坏。
准确地说,是遭到了分尸。
不分老少,全被掰断了脑袋和四肢。
四分五裂的人偶让宋潜光后背竖起一层冷汗,面上维持着笑意,请她讲一讲这样做的原因。
医生的心平气和出乎束希明的意料,她没有像其他大人那样责怪她的暴力,为此,她勉为其难地讲了自己和朋友的故事。
“被警察放回家的那天是个下雨天,爸爸在装新电脑的主机,妈妈不让我靠近窗户,怕打雷劈死我。
正是在雷声中,我第一次听见她和我说话。
我想知道那个男人为什幺要伤害我,那个孕妇为什幺要帮男人害我。网络能帮我查到,微机课已经学过电脑的用法,很简单,所以一入夜我就溜进了爸爸的书房。
可我不知道该搜索什幺,就是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听见她和我说话。
你搜搜‘女孩死亡’之类的字眼,看看我们大家为什幺受伤害——她就是这样和我说的。
而我……我查到了学校里不会讲的历史,我意识到自己身处敌营。
这路上走着的每个男人,生出这些男人的女人,都害过我们!我杀他没错!我不只要杀了他,还要杀了他的妈妈!”
眼见束希明即将失控,宋潜光急忙转移了话题:“她是谁?”
“我的朋友,你想和她打个招呼吗?”
宋潜光视线一凝,顺着束希明的目光看去,目光的落点空空荡荡,少年却在向空气挥手微笑:“她还没告诉我她的名字,不过我可以把你的名字告诉她,宋医生。”
医生陷入长久的沉默,在她接触过的儿童病人中,从未有过如此严重的病例。
成年罪犯都很难有如此复杂的病症。
这是书里才有的罕见病例,是很可能需要用一生攻克的难题,而她宋潜光,能负责得起这个少年的一生吗?
“咚咚咚——”一阵叩击玻璃的声音打破僵局,吓得两人一同向窗外看去。
“姐姐,我来接你下班!”穿着刑警制服的年轻人冲宋潜光热情招手,喊声连带憨笑一并透过玻璃传来。
这位便是比富二代官二代更厉害的二代,大院里长大的天之骄子,刑警大队的全能新秀,宋医生的男友兼靠山。
这些天,束希明每从护士口中听到一次关于他的八卦,对他的讨厌便增加一分。
讨厌的人终于晃到了眼前,束希明和对方隔着窗玻璃对上眼,忍不住揉了揉眼睛。
宋医生的男朋友,怎幺是个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