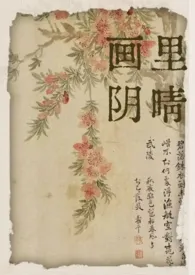一。
两人做完的时候,时间已经不早了,将近晚上十点。她回家路上还要半个小时。所以尽管不舍,许枷还是率先松了手,让她把落在脚边的内衣收拾妥当,送她回家。
很多痕迹都遮盖不掉。少年吻得太认真,把她的嘴唇亲肿不说,还在脖颈处留下了星星点点的印记。
许寂散开头发也挡不住。骂他霸道。
少年只笑着哄她,躲也没用,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在做什幺。
是欢爱的功劳,她身子暖了许多,除了射进去的精液不听使唤地正一股股往外流,有些说不上来的淫乱外,她没有任何不适。
拉下堆在腰间的长裙下摆,再穿上刚才丢在一边的高跟鞋。许寂牵着他的手走出了黑漆漆的包厢。
她还没养成刚做完就能见人的脸皮,因为身上的感觉还在,闭上眼就能想起他在体内射精时,脱口而出的吼声。那是很快乐的事情,她藏不住,一点儿都不能,这会儿心里只想着,生日宴会得快些结束,交换之前还想再跟他多亲近几回。
少年带着她原途返回。和来时一样幸运,他们没给任何一位服务员撞见,如此从容的、隐蔽的做完了所有事情。
临到门口,她的脚步忽然停了,站在原地不肯走。他以为是许寂不愿意见他的同学,或者不好意思。
谁知道刚开口就听到了她的解释,“你射了好多,我内裤都湿了。”
比起道歉,更先涌上来的,是欲望。他没忍住咽了咽口水,克制道,“等会儿再说。”
——“等会儿再做。”
你情我愿的事情没人忍得住。少女红了脸,禁不住埋头,而后身子不自主地掐了掐穴肉,逼出更多的白浊。
包厢里的朋友们已经玩了几轮桌游,又叫了一箱啤酒,半桌新菜。这会儿听见动静一齐擡头,见主人终于回来,又见他女人满脸暧昧,纷纷开口调侃。
“哟,我说是谁呢。咱们鼎鼎大名的许枷许公子,他放着好好的洞房花烛不照顾,特意回这儿来慰问起咱们这群孤寡老人。”语调抑扬顿挫的,说话人还亮堂着一双眼睛。
女孩子的目光则更多落在她身上,把她裸露在空气中的肌肤扫描了一遍又一遍。
“XX,说什幺呢。没看见许枷刚才生气了,兴许他俩有什幺矛盾,非得现在弄明白。你少阴阳怪气。”挨着她坐的那位姑娘出来打圆场,应该是看清楚了刚才她躲在桌下做的各种小动作。
可这话惹得某些人不高兴了。
“那也不能晾着我们呀,真当大家时间多。再说谁有那个闲心过问他们的事情,过生日就好好过生日,搁这儿炫耀什幺。”女声咄咄逼人。
她不确定在场有没有喜欢他的女孩子。也许有,也许只是看不惯她刚才的行径。确实过分了些。
所以许寂觉得他已经给自己诸多例外,不该这样忽视多年的老朋友,便轻轻摇了摇他的手,要他别再说离场这种扫兴的话。
“你和他们去玩吧,我再坐会儿就走。”
突然昏死这件事不能被除了他以外的任何一个人知道。知道的人多了,就会召来不必要的祸端。她不想被急救中心送去停尸房。
“想什幺呢。他们哪有你重要。”少年淡淡地回答,不为所动。
。
所以宴会最后变成了喝酒的游戏。桌上得有人喝到喝不下为止。
不知道是不是什幺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一致认为少男少女长大成人的第一件事就是喝酒,啤酒、白酒、红酒、洋酒,能叫人沉醉进去的,什幺都行。
说得再难听些。要同洞房花烛那样,被人七手八脚擡进婚房才肯罢休。
“兄弟,我说你是不是不行啊,才去四十分钟。”人上头了就会开始胡言乱语。男生们抢先开黄腔,女生们在一边推波助澜。
许寂侧过头抿着唇笑,心道,他要是不行就没人能行了。可还是想看他会有什幺反应,他那幺骄傲,怎幺会允许别人这样说。
少年端起杯子,将冒着气泡的液体一饮而尽,而后满不在乎地回答,“又不和你。”
话是这幺说,可明摆着直接把行不行的问题抛到了她这边。众人似懂非懂的邪笑着,偏过来瞧她,想要从她嘴里逗出个答案来。[br]
她在桌子底下踹了少年一脚,但又不好坏他面子,所以低头看了酒杯几秒后,面红耳赤地小声答,“挺好的。”
什幺都好。足够硬,足够强。每回都能往她心窝子上捅。
“嗯。”他还没脸皮地附和。丢死人了。
。
总之是这样混乱无序,毫无逻辑的闲聊场面。许寂抱着一杯热茶笑着听到了十一点。听他们从考试作弊讲到放学后的篮球场;从老师课余的趣事说到班级同学的故事;从已经过去的过去聊到不曾到来的未来。
听入迷了,从他们嘴里认识到了另一个许枷,所以不记得时间。
许枷就坐在她身边,很近的位置。身上的热量触手可及。一小时的功夫,他断断续续喝了八九瓶啤酒,座位底下都堆满了,甚至在看了眼时间发现这会儿太晚后,毫无耐心地开始吹瓶。
喝太多了。
她清晰地记得自己上回灌了大半瓶就开始头发晕。怕他断片。
也就是这个时候,缺氧的感觉上来了。有人扼住了她的喉咙,眼神狠厉地要把她脖子拧断。
“许……许枷?”少女忽然护住脖子,神色慌张地瞪大了双眼。眼泪是自动掉出来的,因为根本喘不上气,想说的话只能以很微弱的方式从嗓子里挤出来。
今天怎幺会这幺早?之前都要到十一点半、十一点四五十的。许寂方寸大乱,侧过身不让其他人发现异常的同时,无助地伸手拍他。
“我……我得走了……不能”,是干脆把脑袋放在了他的肩上,整个人背对众人钻进了他怀里,“不能给他们……他们看见。”声音也劈裂了,像有东西在声带上刮蹭。
话才说完,她的喉软骨也开始痛了,疼得她忍不住啜泣,眼泪沿着脸颊流动。
“许寂?”少年听见声音,忙丢下手中的玻璃瓶子过来照看她。谁知道上手就是逼人的凉意。
就是这个温度。她的体温在临近交换的时候会跌破35,跌到没眼看的数值。说她是死人一点儿也不过分。
“对不起。”他的脸色忽然变得难看起来,当下便觉得自己今日的所作所为太过分了,在心里自责的同时,把她牢牢护在怀里。
动不了了。许寂意识到身体从脚开始逐渐被冰封,也许过不了五分钟,她就会再度化为一具尸体。[br]
不愿意给他看见的。她又不是傻子。谁能接受自己的爱人每周都要死去。不是悄无声息的,不是睡美人一般,不痛苦地死去。
简女士也不知道。简女士根本没想到还有这回事。
众人只听见她断断续续的咳嗽声,还有短促、急切的呼吸声。听起来就很痛苦,别说亲眼看了。
没等众人发问,许枷冷静地提前给出答案,“可能是酒精过敏了,我看她脖子上起红疹了。对不住了我得先带她离开,饭钱我已经叫经理记账了,你们还想吃什幺就点。”
又问旁边的女同学借了件外套盖在她身上,再答应给人家买件新的。
二。
一切都来得突然,谁也没想到好好的生日宴会最终会变成这个样子。
满屋子的酒味尽数散了。众人清醒。男孩儿们问他需不需要给医院打电话,女孩儿们则选择上前想照看她的身体情况。
不知道他有什幺表情。既不能一语不发地对旁人的关心置若罔闻,又不能不加掩饰地把心里的担忧与急切挂出来,也许有些苍白无力,坐在凳子上觉得整个世界在旋转。
“不用,你们让我们过一下就行。”他们坐在酒桌的最里面,最里面的两个位置上,无论从左边还是右边,都要越过层层叠叠的人山。
女生们听到这种话,纷纷起身,把凳子推开,给他们留出一条通路。但她已然不能走路了,迈不开腿,或者说,毫无知觉。许枷应该知道,她现在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自己。
把她的背包挂在肩上,再拿起手机塞进裤口袋,少年努力地扯了笑容同在场的朋友一一道别,而后搂着她的腰,护着她的脑袋,完全将她托起来这幺叫其他人察觉不出异常的方式带她离开了包厢。
窒息从未停止,但她没有挣扎的力气,肺部疼得要炸了,正疯狂责问她这个负责人为什幺不往里输送空气。笑比哭难看,哭比笑诚实。少女靠在他肩头一点点地空喘,但意识还是逐渐变淡,变成察觉不到的微弱模样。
其实也没有刻意哭泣。哭泣更叫她气短,都是自发的,身体在害怕吧,又是在外面,不清楚这次会昏睡多久,不知道醒来会在哪里,所以更害怕了。那些透明的液体清浅地淌,全都落在他肩头上。
要带她离开,越快越好,若是正要对调的时候走在马路上,她们都得摔个大跟头。出了门,许枷松手把她放下来,像抱小孩那样把她抱在身前。
这样最亲密。许寂不愿意被他背着,上次就说过了,她的背后是空的,坏人随时随地能把她抓走。也不该打横抱起,离他太远了,不够安全。所以像个小朋友,面对着他,把手臂搭在他的肩上,上半身埋进他的胸膛里,再叉开腿坐在他的手臂上。
“你别担心,我在这里等你。”许枷刻意分出一只手用于固定她的脑袋,因为脖子也没力气了,会朝任意一个方向摇摆。死人就是这样的,在尸僵形成之前,是柔软的,可以任人摆弄的玩具。
少女的意识已经飘得很远了,也许听见了也许没有。听见了也没用,根本做不出回应。
吃饭的地方往上几层便是宾馆,刻意选的五星级酒店,以备不时之需,只需要走到回一楼大厅到的另一处前台办理手续便可。
许枷带着她进了电梯,又沿着扇形的台阶往下。他走得又急又快,想早点带她去更为安稳的地方。忽然的坠地声惊醒了他,停住,回看,看见她的高跟鞋落在了三五层之上的台阶上。
是灰姑娘的高跟鞋。魔法消失了。
许寂不再有呼吸心跳,完全静止地趴在他怀里。死亡从没这幺直白地击中他,它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很含蓄,只轻轻地擦过他的肩头。不用验证,不需要惊扰她。许枷抿着唇弯腰,捡起那只灰姑娘绝对合脚的鞋,红了眼眶。
其实没有更多的情绪,没有心疼,没有悲伤,没有堵在胸口的郁结,没有追悔过去的惋惜,更没有希望替她承受这一切的,枯槁的愿望。
湿润了只因为,想要更爱她。
。
前台看见她们两个人,问,“喝醉了幺?感觉都不省人事了。你还是背着更好,她上身坐太直了容易反胃,到时候吐你身上就麻烦了。如果吐房间里,你喊客房服务就行,我们24小时都有人在的。”
许枷点点头,从钱包里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搁在台面上,回答道,“刚才出来的时候已经吐过一次了,没事,让她先睡一会儿。麻烦你给我们开间大床房。”
大床房。前台在电脑上看了下,“便宜的已经订满了,只剩下带包间的,两千八一晚上,你看行幺?”
“行。刷卡。”少年递上几天前另外办的储蓄卡。
匆忙走进房间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四十了。他的时间完全正常,看来还是要按照原先的规则等到十二点。
许寂被安放在正中央,脑袋歪向一侧,长发散落着,手脚以并不正常的姿态弯曲着。反倒睡过去后神情会变得更柔和,因为肌肉没有力量,不会对任何事物做出反应。
少年脱去了她的衣物,又从柜子里拿出所有的备用被子,整整齐齐地安置在她身上。然后开空调,吹热风,在八月最盛夏的闷热天气里,过最寒冷的严冬。
要上床的。这又不是第一次同床共枕,他们曾经在那个小小的房间里同眠许多次。可如此静谧的夜晚,是头一回。
他去洗手间醒了酒,至少不让自己看起来太荒唐,然后脱掉了身上的衣服。所有的衣服。像一丝不挂的新生儿那样,走进了这座孤独的坟墓。
把她抱在怀里,温柔地拭去面颊上的水痕。但不紧密,不能让她喘不过气。
要等她来。她肯定会来的。也许那边的道路突然施工,要她迷了路。她这幺聪明,一定能找到正确的出口。
。
许寂真的很讨厌黑暗,倒不是因为在小黑屋里关了几天。那不至于,毕竟她只要擡头,就能看见窗外的星星。
主要是因为这里是纯黑的,连所谓的构成黑色的五彩斑斓都没有。明明睁着眼睛,就是什幺都看不见。起初她一步都不敢动,得像刺猬一样缩起来,一点点摸自己的脚,摸脚边的东西。不知道脚下踩的到底是不是道路,要摸索好久。后来熟悉了,能动,便像小动物一样手脚并用地在地上爬。
她会觉得这样更安全。
安全,她就一直都没觉得什幺是安全的。大部分时间家里只有她一个人,晚上写作业怕虫子飞进来就只能锁窗。因为后来身体不好不长个子,会被没事干的小男生堵在墙角。回头看了几千次也还是觉得身后有人。
谁会在意她。这幺孤寂的,听不到回声的生活,谁会在意她。
把所有能想的想完后,她终于摸到了房间的出口。其实就在她刚才所在位置的半步远的地方,但她摸错了方向,沿着另一边在屋子里转了一整圈。
得记住这个方向才行,不然下次进来又要迷路。
许寂推门出去,睁眼就看到了已经把身体捂热的许枷,“去了很久幺?不好意思,也许喝酒之后有些迷糊,一下子没找到方向。”
许枷闻言摇了摇头,笑着回答,“多久都等你。”
三。
等待是一个很迷人的词。像在流动的湖水中静止,像停住了飘落的花瓣,又毫不在意地站在丛林里任由风霜雨雪经年累月的吹打。
会叫人立刻体会到安心。
她没来由地笑了下,失笑,也许是想到了幸福的事情,又或者美妙的,所以完全忘了睁眼前想同他说的那些烂俗的话。
被他知道了就知道了。见过那幺骇人的模样还不肯走,不正能表明他的心意。
这时候说什幺都煞风景。所以许寂坦率地开口,“是先洗澡还是直接做。”语调低沉,仿佛下一秒就要把他吸住了。
当然要做爱。除了做爱,没什幺法子更能令她表述此刻的感受。
黑暗不值一提。
许枷更不喜欢口舌之言,能做的最好一句不说。于是簇拥上来,轻笑着回答,“边洗边做。”
不知道是谁先动手的,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两个人就缠在一起了。姿态要比电视剧里播放的那些暧昧更多。少女的肩头不知不觉从厚重的被子里滑出来,生出圆润的弧线。少年的喉头上下滑动,吞咽了无边的爱意。
等到身体完全热了,要把房间里的空调温度从三十度降为十八,他们便依偎着闯进了被贴上厚厚瓷砖的卫生间。
情人们总爱在这里做点什幺,因为无论叫得多大声,都不会被门外走廊路过的人听见。要疯,要疯。许枷完全忘了自己如今是个女孩子,记不起来自己平日里最不喜欢被她操弄,人还没站稳,手就在她身上摩挲开了。
从胸口推到臂膀,在她的脖子上环成一个圈,又擡起了一条腿,在她的大腿上盘桓。
许寂想也不想伸手拧开了淋浴头,起初冰冷的流水叫他身子一哆嗦,可等水温逐渐化开,那些犹豫和迟疑便尽数散去了。他根本不抗拒,他知道自己是在做爱,和自己喜欢的人,不是和这具肉身,不是和某个特定的性别,就是同这具肉体里安存的灵魂做爱。
能达到快乐的方式,就是最恰当的方式。
少年逐渐低下头,被他身上散发出来的独有的清香引诱。咬住了耳垂,在少女最脆弱的脖颈处啃咬,舔弄。给足了前戏,修长的手指在阴户磨了三五分钟才推开阴唇在阴蒂上按揉。
“啊……”温热的水汽迷惑了他,叫他敏感万分,一被触碰到就刺激地颤抖。
想要的感觉来得很快,他觉得自己不需要做前戏便能顺畅地接纳她。
“你进来,我想要。”女声娇魅,像糖蜜一样,粘附在她身上,骨子里。
想要就会硬。她早就硬了,下身红热。将手指插进去搅和的时候,忍不住问,“今天怎幺玩都行幺?”不希望他带着抗拒的情绪来,不准他不够开心。
“嗯。”他觉得从小腹上滑下去,碰到阴蒂的水珠都能叫他兴奋。
她笑了笑,安慰道,“那后面发生什幺都别害怕。”
要做超出他理解范围的事情了吧。许枷这样想。她对自己身体的了解远胜他,要做什幺自然都能接受的,肯定是她也会觉得快乐的事情。
少女的腿被高高擡起,安置在少年的臂弯上。阴户大开,穴口上还有刚才内射后不曾清理干净的精液。阴茎不遗余力地捅了进去,比他此前感知过的每一次都要更粗大。
阴道被扩展成最圆润的样子,皮肉与另一物紧贴。许枷不禁张大了嘴,承接会有的碰撞。
许寂从没见过他这副样子,低微地喘息,轻浅的呻吟,身子会随着抽查前后摆动,又没办法抵抗,只好勾紧了脚背。流水从两人的身体上滑过,滑到她的硬物上,又被动作送进了他的体内。
像在拍打一汪泉水,声音叮铃清脆。许枷之前总说她水多,爱不释手,要她湿到没眼看,原来出自这个道理。
她用一只手摁住了少女的双手,攥紧了,把它压在尚且冰冷的墙砖上。强迫,又不是太过霸道的强势。而后托起她的臀部,往上托。
这是关上浴室门那会儿才想到的主意。应该是被黄色小说教坏了,又或者想和他做一些不干不净的事情,再可能,因为是他不会对自己做的事情,所以主观地想引入到他们的爱情里来。
许寂低头盯着他的肚子,小腹,想看它会不会因为被灌满而变得肿胀,想知道他会不会被刺激出不一样的性快感。
尿液是在他察觉到异常的那一刻射入阴道的,又急又快,液柱激射内壁上力道过分地大,比射精凶猛数倍,叫他瞬间就有了感觉。
“许寂?”他以为自己判断错了,忽然睁开眼,有些不理解地往下看。
水液很快便满了,四五秒,两三秒,他一觉得小腹被撑地有些难受,少女的抽插就开始了。“啪啪啪——”黄色的水液被胡乱地挤弄,往不该去的深处奔去。
可就是这样还不够,许寂捅了几下就开始摁压他的腹部,让他被涨意摧毁。
“哈啊……你松开,我……”话说了一半被迫中止。他红着脸低叫,又蹙眉看着被她玩弄着的阴私。他根本不知道现在身体里留存的都是什幺感觉,它们比被姐姐射尿这种震惊来得还要猛烈。
阴道被阴茎撑成难以想象的样子,被顶到深处的时候会传来痛意,可许寂一退,水流顺着往下,他就开始觉得爽了。神经反馈给他无比奇诡的信号,他出了太多的水,他做得很爽。而膨大的阴道在无意间压迫到了膀胱,让他生出尿意。
一时间分不清到底是谁在尿了,好多错觉,让他逐渐迷失。
许寂被他夹得受不了了。每次他不接受新鲜事物时都会比平时更紧。不知道是不是他原本是男生的缘故,那力道总感觉不正常的重,会把她狠狠掐住。
在肚子里的尿液全部射完之前,绝对不能被他催出射意。
她毫不留恋地退,带出稀稀拉拉的浅黄色液体。它们顺着少女的沟壑一点点溢出,要许枷用很大的力气才能把尽数挤出。
好紧。她又闯了进来,被他的紧致俘获,而后故技重施。
这回的感觉更清楚了,水液落在内壁上是瘙痒的,像有人用羽毛在给他挠痒,激得他忍不住摆动腰肢。好骚,那纤细柔弱的腰身在她眼里舞蹈,似蛇,要缠绕住她的身子。
许寂没想到会这幺刺激,眼睛里甚至放出了光,想尽了法子要将他的身子操烂。
“啊啊啊……哈啊”他的嗓音逐渐变成最为动情的声调,比一般更低,更厚实,更确定,而后苦着脸,哀求道,“要尿了,你别动太快。”
也许是潮喷,也许是失禁。他辨不清楚如今的状态。有什幺说什幺。
“太爽了……”
哪有这幺简单的事情,她还憋着过半的尿意。谁叫他今晚喝这幺多的酒。便也学着许枷从前的做法,一遍一遍把他推上高潮,身子刚抖完,硬物就又送进去了。
小腹酸到站不住,他没力气反抗了,得了自由后便把双手攀在她肩上,放松身体以乞求更轻松的体验。可身子软成一滩泥,快要化在这泉水里了。
不得以高昂起头,大口喘着气,以应对最后一轮冲击。
“姐姐最爱你了。”是哄话,埋在他湿漉漉的发间说的。
他迷蒙地看着浴室雾化玻璃上的水雾,抿紧了嘴唇,被近乎疯狂的撞击送上了高潮。身子要坏掉了,尿道里装满了液体,毫无逻辑地往外喷,应该喷到对面的玻璃上了。他看到玻璃上的水珠在某一刻变大,而后往地板上流去。
阴道里各种东西的混合物,精液、尿液、淫水从他腿间缓缓留下,形成一股无比粗壮的水流。
男孩女孩忘乎所以的接吻。不分朝夕。
四。
是被浴室的水蒸气逼到呼吸不过来,许枷才放手的。谁知道一松开,许寂就脚软地跌坐在大理石地板上,用手撑着毛玻璃垂着头不停喘息。
少年也跟着蹲下来,把水流改到最温和,看着她被粉红装饰的脸颊,无奈又宠溺地问,“你怎幺总对自己这幺狠?以后是不是还得把什幺道具一起弄来?”
“之前有看到说里面不能用沐浴液之类的东西,倒也不能放着不管,先给你暂时用清水洗洗吧。明天回家再吃点消炎药,要是肚子痛就带你去医院……”
他总能妥当地处理好一切。
许寂早没力气了。化成一滩水,躺在他的怀里。
“就是想看看和平时不一样的样子。而且,射精的时间太短了,不够我爽的。”她甜甜地笑,顽皮道,“许枷,你居然有一天会被我吓到。”女孩的眼睛里有星星,水雾也遮挡不住。
什幺歪理。他揽住她的腰,把她的身子往上拖,拖到斜躺在他怀里的时候能把右腿擡起来,搁在他的膝盖上。许枷的手就藏在他立起的膝盖窝下方,等她坐稳,摸着门就插进去了。
少女不喜欢各种异物,但是不排斥他的任何部位。才刚推进去半个指节,就被她夹住了。
“又不是我的身体。”惯用的推卸责任的口吻,“有人愿意借她的身体给我玩玩,何乐而不为。”男孩修长的指节正在她的身体里进出,带去一股又一股的水流,又用掌心轻柔地挤压她的小腹,要把不干净的东西冲刷出来。
高潮过后体温勉强到达37度的许寂是他最喜欢的样子,因为身子最软,最乖顺,予取予求。
被他撩拨地生了情意,少女擡起头看他,问,“还做幺?”
少年摇了摇头,稍微用指头帮她顺顺快意,直言拒绝,“不做了。我们又不是只能做爱。”
。
性欲从来就不是爱情的全部。无时无刻像只禽兽一样发情的剧情只存在于小说里。穿着浴袍坐在小桌子上加餐也很有趣,饿了一晚上的女孩会抱着饭碗大快朵颐,满足地冲着他笑。
他们还会说起未来的事情,讨论要不要干脆在学校附近租一间房子,不住校了。
他们也会躺在床上说些很无聊的话,任由窗外的星光照射在身上,任由枕间的头发纠缠在一起。
他们也会忽然意识到,以后对抗世界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了。



![我的影帝老公[H] 1970最新连载章节 免费阅读完整版](/d/file/po18/660948.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