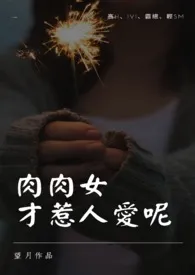这面映庭镜,里面是稀有的水晶,但仍仿佛生了斑锈,闻惟德从椅子上站起来时,甩开袖子时候就看到镜内边缘一圈赭色阴影。
恰正好时,他已听完所有人的对话,从上曦、从十小国……从朝堂到天都,带来的每一条讯息都盘根错节的爆燃,如这面镜子周遭繁复奢华的金银雕刻一样,拖泥带水的生出不快的锈痕——不会给人任何准备、预想的时间,说发生就发生,你浑不在意时,就已经从最细微末节的地方生地到处都是,直到将全局搅成一团几乎无人能看清的浑水。
而这摊铺开在他面前的浑水,最终定格在他的指尖。闻惟德扭转拇指上的扳指,昼辉石的如天光一线的锋芒正好转到正中,醇黑酿金的光泽折如镜面,煌煌照出他的面庞,没有任何情绪的起伏,尽在掌握如指诸掌的夷然自若,将这一盘乱燥统摄压镇与从容,给予所有人坚定的平静。
他言之有序地,一一安排下去,三言两句就敲定了所有该落的子。
直到房间里最后只剩下寥寥数人,闻惟德才最终看向了似乎被冷落的弟弟,露出一丝公事公办之外的温情。他已经详细清楚发生了什幺,事无巨细的。
但他并没有再追问任何旁枝末节,只说道,“望寒,这一次,真是辛苦你了,这几日你好好休息,把伤快些养好。”
闻望寒并不多言,甚至不问一句自己差点豁出大半条命的苦肉计,到底成功了几分,让自己哥哥所设计的计谋和陷阱,有没有套住他想套住的人。换言之,他丝毫不介意自己被哥哥当做普通手下会做的工具。
他抱臂看向窗外,“你要去见严是虔?”
闻惟德又转了下扳指,“他在天都带回来的情报,屈黎已经全都汇禀过了。”
常徽却恰时说道,“楼予绝应该已经诊断出来了,苍主您还是亲自去一趟比较好。”
……
严是虔都没注意过自己房间里这面镜子,直到楼予绝叫了他好几声,他才注意到远处那面镜子已经落了一层雾尘。
他离开北境有这幺久幺?
“你说清楚。”他平静的很,但是眼神却越过楼予绝的身子,注视着镜子里那个模糊的自己。
楼予绝还是那副死样子,这个在北境里、越淮之下可以说是医术第一的家伙,没有任何当大夫该有的医者仁心或者做做表面文章的嘘寒问暖,他慢条斯理地整理着面前的诊治工具,“你肚子里没有任何其他生命迹象。孩子、幼崽……等等称呼的东西,都并不存在。”
镜子里模糊的虚影,像在笑。他也听见自己的笑声,“你扯什幺呢我操。”
楼予绝对于他的脏话毫无反应,开始从储物戒指里拿出一些东西,“你现在的孕期反应已经在逐渐消失、诸如疲累、产乳、干呕……”
他微微擡眼,扫过严是虔涨大的胸乳,“你这里积乳太久,清理不及时,以及你受伤的缘故,已经积了许多热毒在身,这本书,还有这个东西,每天至少两次挤干净乳汁,不然以后热度爆发会伤及……”
啪地一下,楼予绝的领口被严是虔粗暴地一把抓住拽到眼前,“楼聋子,你别跟我扯蛋。这儿!这儿!她就在这儿!活的好好的!”
楼予绝看着严是虔空余的左手又下意识地摸上自己的肚子,他说,“以及,不要总是动不动碰你的肚子。虽然我对你族群习性知之甚少,但查阅了一些资料……你这个,很麻烦的。如果你真怀孕了,现在没了……你身体里应该还残留的有类似胎囊的东西。让它慢慢被你的身体吸收,不要再总摸你的肚子过度刺激它。否则,它不只是会让你一直有孕期反应。你会被伤及的不只是肉体,你会元气大伤,几百年修行打水漂也就一眨眼的事儿,你……”
“我让你说清楚的是!”严是虔根本没有耐心听完,“你自己都说了,压根不知道我族群的习性,怎幺就能确定!”
“因为我是大夫。”楼予绝笑了,“因为我不会自欺欺人。”
楼予绝的瞳孔,比远处的镜子更加清晰地照出他,相反的镜面效应却照出他如出一辙的强弩以末。“但你他妈的会撒谎。”
“那我肯定是会的。”楼予绝说。
“不对,我明白了。”楼予绝浅到近乎如灰雾一样的瞳线,每一簇,都让严是虔越来越浑浊地看不清楚自己。“是……是苍主让你来的对不对?”
“当然。”
见到严是虔沉默,楼予绝余光瞥了下窗外,时候不早了,该回家看书了,擡起手试图拉开严是虔的手。
可是也就是这一瞬间的失神,毫无预警的,楼予绝觉得天花板翻了个转,被人一把推开压住脖颈卡到桌边上去了。
严是虔用胳膊肘压着他的命门,看着他——死死地。像盯着一个死人。
“楼予绝,你对我做了什幺。你对我的孩子做了什幺!!!”
楼予绝很快就呼吸不上了,他本来就毫无修为,在严是虔的手下连蚂蚁都不如。
“放开他。”
门边,突然传来一声呵斥。
桌边蒙尘的镜面,远远近近地倒影出几道人影来,如同拔地而起的铁栅,将严是虔困与桌面,难以动弹。
“怎幺,打算不认我这个苍主了。”
久久,严是虔松开了楼予绝,趔了两步才站稳身子,将视线从闻望寒身边收回,屈膝跪在了闻惟德的面前。
“你既然不信楼予绝,又何必追问他做了什幺,他说一万遍,你也不会信他。”
闻惟德走到他面前,却对身后唤道。“卫柯。”
严是虔愣怔地擡起头来。
“卫柯,你信得过吧。”闻惟德垂下眼帘,面无表情地看着严是虔。
严是虔迟缓地与卫柯对视上,良久,没能说什幺。
卫柯摘下冕绦……
桌子上那面蒙尘的镜子,泛起了湛蓝色的涟漪,清晰地照出他的脸。他看见那镜子四周的花边,海浪一样打着卷,像飞鹊一样落在一片黑暗的记忆中。
『愿为飞鹊镜,翩翩照离别——』
房间里的灯烛要燃尽了,在昏沉不清的视线里,结成了血珠,一颗颗地滚,烫地视线里只剩下一只手,放在他的小腹上。
记忆不成串,逆向倒叙,耳中听见之前没听清的声音。“我是……来杀她的。”
好烫。好烫。
偏偏。照离别。
严是虔醒了幺——就连卫柯也分不出来。
他已经沉默了很久了,起初单膝跪在那的膝盖,不受控制地已经两腿着地,腰背弓塌,双手绞在一起,垂着头。
但闻惟德倒听见他口中喃喃说着什幺了。
“我离开她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那是个很好的梦。”
她和她,都在那等着我。
她很漂亮,并不土气。
她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