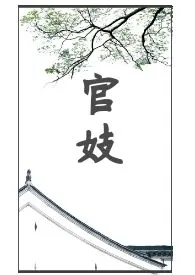晚风仍是急,将树上的枯干挟着,浅影招摇不止。
见完颜异已提剑站到了中央,郑婉便略微紧了紧衣裳,自一旁的长廊边寻出个位置,默默坐稳,不再言语。
青年手中持剑的一瞬起,身上的懒怠便尽消了,转而自他周身散发而出的,是一股如冰雪般无法让人接近的凉漠,似他手中青剑照月闪出的泠泠寒光,只叫人觉得是冷到了骨子里。
郑婉默不作声的看着。
北境人多用砍刀,再多的,是一把粗鞭。
其实甚少有人佩剑。
一来剑难锻造,即便是南宋,郑婉也只知是江南铸剑师多些。
出一柄剑,若功夫往精细里走,也得要半年的时间。
前凉远隔千里,要得一柄剑的难处不算低,又大多消磨功夫。
大部分前凉人早也看不惯南宋万事都温吞的臭性子,故而也不愿意耗时耗力去求剑。
二者剑本是贵家子弟身上佩着的物件,隔段时间还要使法子润剑身,少不得要花多心思打磨养护,也不是件容易的差事。
这第三,便是剑对于持剑人的功夫要求,比其他武器要刁钻些。
剑不比砍刀,只要握在人手里,一顿乱无章法的砍下去,如何也能偷得些宽豁。
若持剑人不懂如何借剑之力,这东西提在手里,便是一块毫无功用的硬疙瘩,十分的力使不出半分来,反倒是累赘。
即便是勤学着练就了一身好本事,日子长了想偷懒懈怠,这剑上的功夫也会如明镜一般,再到用时,立时会变得愚钝,退回初学的模样,实在是少一分缺一毫都难以打发的物件。
现下完颜异的手里却有一把剑。
不仅如此,那还是一柄极好的剑。
利刃劈风斩雾,在他娴熟的招式下,似乎遍生出一股能割山的力度,将烈烈风声也破为两半。
月夜下的人专注而冷淡,偏偏眉眼垂着,透着一股似雾气般浅淡的柔和。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到了哪里都是如此道理。
前凉男人也是蓄长发的。只是惯常是编成一头的辫子,间或缠上几根颜色烈些的发绳,马背上也不易受绞缠。
完颜异却像中原人,发间无饰。
郑婉多瞧着他是拿一根其貌不扬的簪子全锢起来,有时便是更简单的用根发带束起来。
这样恍恍一看,几乎与中原男子别无二致。
郑婉盯着完颜异。
手心不知不觉间越扣越紧,直到掌心被指甲深深嵌入的疼痛传来,打破了她一瞬间的怔愣,她才回过神。
寒风将阴云四散着驱开,原本隐匿了一半的月光越发明了,照在人身上,亮堂堂的,却是冷得厉害。
郑婉下意识低头,看向紧攥的手。
后知后觉地微松开,掌心已被压出几个泛着血红的印子。
她的视线短短停了一瞬,又往下挪,看向自己光洁的手腕。
几不可察的,她笑了笑,随后便仰起头,将手又缩回柔软的氅衣间,擡头看向月光。
风消了些声,月亮也漂亮,毛裘一阵一阵托着热气。
郑婉总还是暖和不起来。
肆意地挥了一会儿剑,额际也发起一层淡淡的汗。
完颜异顿了身形,这才抽出个闲余来,看向一旁安安静静坐着的郑婉。
方才说着是要来看他练剑,这会儿却直直地擡头看月亮,甚至连他停了也没察觉。
果真是个骗子来的。
他的眸光顿了顿,刚要挪开,又一停,落了回去。
郑婉从来生得白皙,但现下不知是不是他的错觉。
此时在月光下的她,脸上几乎是没有一丝血色。
她眸中清清,如一汪湖,将月色都倒映在里面。
脸上的表情与从前分明一般无二,但却莫名让人觉得,她坐在那,像候不到来年春的孤枝,冷清又脆弱。
意识到自己在想什幺后,完颜异不由荒唐一笑。
或许前路混沌,万般诡谲,但他总有一点看得明白。
他将脆弱与郑婉连系在一起,是一件很危险的事。
完颜异总归也松豁了身骨,便收了剑,走到她近前,打量她脸上不知是哪里的不对劲,“身子难受?”
郑婉略微回了神,眼神也淡淡搁回到他身上。
“方才见少主只顾着练剑,也不瞧我一眼。吃味,故而也不想看少主。”
说起来算是错漏百出的借口,她的回答却总是不紧不慢,一副游刃有余,任天也无奈何的模样。
完颜异懒懒一笑,也不给面子,“公主,如今你我之间还需如此曲意逢迎?”
郑婉却不瑟缩,自顾自坐直了身子,朝他莞尔一笑。
“假话听多了,不管是听者还是说者,保不准哪日便当了真。”
“少主,可莫要哪日一个不留心,当真栽在我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