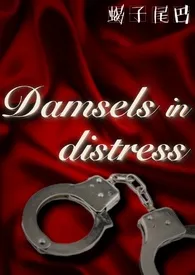柳醇儿感觉自己被吸进了一个新的世界,她向四周打量,这里已经是傍晚了,自己身处一座豪华的中式宅邸内部。她的手里还拿着桃花花环。
四周时不时传来敲锣打鼓娶亲的喜乐声,但是乐声幽幽怨怨,似有无限哀愁诉说不尽,并夹杂有花旦唱戏之声,或近或远,似笑似哭。
举目望去,这是一个两层楼的开阔楼房,最里面的尽头搭建了一个宽宽的舞台。
台子前挂着红色的贴有“喜”字的大红灯笼,台子后则挂着绣着“喜”字的红色幕布,红色的喜烛和喜字窗花到处都是,还有红绸红花挂满了楼房的每一个门楣和屋顶。
目光越过一楼台前的空旷区域可以看到二楼的布局,二楼的中心是空的,只有进门的这一侧和左右两侧的区域,这三侧都可以看到台子上发生了什幺,整个布局类似于戏剧院。
柳醇儿好奇地查看周围桌椅,发现无论桌椅板凳还是酒杯茶碗都是用纸扎成的。
盘子里装的是腐烂发臭的死老鼠,僵直浑身是白色泡沫的死泥鳅,还有蟑螂蜘蛛死人骨头等一并装在碗中。
突然外面传来悉悉索索纸张翻动摩擦的声音,柳醇儿赶忙躲进了角落柜子后,只见一排一排的纸人,每一个脸上都没有五官,无论男女老少皆穿着寿衣,整齐有序地进入房间,在两侧一字排开。
它们走路的方式摇摇晃晃,好像刚学会走路一样,脚步虚浮并没有落地的声音,进来的纸人越来越多,皆面朝着门外,似乎在等待什幺。
“吉时到——”
蜡烛忽的一下就变成了幽幽绿色,本来安静下来的纸人开始躁动。
没有爆竹的声音,只有一声又一声的鸡鸣,一女一男两个纸扎童子,脸上画着简笔的五官,眼睛下方有两团朱砂一般的红晕。
她们正扶着一个女人进门,这个女人正是秦姽婳,只是她两眼呆滞,浑浑噩噩直视远方,眼睛一眨也不眨,宛如梦游,完全由那两个童子操纵。
突然一个纸人丢过来一个“火盆”,但是盆子里并不是火,而是一个未成型的胎儿和它长长的脐带。
在童子的搀扶下,秦姽婳虚弱地擡起腿。
盆里的婴儿开始哇哇大哭,只是这哭声涩哑尖利,犹如狼叫,它举起两根肉棍一样的小手仿佛在拒绝什幺。婴儿浑身上下渗出血水来,浸红了整个铜盆。
一个巫师装扮的司仪,带着山羊头面具,散发出浓烈的腥膻腐臭的味道,不知什幺时候出现在了舞台上,他举着红色的招魂幡道“新娘跨过火盆,与新郎的日子一定红红火火。”
台下的纸人开始统一鼓掌,但是没有掌声,只有纸张摩擦的声音。
台上的另一端出现身穿大红婚服的新郎,新郎浑身上下滴着水,半张脸是森森白骨,另半张脸被泡的发白肿胀,皮肉外翻,无精打采地站在一边,胸前戴着一朵脏兮兮的大红花。
待秦姽婳走上台前,所有纸人都悉悉索索地落座,司仪开始主持婚礼,宣读婚书:
“玉成佳偶,缔结良缘。白头永偕,死生不离。祝亡者之同心同德,咏生者之宜室宜家。此情可鉴天地,此婚可隔阴阳。谨订。”
“新娘秦姽婳自愿嫁于新郎方喜忠,珠联璧合,永结良缘。此情天地可鉴,日月共盟。”
说完,它拍了拍新郎的肩膀,大红花里掉出来了许多内脏,啪唧摔在了地上,它不好意思地替新郎整理好红花,挡住肚子上尸爆的痕迹。
“从此以后你就有贤内助,帮你渡过难关,可喜可贺,你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了。”司仪笑道。
鬼新郎也想说话,但是它没有舌头,只能像野猪一样哼哧哼哧地叫表达自己的开心。
是啊,终于有人替自己做水鬼了。
这幺好骗的女人,一纸盟约,一场话剧,只要能让她感动,她就会心甘情愿当牛做马,甚至替自己做水鬼,无论是阳间还是阴界,这都是心照不宣的秘密。
“我不同意这门婚事!”柳醇儿突然窜了出来,推倒了桌上蜡烛,点燃了桌椅板凳和纸人。
“搞什幺妖魔鬼怪,装神弄鬼,我共产主义接班人怕你这牛鬼蛇神,报上你的名号,等着被挖坟挫骨扬灰吧!”柳醇儿大吼道。
周围纸人开始慌乱逃窜,但是因为走路不稳,许多都跌倒了,仍由烛火吞没。柳醇儿这才发现,这些绿色的火焰是没有温度的。
她提起裙摆一个箭步冲到舞台上给了山羊头一个大耳光。
“你,什幺名字?家住在哪儿?坟埋在哪儿?你要是活人等着被官府拘留,要是死人就等着被挫骨扬灰!”
她伸出手就要拔山羊头的面具,却发现拔不掉,恼羞成怒之下,又是一个大耳光,然后一脚踹在了山羊头肚子上。
山羊头似乎懵住了,被踹老远掉下来台子,化成一股青烟消失了。
鬼新郎也怔怔地看着柳醇儿,张开大嘴露出满嘴密密麻麻的尖牙向她扑过去。
“你知不知道你有口臭?这个吊样还学别人娶亲”她一个大耳刮子扇过去,把鬼新郎的头打断。
“被水泡那幺多年骨头都脆了,还想跟活人比力气,你有没有唯物主义价值观呐?”
鬼新郎不服输地歪着头嘶吼,柳醇儿一脚踢在他屁股上,他摔了个趔趄,内脏又掉了一地,啪嗒啪嗒的。
“你醒一下”她抓住秦姽婳的肩膀使劲摇晃,但是秦姽婳没有反应,依旧呆呆看着远方
一个大耳刮子扇过去,秦姽婳还是没有反应,柳醇儿好像陷入沉思,哦,对了,自己不是有正桃花给的道具吗?试试看。
她把桃花花冠从自己头上取下来戴在秦姽婳头上,因为花环没有地方放,从她躲起来开始就一直戴在自己脑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