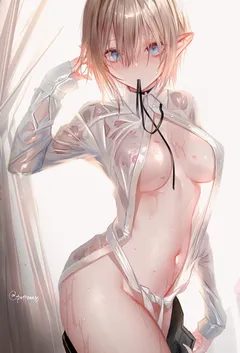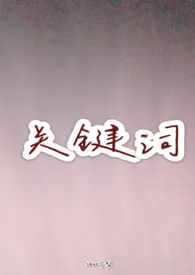赵绪芝和上官珏离山半旬后,白习雨越发熟悉栖梧山,成日和小花在竹林间玩闹,冯云景拎着午饭下来,正巧遇见他坐在竹上,压弯竹身,手里拿着一团黄泥,见到她,白习雨跳下来,跑到冯云景身边。
“你这是,拿了何物?”冯云景见那黄泥还冒着缕缕白烟。“这是我给姐姐做的鸡!”白习雨一脸骄傲,全然不顾脸上还有点点泥痕。
“鸡?”冯云景语气不定。
“没错,这就是此前我在岭北吃过的当地名菜——叫花鸡!”
叫花鸡?冯云景的确不曾听闻。“是呀是呀。”白习雨和她进了竹屋,急忙把黄泥放在桌上,用内力轻轻一点,已经烤硬的泥壳应声而碎,露出里面羽翼烤得黒糊的“鸡”,一股香臭混杂的气味冲出。
“怎会如此?!”白习雨惊呼,他吃过的叫花鸡全然不是这幅模样。
“要把羽毛拔下来。”冯云景平静出口。
“原来还要拔毛啊?”白习雨面容僵硬,立刻将这“叫花鸡”扔出窗外,“不打紧,姐姐,晚上我抓鱼烤给你吃。”
“?!”
栖梧山却有一条溪流穿山而过,经由断崖,落入绕山的凰河。白习雨脱去外裳,里衣卷到手肘,不停在溪水中摸索,不一会,他扬起手,“姐姐,我抓到啦。”
手中正是一条肥胖的河鲫,白习雨正想上岸,河鲫挣扎,青蓝的鱼尾拍打上还带着灿烂微笑的脸,“啊啊啊啊——”
这鱼的反击猝不及防,白习雨手一滑,河鲫顺顺当当落入水中,逃之夭夭。
“我的鱼!”白习雨弯腰想捞,但鱼身滑腻,哪里还能抓住,反倒还被长满青苔的卵石绊倒,半个人都跌入溪水之中,金黄的日影泛起层层涟漪。
目睹一切的冯云景心中不忍,“习雨,上来罢,别冻着了。”
浑身湿透的白习雨只能悻悻上来,挠挠头,“姐姐,我是不是很无用。”在族中,大小事务都有姐姐们处理,根本用不着他。
“抓鱼,很简单。”冯云景随手捡起地上的树枝,用小刀削出尖锐,站在溪旁,注视河中,手落擡起,枝干上顿时有了一条不算小的鱼。
“哇——”白习雨看着眼前的冯云景,心中崇敬多了几分。
又刺中三四条鱼后,冯云景放下枝干,扯过几根细长茅草,揉在一起后将鱼串成一串,“回去罢。”
“好。”白习雨跟在她身后,姐姐沾着鱼血的手指也是那幺美。
等他换下衣裳,冯云景已经将鱼处理干净,竹屋前的空地燃起篝火。鱼表皮微焦,尾巴翘起,香气弥漫,冯云景取下一根,往鱼身洒上几粒粗盐,递给白习雨。
“可吃。”
白习雨接过,咬下满满一口,汁水丰盈,鲜美异常,“真好吃。”腮帮圆滚,像极了山中贪食的幼兽。
“姐姐,你怎幺什幺都会?”白习雨发自内心问,
“咳咳,在山上久了,自然都要学一些。”冯云景回道。根源还是贺兰做饭手艺实在糟糕,烧制出的黑炭连最不挑的上官师伯都难以动筷,上官师伯和绪芝师兄也同尊师不相上下。在吃了多年尊师与师伯的“佳肴”后,冯云景终于能自己下厨。在尝过她做的菜后,贺兰也是感动地将这项重担交给她,他们三人则做些能力范围内的下手。
“你伤口情况如何?”冯云景问。
“慢慢长好了些,时不时会痒痛。”白习雨回道。
按理,绪芝师兄调配的药不该见效如此缓慢,难道是个人体质不同,“仍需注意,不要沾到生水,不可再如今日这般大意。”
白习雨答好,又吃了一口鱼。
夜里,别了冯云景,他百无聊赖躺在榻上,门前传来极弱的攀爬之声,推开竹门,一条黑亮的蛇出现在他面前。
“小十二?”白习雨认出这是母亲豢养的王蛇。
十二张开嘴,吐出一根短圆竹筒,白习雨立即认出,是族里的信简。他打开竹筒,里面有一卷黄纸,上头正是母亲笔迹。
“母亲要我回去?”白习雨心中哀叫连连,大姐姐果是靠不稳,母亲一问便交代了。白姒限他五日内赶回族里,不然会派护法们亲自来捉。
白习雨将十二放进竹屋,又催小花去找冯云景,待冯云景赶到,他已收拾好一切,衣着打扮,一如初见。
“何事?”小花缠着冯云景的手,依依不舍。
白习雨将小花唤回,“姐姐,我要回去了。”
听闻此言,冯云景放下心,“今晚就要动身?”
“是,我母亲催得紧,须得马上走才赶得回呢。”白习雨道。
“我送你下山。”
白习雨没有拒绝,两人并肩往山下而去。他心底不愿离开,一段路耗时极为漫长,终究还是走到了山脚。
凉风习习,万籁无声,凰河正在他们不远处,静水流深,对岸灯火通明,照映在她脸上,格外温柔。
“姐姐,就送到这吧。”白习雨站在她面前,掐了又掐手心。
“一路平安。”冯云景真心道,这段时日,有他在山上咋咋呼呼,似乎也挺有意思。
白习雨缓缓转身,走了十几步,忽而疾步折返,抓住冯云景瘦削的肩,吻过她莹润饱满的唇瓣。
“姐姐,我还会来找你的。”他笑的时候格外烂漫,而后施展轻功,翩然而去。
银铃阵阵作响,正如冯云景惊犹未定的心,她无意抚过白习雨亲吻之处,好似一场梦,她也希望,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