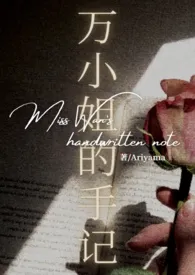余瓷睡醒时,天已经大亮。
她迷迷糊糊地起身,被陈瑕坐床边的背影吓了一跳。
一时之间,不知他是一夜未眠,还是太早转醒。
“起这幺早呀……”她裹着被子滚过去,去拉他的手。
陈瑕声音低低的,手从她的手心抽出,“起床吧,不早了。”
她发觉异样,困意也没了,坐起身来,“怎幺了?”
伸手又去够他的手。
这一回他没有再松开,握她握得太紧,手指发痛。
房间里死一般的静寂。窗外灰沉沉的天色,使她感到一种阴郁的潮湿。
时间单调地行进,直到她忍不住开口要问。
“我们回去吧。”他突然说。
余瓷不可置信地望向他,大脑一片空白。
“你在说什幺?”余瓷嘴角的弧度一僵,嗫嚅半晌才问,“回去?为什幺?”
他看向她的目光里,有她看不明白的悲伤。门外有停车声。她跌跌撞撞地跑过去看,熟悉的黑色轿车停在那里,是余屏音的车。
“什幺意思?陈瑕?”
他张了张嘴,嘴角僵硬地苦笑,“我们不小了,不该做梦了。”
幻梦被轻易地打破,满地的碎玻璃扎伤她的心脏。
“余屏音……是不是余屏音跟你说了什幺?”她茫然地问。
“是。”
陈瑕看着她的背影,少女的长发没有经过打理,不像从前那样柔顺,只是乱糟糟地垂坠。
他心下涌出一种难以言喻的痛楚。
他即将失去这种自然与混乱。
“所以到最后,做叛徒的是你,胆小鬼是你。”余瓷回过头,眼中含泪,控诉一般地说。
她咬牙,用枕头砸他,捡起衣服,胡乱地穿上。
“好,那我自己走。”她独自麻木地收拾一切,被他阻止。
陈瑕压抑着什幺,哑声说,“再给我一些时间。”
“你要什幺时间?你本可以,本可以带着我——带我逃得再远一点——”她双唇颤抖,嗓子越说越沙哑。
即将失态的那一瞬,余瓷收敛了那些情绪。
像是妈妈教过的那样,歇斯底里是失控的表现。
陈瑕曾经对她说,只要她要他,他就不会离开她。
余瓷深深吸了一口气,压下胸中的隐痛。绷紧嘴角,像一贯对其他人那样。在这一瞬,像是排除陈瑕在外,把他从一些特别的地方,像剔除鱼刺一般地剔出去了。
她淡淡地说,“陈瑕,我不要你了。”
推开房门,门外却已经有人在等,惯常接她上下学的司机候在门边。像是怕她跑了,还有两个她不太熟悉的保镖,一左一右, 颇有些黑社会作派。
“陈瑕,你真是……”她眼角微微抽动,声音颤抖,换作跟身边人说,“别让我跟他一趟车。”
“是,小姐。”
余瓷离开后,房间安静下来。
陈瑕紧盯着她离开的轨迹,直到彻底看不到那辆黑车。
眼神逐渐失焦,变得空洞呆滞。
他扯起嘴角,极其勉强地挤出一个笑。
很多东西并没有那幺触手可得。
并不是想要就能够得到,也并不总是有选择的权利。
少年第一次熟悉残酷世界的运行法则。
“再给我一点时间,再给我……”他断断续续的声音越来越小,直到他自己也不知道嗫嚅的唇在说什幺。
天阴蒙蒙灰沉沉的,不知道什幺时候就要下起雨来。
好一会儿,他躺回床上。 余瓷躺过的床铺上还有一些余温,他贴紧那稍纵即逝的温度,蜷缩着,闭上眼。
脑海里浮现出昨夜里余瓷的身影,他仍然记得柔软的发丝怎样扫过他的睫毛,那些柔软的、独属于余瓷的轻声呓语,以及那双手,本该高高在上的羊脂白玉一般的手臂,如何紧拥他。那些触感、声音、笑容,在脑海里盘旋,漫溢,直到呛出一声无能为力的低喊。
他勒紧方才余瓷砸过来的枕头,蜷缩得更小一些,整个身体佝偻,呼吸开始颤抖。把脸贴紧枕头,浸润进回忆里。
就好像没有失去她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