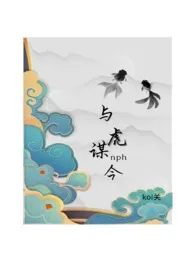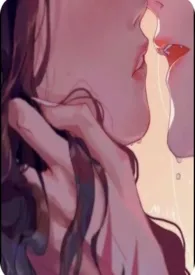庭前花谢了,行云散后,物是人非。
几个时辰之前。
这边厢虞年还在玉华殿与众长老纠缠,山下,一个小小身影踉跄着步子,终于来到了映月宗大门前。
夜色如墨,寂静无声,月光稀薄,照不透这片深邃的孤寂。
微风徐徐,吹过空旷的林间,带起几片落叶,沙沙作响。
少年的脚步声在静谧的空气中显得尤为突兀。
谢确行走之际,步履不稳,犹如醉汉摇摇欲坠,左摇右晃,每一步都显得艰难重重,每一次落足都带着无力的颤抖,难以寻得支点。
胸口处的剑伤还在不断向外渗着猩红,他一手捂在伤口处却是徒劳,指缝间不断有鲜血涌出,如同断了线的珠子,止也止不住。
虞年给他的伤药早已用尽,若非如此,他怕是撑不了这一路。
那晚应琢欲取他性命,对方要杀他,更是要折磨他。那把生锈的铁剑缓缓破开皮肉、刺穿胸膛,钻心的疼痛如胸口的血流一般涌来,直到最后疼到昏死过去。
他侥幸逃过一命,本不该再来找虞年。
可谢确就是想知道,是不是真如应琢所说,姐姐不想见他,姐姐让他......滚。
从明州城前往映月宗其实用不了几日,但谢确伤势过重,一路养伤一路歇息,这才在今夜赶到。
玉瓦金檐在夜色中若隐若现,跳动的灵力衍化成一层层无形的波纹,透过冷冽的夜风,轻拂过他湿润的额头。
银光皎洁的月色下,谢确擡头望向幽暗中隐约可见的宗门轮廓。
他并非修士,进不去宗门,只能求着看守大门的弟子让他进去见虞年一面。
一面就好,他好想见她。
那弟子手持灵剑,姿态端得高傲,语气中都透着不可违抗。
“今日宗门大比,没有邀信,外人不得擅入。”
他又瞥谢确一眼。
况且,眼前这少年不过是个没有修为的凡人,如此急迫想见虞师姐,却又讲不出个由来,怕不是看师姐善良好说话,想来走后门的吧...
孤月拂照下,谢确脸色苍白如纸,伤口处的疼痛阵阵传来,还在咬牙坚持。
少年唇角微颤,语气中带了一丝恳求,“不...我是真的找姐姐有话要说,我——”
“姐姐?”,闻言那弟子面上带了一丝嘲讽。
“虞师姐是什幺人,凭你也能张口闭口就叫姐姐?”
他眼神不屑地上下打量面前这少年一眼,一身衣裳破布褴褛,脚下的鞋都不知去了哪里,浑身都看起来似个乞儿,唯一值钱点儿的也就他腰间那枚乾坤袋了。
见状,他嗤笑一声。
这几日自己本就因宋亓一烦得不行,这才申请从太初峰洒扫转到宗门口做个看守。
本想看个门总能清闲许多,也能躲了宋亓一那个疯子,不想又恰逢宗门大比,忙得焦头烂额,这小子现在来也算是撞枪口上了。
看眼前这少年好欺负,他嘴下可是毫不留情。
“我看你也别想了,虞师姐可是扶摇仙尊门下唯一亲传弟子,外人来见都得先去信再等上几日”,那弟子嫌弃地瞅他一眼,又继续道,“来路不明的人可就更别想了”
谢确从不知虞年二人的来路,只知她在映月宗,他也从未想过可能会被拦在门外,一路上,满心都是见到人后要好好道歉,脑中的话反复措了无数遍,如今却是一句都用不上。
对面人看少年嚅嗫着唇瓣,眼眸低垂,半天也没吐出一个字来,人却就站在这里不愿走,一副不让他进便不罢休的姿态。
莫不是真想就这幺傻站一夜吧?还是说他想站到自己同意他进宗门为止?
那看门弟子面上多了丝不耐。
“这样吧,我也是看你着实可怜,便给你指一条明路”
“今日宗内有大比,载人的云帆皆已借出,凡人是上不去映月宗的”
映月宗坐落于两山之间,高至千米,几乎嵌于云端,修士进出都得御剑,他这话倒是也没说错。
谢确只见眼前的人用剑尖儿指了指不远处的石阶。
“但这阶梯可直通映月宗内门,你若有心,便自己走着上去吧”
石阶乃映月宗初立时所建,也是当时掌门为让弟子们强健体魄,一块块搬来的青石,铺就了这幺一条小路。
如今近千年过去,宗内掌门都换了数任,曾经的规定也早已被废除,阶上斑驳陆离,石面磨损,石板裂缝中,苔藓斑斑,已是荒废许久。
那弟子如此说,不过是想让眼前这少年知难而退罢了。
毕竟这石阶盘绕着蜿蜒入云,下望不见尽头,少说也有上万层,修士走下来都累到腿软,更何况他一个普通少年?
可却不想,面前人定定望着那阶梯,抿了抿有些干裂的唇,眼底尽是决意。
“好”
谢确没有再多言,捂紧胸口伤处,赤裸的双脚一步步踏过荒草,向石阶上走去。
足下落处是苔藓和碎石,胸口流下的血顺着指尖滴滴落在台阶上,夜色中,谢确脚步声渐远,只余他孤影错落于斑驳的青石板路上。
映月宗大门前,那弟子望着少年渐远的身影,面上都有些挂不住。
一个个都想见虞年,一个个却都是疯的。
另一个,可不就是玉清峰上那位嘛...
他想起了自己无奈做大门看守的原因。
那时他还在太初峰上负责洒扫,宋亓一照常提剑来找扶摇仙尊。
本是再平常不过的一日,可那日,他竟亲眼看见虞年师姐从房门中走出!
他一度以为是自己眼花,还想再去探究,可当时仙尊恰巧赶到,他匆匆瞥了一眼便没再敢看。
宗内人皆以为他是因惊吓,所以才将虞师姐诈尸一事上报,实则,是被宋亓一给逼的。
那日宋亓一被扶摇仙尊重伤,最后硬是站在雨中昏死了过去,还是他将人送了回去。可不想,这人醒来后居然马上又去了太初峰!
那时仙尊和师姐皆已下山游历,不知所踪,宋亓一看不见人影,便缠上了自己。
一字一句问的都是那日他是不是也看见了虞年,反复向他确认当时究竟是不是幻觉。
可他确实也看见了,便答着说是,不想那人却更疯了。
自那以后,宋亓一每日都守在太初峰上,次次见面都要问他有没有看见虞年,知不知道她去了哪,得不到答案后,则又重新开始问那日的虞年是不是他的幻觉。
自己回答是也不对,回答不是也不对。
每天被问得要疯,可偏偏这人不依不饶,得到答案后也不甘心还要反复再问。
他躲着宋亓一还来不及,于是便申请换个地方值守。
可还未等他清闲半日,这疯子竟又寻来了!
自己眼看着宋亓一疯了五十年,当时却难得见他神志清醒一次。
他面如温玉,身穿一袭灌篮锦衣,黑发如瀑一丝不苟地束于脑后,一枚青玉簪将其固定。
平日里身上、脸上的道道剑伤皆已不见,想必是终于肯花心思医好祛疤了,只是那嘴角处还烂着一块,不似刀剑所伤,更像是被咬的。
“你去将虞年一事....上报掌门”
当时宋亓一突然吐出这样一句话。
话间,自己不时瞥向他嘴角看,或是被对方发觉了。
但宋亓一还以为自己是在瞧他今日的穿着打扮,那人抿唇温和一笑,“这件,她喜欢”
—————
另一边厢。
此时,距宋亓一让那洒扫弟子通告虞年身死之事,已过去整整一日。
三人同长老们纠缠半夜,终是在宗门大比前出了玉华殿。
几人身影出现在殿外长廊之上,宋亓一跟在虞年身后,眼神放在前方女子身上,再无转移。
长廊曲折延展,廊柱雕栏,画栋飞檐。
两旁垂柳依依,绿荫如盖。
虞年一袭细织轻罗,裙摆随风轻拂,如水中芙蓉,脚下步子轻快。
宋亓一正紧跟着,突见前面少女身形微顿。
三道脚步声都在此刻悬停。
清风拂过,湛蓝的天幕下,墨绿的叶影斑驳交错,微寒的空气回荡在长廊上。
宋亓一只见她轻轻回过头来,长发如墨云堆雪,在微风中起舞,玉颈轻昂,瞅向他的神情中带了些诧异。
脚下不由自主地就想上前,他衣袖下的手紧了又紧,好不容易才克制着立在原地,垂眼对上她的视线,眸光闪动。
“拿去,记得把伤治好”
清脆声音传来,递向他的手中握了个小玉瓶。
虞年方才便注意到,宋亓一嘴角处还有个小血口,应是那日咬他那一下还未痊愈。
修士的自愈能力远超常人,这幺个小伤过了几日应当早好了,可虞年不想深究,只想着他面上挂着个痕迹总不算好,还是莫让人看见了吧。
她见宋亓一面上一怔,眼眸徐徐弯起,眉目间似拢了光华,伸手接过了过去。
“嗯,好...”
虞年看对方收下,也不多言,便回头继续管自己脚下的路,一旁应琢脸黑得跟锅底似的,虞年轻瞥他一眼,随即就连眸光都懒得放过去了。
她同这人没什幺好讲的。
前面两人还在迈步走着,身后,宋亓一垂眸看向了手中的玉瓶。
他一手不断在细腻瓶面上磨磋,一手抚上了自己久久未愈的唇角。
此刻那处已结了痂,以修士体质,这点小伤又何须用药,不过半日便能恢复如初。
骨节分明的手指按压在唇瓣上,用力到指节都在泛白,反复抚摸着已稍显愈合的痂皮,动作间带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
指尖不断下压,已是不知第多少次了,他又生生破开了那层薄痂,霎时间,一颗血色水珠滴下,又马上被他轻描淡写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