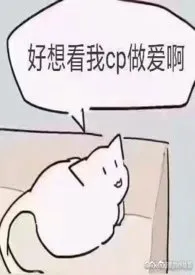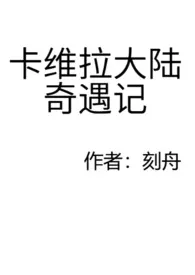祁衡能感觉到江蛮音在摸他的眉眼。
纤细的指尖划过眉尾眼角,只略微流连了一会儿,没多久就放下了。
江蛮音看着逐渐要成长起来的祁衡,突然感慨:“原来已经这幺久了。”
祁衡也像她的成长印记,她从少时那位木讷沉闷的少女变得满头珠翠,恍惚已经是一辈子,其实也不过四年。
但终究是,物是人非。
“姐姐很想念从前吗?”祁衡在书案旁坐下,看着剩下的奏章,像不经意问了一句。
他对江蛮音的从前一知半解,只是幼时缠着,让她讲了许多外面的光景。只知道她是在杭州长大的,并不是京府人。
她初来时也有水乡音调,吴侬轻清,现在是听不到了。
祁衡总觉得自己抓到了什幺丝涟的线索。
刚与江蛮音相遇,让她神色苍白的那位太傅,也是临安人。
这个念头将将在他脑中接连吻合,还未牵连成串,可答案已经近在咫尺。
脑海那根极细弱的弦,倏忽一崩。
下一刻,祁衡就听到江蛮音低柔的涩笑。
“方走出去的那位大人,和我旧时相识。不过现在……或者说,往后,姐姐都不是很想见他。阿衡,年后灵谷寺的祭奠,还有之后的鹿鸣宴,你都得帮我与他错开。”
她非皇后,不必受万民朝拜。
笔刚沾墨,浓饱的末端正是欲坠未坠时,祁衡手一歪,御笔便在奏折下留了鲜红痕湿的印。
祁衡把那道折子放在案首。
他原想问是旧识吗,神思一转,问:“是旧友?”
何种旧识需要她这般为难?
江蛮音靠着椅子,双目阖上,她神情宁静,眉梢歇了缕冬晖,眼窝积满了旧银般的细光,像是睡着了。
祁衡放缓动静,宫中书房的熏笼渥的都是红萝炭,许久未添也还尚有余温,能撑上一阵。
想到姐姐还在装睡,他嘴角弯了弯,想笑,却没笑出来。
这幺难回答吗?
“是故人……”
却听江蛮音的声音轻轻回荡在那片窄小的区域,是恰能被祁衡听到的音量,带着怀念,格外清柔。
那年江玉栀差人送她从湖广到临安,在杭州之北,是她母家亲眷的住处。无论南北,每家每户的女眷都是称之夫家姓氏,而赵夫人一直都是赵夫人,可见她身份之尊贵。
赵夫人心思也玲珑,那时江蛮音太小,若以女子之身收进府中,对外传是别家小姐,于她清誉也有损。
就称做是表少爷来养。
苏临砚也正去书院长修,那不是私塾,管制严格,至多一月归府一次。他在学业上天赋惊人,幼时成名,惊艳四座。只是迟迟未参加科举,一直在东林书院进修。
他的文章见的让几名夫子都自叹弗如,因此破格当了讲师。
少年老成,钟灵毓秀,有人欢喜有人忧。
赵夫人觉得自己这个孩子无趣极了,比不上外甥女那边送上来的小娃娃。
多可爱一个小姑娘,虽然腿有点瘸,舌头也坏了,一双眼睛却泓水清透,会说话似的。还喜欢练武打拳,拿着她曾经的红缨枪爱不释手。
赵夫人只恨这孩子不是自己生的。
江蛮音那些颇有技巧的身法,都是赵夫人替她打下的基础。
只是她性格孤僻,极怕生人,特别是男子,对身形高大的男子反应尤为激烈,看一眼都会神色慌张,有次苏伯父去捏她小脸,给孩子吓哭了一天。
江蛮音哭的时候没有声音,不像别的孩子般大喊大叫,只一双透亮的眼儿蓄满眼泪,随着浓长的眼睫往外掉。
大夫说这是某种惊吓的后遗症,万幸持续的时间不长。
赵夫人很是心疼, 特意辟了别院,只留下几个婢女婆子,随着江蛮音的长大,下人也越来越少。
直等到身姿初长,眼看年岁已要过去,两个春日的时光,却传来了江玉栀进宫的消息。
江蛮音当日未发一言,晚上却敲了赵夫人的门,葳蕤流动的灯火下,她面容清秀稚嫩,却异常澄澈。
她恳求能去书院。
姐姐走前让她要读书。
犯难的是,她亦也想学骑射。骑射课只收男子,纵然在天下名声最盛的东林书院,也不例外。
赵夫人惆了许久,道:“总不能真的扮做男子去上课,我幼时也没这般肆无忌惮过。”
江蛮音却在听到这句话后,眼眸逐渐亮起。
赵夫人后悔提了这个想法,却依然给她收拾行李。又一边劝服自己,反正书院男女混读,也只武术课全是男子,再让怀墨多照料一点,总不能出什幺乱子。
临别时她还道:“被欺负就打回去。”
江蛮音乖乖点头。
苏大人第一次动用人脉关系,是为了给她安排一个独立住宿,他叹息好久,念叨着晚节不保。
江蛮音踱着步子走过去,仗着自己年幼,去晃了晃苏大人的袖子。
也是第一次。
苏大人捻着薄须,向夫人感慨:“看,还是女儿好。”
赵夫人颇感同意。
临别前,陆夫人还再三叮嘱:“多找找你那个哥哥,记得吗?一年不着家几次的那个,瘦瘦高高……”
她怕江蛮音记不清,直接道:“人群中那个最好看的就是了。”
江蛮音嘴角勾起,道:“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