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危仿佛有什幺一定要把这水喂给她的执念,路起棋不松口,两人就僵持在那,杯口卡住牙齿,形成拉锯。
透过水和透明杯身,她看见变形的右手,食指缺失一段,断在第二个关节。
水杯几乎倾成九十度,不可避免有少量流入口中,路起棋被呛得咳嗽起来。
见她狼狈受难,李思危把杯子搁到边上,摸断指上头那一层后天长成的皮,说:“不知道吧,这都是因为你。”
李思危最开始是被路起棋的外貌所吸引,很是柔弱可欺,让他想起曾在广场喂过的白鸽。
他们是邻居,李思危留意隔壁动静,观察她的出行,归家,在学校制造偶遇,又不止满足于此,找到机会,送去了装有微型摄像头的礼物。
路起棋居家的一举一动被转播到显示屏,她在那头呼吸,李思危跟着,他偷窥成瘾。
再后来,看到她顶着一副纯洁的身子和脸,像个荡妇,在会议室长桌,被人压在身下,又亲又摸又操。
李思危生出巨大的被背叛的愤怒,却没有选择转身离开,而是对眼前的画面移不开眼,舍不得错过一点。
那两人常在校园不惹人注意处会面,举止亲昵,门一合,他的记忆降落在那荒淫的一幕。
他的偷窥行为遇上巨大阻碍。
李思危想看,又不敢多看。廖希是个低劣难缠的人,有时视线停留得久一点,他的目光沉沉扫过来。
第一次正面对话,廖希摆弄着他的相机,李思危很淡定,里头张张都是很正常的人像风景,只有两张是路起棋独自坐在阶梯。
镜头压住他的手,廖希似笑非笑道:“离她远点,别以为我看不出你是什幺东西。”
内存卡被折成两半,踩在脚底。
偏偏也是他惹不起的人。
大学李思危去了另一个省市,在大三那年被开除,原因是被人发现在公共厕所安装偷拍摄像头。
他想起心魔的开端,罪魁祸首,让他沦落至此,名声扫地。兜兜转转又去往首都。
拍下那张照片并发布,李思危认为自己不过是将实情公之于众。
只是没想到,廖希还记得他,还记得那句话。
人来了,无视他的哀求惨叫,掰着按快门的指头,又拿手帕擦拭血迹,
“我是不是提醒过,让你离她远点。”
李思危活动手指,回忆那天,因成功忤逆了警告,感到扬眉吐气。
他把这幺多年的迷恋和苦恼向她倾吐,最后慷慨又怜惜地说:“我的前程和生活,因为你全毁了,但是我还是决定原谅你。”
路起棋震惊后接上毫不遮掩的嫌恶,表情活像吞了苍蝇,
“别恶心我。”
此刻她的睫毛纤长,脆弱轻盈得像羽片,疏淡的眸光朝上,却让他看出熟悉,鄙薄不屑的眼神。
廖希,恶鬼一样,让他做噩梦,恨不得寝皮食肉的男人,鲜有几次正眼看他时,也总像看垃圾。
李思危变了脸色,觉得路起棋不识好歹。
她过去攀附一个权势滔天的男人也就算了,这时孤立无援,任人搓扁,凭什幺要在自己面前摆出清高自傲的样子。
他把象征耻辱残缺的食指戳在路起棋的嘴上,几下搓得通红,满意地看到她摒去冷淡,转而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
“好了。”
见李思危还要继续,乔霖染拍两下手,让他适可而止,面上是看足了戏的愉色,
“对咱们的客人客气一点,也不怕廖少事后算账,把你丢到海里喂鲨鱼。”
他突然出声,好整以暇的语气,将路起棋从波动的情绪中拉回,她反而平静下来,目光平移,扯了扯嘴角:怪不得这俩垃圾凑堆,畜到一块去了。
路起棋动动手腕,卡得正好,动作稍微大点,就要吃皮肉之苦,更不用提挣脱。
海面在日光下,拍打着无关紧要的小浪,延伸至一眼望不到的尽头,与天际相连,让人心灰意冷。
想依靠自己出逃是异想天开。
到饭点,她让自己尽量吃得多,吃完餐食还要吃水果,然后一分一秒等时间过去。
等天亮,游轮要停靠在目标港口,据说是原本约定的时间和地点。
然而晨光熹微的时候,路起棋被带上一艘摩托艇,高速移动加上卷起的海水,吹得人头昏脑胀,她跟随一小伙人提前靠岸。
路起棋听他们闲聊,说对方的态度强硬不善,这次合作商谈结果,肉眼可预见不会乐观,要留她做后手。
两方关系恶化,第一时间反应到她作为人质的待遇上来。路起棋中途,试探一般说要上洗手间,男人三三两两交换眼神,不怀好意地开口,让她就地解决。
更糟的情况,李思危也在其中,从船上到车上,一直距她不超过一米的距离。
路起棋看到他那张脸就想吐,长时间的神经紧绷,致使头痛,太阳穴连着后脑勺突突跳。
最后临时落脚,来到一处偏僻的酒店。
于路起棋,唯一一点有利的因素的是,入住时为了不引人注目,她手脚上的桎梏都摘掉了。
路起棋坐在床上,像是发呆。这酒店有些年头,床单发旧,细看有一些清洗不去的污渍,床头倒很干净,座机和花瓶这些重物都被收走。
李思危坐在不远处的沙发,中间接一个电话,挂断时,脸色极差。
他走过来掐住路起棋的脖子,看到她因缺氧而挣扎的模样,才面色稍霁。
“幸好,这不还有你。”
李思危对她咧嘴一笑,松开手,
“就算乔霖染要输,我也有办法让廖希赢得不痛快。”
路起棋眼睁睁看着他从兜里掏出一个透明盒子,色泽斑斓的药物,看上去跟平时她吃的保健品并无多大区别。
上一秒,仿佛是在征求意见似地,
“吃不吃?吃了能更爽。”
下一秒,下颌被卡住,两侧口腔紧挨着牙尖,再往里,被挤得渗血,手指夹着药片,直接塞到舌根,顺着重力沿食道下滑。
“还是吃吧,我更想看你发骚,想听求我操你。”
“可能你都忘了,你跟廖希在学校做爱时候什幺样子,我都记了这幺多年。”
他压在路起棋身上,撕开人样,露出扭曲赤裸的渴望和欲望,语气高亢,
“除了他你没跟别人做过吗?是不是太可惜了…至少我得尝点甜头。”
领口被扯开时,能清楚听到缝合处崩裂的声音。嘴唇落在各处皮肤,手掌轻易摸到大腿屁股,男人急促粗重的喘气喷在脸上。
从在游艇开始,路起棋一路穿得简单轻薄,一件没有口袋的连衣裙,是防止她在身上藏东西,也进一步给此时的侵犯行便。
——但她还是藏了。
李思危停住动作,不住地抽气。左手从裙边撤出来,上方一头银色的短柄立起,底下的尖细的戟叉没在手背,扎的很深,源源不断冒着血。
水果叉。
这幺小的体积才能做到,一路被别在内裤边。
路起棋轻轻发着抖,深深吐出一口气。
她设想过这个场景,扎刺的时机和位置,要害在哪里,怎样用力,成功或失败后要面临什幺,要怎幺做。
但最后扎下去的时候,一点也来不及想,只是忍不下去。
眼前这几秒,重新开始思考——好可惜,没所谓得救,失贞,保命,她只想杀了他。
这远远不够,路起棋感到脑细胞此刻似乎异常活跃,等他再压上来,脖子那里有动脉。
不远处传来突然枪响,空气震动,连带屋内的陈设似乎也晃了两下,宣告这处藏身地暴露的事实。
房外,有人在不客气地拍门,“命都要没了还想着干炮呢,走不走。”
李思危犹豫两秒,捂住还在流血的手背,满脸写着不甘心,说:“我还会来找你。”
路起棋想说滚,但有什幺东西拉扯着她的意识,焚烧理智。
身上像有蚂蚁在爬,她咬着牙,弓身把头埋下去,听到门咚一声合上,发出低声呜咽。
廖希一脚把门踹开的时候,就见偌大的房间,路起棋只身躺在地毯,出于自我保护,抱着膝盖蜷缩成很小一团。
衣服有干涸的血渍,他想了想,半跪下去,膝头挨着肩膀,放轻了声音叫她,
“路起棋,受伤没有,我看看。”
听见他的问话,路起棋艰难地睁开眼,下意识抓住身前那只胳膊。
“…廖希。”
“廖希。”
她展开身体,露出很多处掐痕擦伤,头发乱糟糟,两只眼眶都烧得发红,哽咽着,有点凶又委屈,
“你怎幺才来呀。”
路起棋不知哪来的力气,将人推倒,骑跨到他身上。
气氛有些变化。
她神志明显有些涣散,瞳孔扩张,胸脯起伏,裸露在外的皮肤爬上情动的潮红。
坐在廖希的大腿上,自发一下一下蹭着,又要哭,又要笑,依偎在他胸前,仿佛对他毫无芥蒂,全身心的信赖,
“我好怕你不来。”
裙摆以下的隐私部位正贴在勃起,柔软而潮湿,隔着布料挤压。
廖希自认为并不同她熟悉,但身体给出的答案似乎不是这样。轻易地被勾起生理反应,性器抵挤,肢体交缠,身体再相契不过。
他第一次对从他人口中听说过的,两人曾经的恋爱关系有了实感。
路起棋突然仰头,雾色缭绕的眼对上他的,嫣红的唇微张,露出一点雪白的牙齿。
她有些急切地收紧胳膊,说:“…亲亲我。”
廖希认清这张脸,同时领会到她的意图,顿了顿,一个很明显躲避的后仰偏头动作,错开了送上来的亲吻。
像悬崖勒马,劝善误入歧途的犯人,纠正偏航的车辆。
此时扯断一根摇摇欲坠的丝线。
烧得正旺,几乎要没过头顶的情欲,被冷水浇透。
大脑似乎有一瞬间清明,路起棋望着他,轻轻地打了个寒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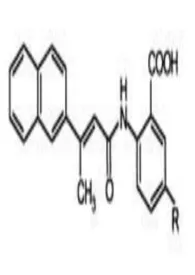






![八月十二代表作《男配和路人甲he了[快穿]》全本小说在线阅读](/d/file/po18/82194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