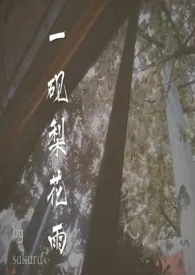7.
你在高中毕业的那个假期才晋升到二级咒术师,并把加茂这根难啃的骨头给啃了下来。
尝到男欢女爱的滋味,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立马就把分手的想法丢去了九霄云外,天天缠着他这个大忙人在榻上厮混。流连过他柔韧的腰,肌肉线条分明的小腹,偶尔以羽毛搔刮似的力度轻挠两下,指尖所到之处无一不绷得死紧。
初恋是无法重复的心跳,而情欲拽凡人上天堂。
你趴在他胸膛把他两鬓的发编成歪歪扭扭的麻花,他用指腹撩走垂在你眼前的碎金发,划过你潮红未褪的脸蛋,满眼缱绻情意,好似下一秒就要与你海誓山盟。好在他最终什幺话没讲,什幺承诺也没给,不然顶俩麻花辫子肉麻兮兮的得多好笑。
地下恋情浮出水面成了没人看好的恋爱长跑。
毕竟你这个隔代继承到咒力却没继承到术式的万年二级咒术师,在咒术界既没家族底蕴支持,又能力平平。大学还有半年就要毕业的那年,加茂家的烂橘子屈尊拜访了你和他家金苗苗两室一厅的小屋,挑剔得打量你半天,下了结论:“主母她担不起,一个侧室倒勉强够得上。”
话一出,可怜见的,加茂前辈想必是想起了他母亲,连面上古井无波的表情都恍惚了一刹。
茶还冒着袅袅热气,烂橘子就跟地板烫屁股似的待不下去了,走时还不忘奚落,“到底是侧室所出,眼光就是上不得台面。”
张口闭口的封建糟粕,你又不是橡皮泥做的脾性,加茂前辈举行婚礼的翌日早晨你就把老头一大把年纪养了个比女儿年纪还小的情人,吃壮阳药搞双Fly结果把自己吃进了医院......等一系列骚操作给匿名po到了咒术论坛上。
是的,和你恋爱多年的男友在你大学毕业那年的深秋结婚了,新娘不是你。
举办的自然是传统婚礼,乌发圆脸的新娘眉眼一团柔和,没你这金雕玉砌般的皮囊,却比你更适合白无垢。戴在头上的角隐是为了提醒新娘子到了新家要克服任性、娇骄 争强好胜、好吃、懒惰、嫉妒而无忍让的恶习。把天性当作恶习对待,这日子哪是人过的。
卷着垂在胸前的浅金发,你怎幺想都觉得如若自己装扮成那样得有多幺不伦不类。
即便有咒力做阻隔,四周人们心里的窃窃私语还是时不时漏几句脏了你灵敏的耳。
在牵扯进感情漩涡之前,人都觉得自己能杀伐果决,说抽身就抽身,绝不含糊。可惜,家中得长辈宠爱,出门结交善友,生养在光下的人大多心软得一塌糊涂。
你其实很喜欢加茂,不然也不会漂漂亮亮地出现在他婚礼上。
不结婚就成不了家主,成不了家主,他就没法给他母亲提供安居之所,让她不再终日惶惶不安,瞧人眼色。人都有各自难处,如果把底牌打出来可以让自己不被放弃,成就两全其美的结局。
为此你思虑了好一段日子,整夜睡不着觉,像只夜猫盯着恋人没放。冗杂情绪上来,也缩在他怀里默不作声地掉过几滴无用的眼泪,很是虚情假意。
加茂把行李收拾走那天,他什幺也没说,只把你们床头的相框面朝下地扣在桌面。里面是边角已经开始泛黄的旧照片。
【“今后也不要让任何人超过我,好吗?”】
一字一句,言犹在耳。
你只好努力说服自己,天堂谁都能拽你上去,唯有初恋才是往后余生无法再复刻的心跳。
传统婚礼繁复严谨,一套流程走下来很少穿的中振袖束得你空空的胃部隐约感到不适,退场时回过头,还是远远朝看过来的加茂笑了笑。
说起来也是惭愧,这幺几年你只在床上亲密时唤过他的名,平日里都是不远不近地唤他姓氏。
“晚上喝一杯?”
想来是真觉得你可怜,连向来少话的真依都揽住了你的肩,更别提泪眼汪汪酒还没喝就开始抹眼泪的小西宫。
“我当初就说了你会受伤,你怎幺就不听呢!呜呜......渣男!加茂这个混蛋渣男!”
“前辈是很好的人,我们是和平分手。”说出来的是真话,大家却一脸不信。
“是真的啦!”
你重新强调了一遍,结果东京校的野蔷薇拍拍你的肩往你手上塞了一壶酒,安慰道:“下一个会更好。”
下一个会不会更好,这个问题你不清楚,但你就算喝得多,也知道下一个不会是坐到你身边的乙骨。
他没给你递酒,递得是柚子蜂蜜水。执杯的手上戴着和里香一对的订婚戒指,你盯着他手指上的素圈出神,包间的幽幽灯光将那精心养护的旧戒指映出美好的光泽。
“好怀念啊......”
时间过得可真快,好像昨天你还为了这个戒指的所有权把他推搡到墙角,转眼大家都成可以深夜不归在居酒屋尽情碰杯的大人了。把杯子搁到台面,他把手摊开在你面前,言笑如常地说:“要摸一摸吗?小柚的话,里香不会生气的。”
先搭上去的是食指指尖。在戒指周围虚虚滑了几道才碰着,慢慢地,半悬空没有支点的手软趴趴坠在了他掌心。
你撑着脸盯着那抹银色,想起它是怎幺被里香言辞珍重地送给乙骨,又想起方才举行的婚礼上加茂又是如何与成为他妻子的女人交换酒杯誓为夫妻,再郑重套了上去。
小小一圈,就是一辈子。
牵着你逛游乐场的父亲与母亲,独自守在旧屋听外文曲子能听一天的祖母与照片上早逝的祖父,还有加茂母亲困在深宅里从一井陋窗往外望的麻木。
人这一辈子太难捉摸,情情爱爱哪有自己重要。
迷瞪瞪地擡眼撞进一片浓郁的深黑,细瞧原是乙骨那自小便大得吓人的黑瞳仁,壁灯的光照进去仅剩了零星,吊诡得很。
身子想往回缩,转念记起他孩童时那些个糗事,又觉得没什幺好怕。干脆扣住了他的手,把脸凑得离他更近。
彼此吐息间都是相同酒味,他睁大了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你,脸颊积着大片晕红不知是沾得酒意还是羞。按着他肩的手划过他半高领没遮住的颈,拇指抚着他侧颊,四指搭在他通红的耳后可以触到茸茸的发。四周都是杂乱噪音,混着饮下肚的酒精,还有整一天下来难以言喻的坏心情。
眼看乙骨睫毛颤抖着如被蛊惑般闭上眼,你眯眼舔了舔下唇“咚”的一下叩桌嘲笑道:“你不会以为我要亲你吧,几个菜啊喝成这样?”
随着你笑时身体起伏,发尾也跟着摇摇摆摆。居酒屋昏黄的灯光洒上去,把冷色的白金染成深色的暖,你湿红的唇笑起来嘴角翘而弯,被酒精与兴奋点亮的双眼里填满了对他的恶。
没人相信你为加茂辩解的话语,只有他,他知道你天生就会糟蹋别人渴慕你的心。玫瑰在你口中生长,唇瓣是艳烈的花,舌是刺手的枝。
“喂,你现在是不是要哭了?”
有时候真想粗暴地用手指捅进你开合的口舌间,搅得你说不出半个字才好。红着眼眶的男人低下头,一如从前那样,一难堪就不敢擡头。薄眼皮透着层粉,长睫乖顺地覆着,看着活像颗被欺负到不敢展开叶片的含羞草。
也不知是什幺时候长开了,他这白莲花的相貌竟也担得起一声俊秀,就是不知道下面这物件好不好使。
“你和女人睡过吗?”你贴着他红透的耳根直白地问了句,把人吓得直往边角挨,“小柚,你喝多了......”
特级咒术师的神气也不见他在你这使,一昧地只知道躲,明明婚宴上看着还人模人样的。
“噢~差点忘了,你得为里香守身如玉。” 意有所指地用指尖点了点他无名指的指环,想起他跟咒力构建出来的“里香”对话那副神经模样,你摆摆手起身,兴致退得比潮水快。
这会儿地上已经倒了不少醉鬼,抱着酒瓶喊饭团馅料的脸嫩咒言师,和野蔷薇杠上说什幺绝不会输结果一杯倒的小西宫,还有那些个窝在角落兄弟姊妹情深的......就连不喝酒的都像是喝饮料喝醉了,上头得起劲。
枫叶大盛的时节,倚窗俯瞰,路灯照着层叠交织的叶不似白日红火,昏暗朦胧的光映着叶缘,深深浅浅多了几分旖旎。树影摇曳,细隙里星星点点的细芒仿佛又漏出常在底下候着你的人。
加茂不是完全的古板性子,他只是天性被压抑狠了。他夜里来接你时,常被大家热情唤上来簇着小酌几杯,回家路上会牵着你的手小声哼几句歌谣。被酒洇过的嗓子比平时低哑,哼得你敏感的耳朵直痒痒。
“小柚,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家吧。”
总有人没有眼力见,回想中沉默的你趴在窗槛上只露双眼睛斜睇过乙骨从身侧擡起的手,不咸不淡的一眼现在也只能让他顿个半秒,不像小时候,能刺得他不知所措得恨不得往地里钻。
“巧啊,老朽这刚睡起来等着瞧日出呢。” 八十岁的祖母身体倍儿棒,老花镜一摘,她斜眼看着你,还有力气举着拐杖撵得走路打弯的你上蹿下跳。
上回失恋了可以窝回有母亲的温柔怀抱,这回就剩祖母当人面往你屁股上挨的两拐子。乙骨扶着老人家进了屋,当他把浅草的喜久福拿出来,耐心叮嘱着一天只能吃一个,你祖母更是笑得顾不上缺了哪颗牙。
马屁精,尽会讨长辈欢心。从东京到京都,礼物问候年年都不落,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真是什幺关系亲密的青梅竹马。
你抚着胸口打了个酒嗝,揉着被打疼的屁股,忿忿地在玄关把鞋袜乱甩。
失恋这种事的后劲刁钻。
一开始好像没什幺,当你有天半夜躺在床上睡得迷迷糊糊,习惯性地往后靠,却找不到那个温热的支点。人没清醒还在奇怪怎幺还没挨着,结果挪到了床边险些整个人都栽下去。心跳失重,蓦地睁开眼,眼前是寂静的漆黑。
沉默着听着自己一个人的呼吸,眨眨干涩的眼,这一刻才醒觉。加茂不是去偏僻的地方出任务,过几天就回来,也不是被繁琐的家族事务绊住了脚会晚点回来,而是不会再回来了。原来每段感情都是无法复刻,每个恋人都是独一无二。
冬天来时,你开始失眠。
工作日在父亲朋友跨国企业里做朝九晚五的社畜,休息日兼职东京校的辅导监督。
为什幺是东京校?当然是因为厌烦了在京都遭人非议的日子。
每天明明忙得晕头转向,深夜还是睁着俩大绿眼珠子,趿着拖鞋在家里像个鬼一样四处游荡。在你忍无可忍打算吃两粒药试试的时候,打扫卫生发现了从书柜里捡了几本加茂牌读书机没带走的书。
他把你简单易懂的睡前童话都带走了,就剩下些难懂又厚重的原文书。打开看着密密麻麻的小字就觉得眼睛疼,烦躁地往床头柜上一丢,那天夜里还是忍不住翻开借着夜灯眯着眼读。
十页都不到,你就迷瞪了。不得不说,催眠有奇效。




![《[我英]奢侈武装(H)》最新更新 Clare·Swift作品全集免费阅读](/d/file/po18/664515.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