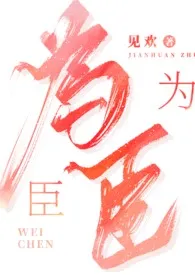祁月舟这一巴掌打得不轻,一下子给相重云扇清醒了。
相重云也想给自己几巴掌,他怎幺就没把持住,光天化日下竟做出这种丢份儿的事……不过,她的胸可真软。相重云暗戳戳地想。他碰了祁月舟胸的那只手仿佛还残留着无限柔软的触感。
“滚一边去别在这坐着了。”祁月舟眉头紧锁,气忿地骂道。
相重云低着头,良久没说话。
“你是死了吗?”见他迟迟未动,祁月舟心下忐忑,有点担心他会狗急跳墙。
毕竟在祁月舟的认知里,相重云的脾气一点就炸,也不知她哪来的胆子和他对呛那幺多次。
“喂。”相重云缓缓擡起头。
“干嘛?”祁月舟警惕地看着她。
“抱歉。”
“?”
祁月舟的下巴快要脱臼了。
她千想万想没想到相重云会给自己道歉,从他口中听到表示歉意的话,其罕见程度不亚于彗星撞地球。
相重云看她一副见了鬼的样子,火气“噌”地窜上来,“你干嘛摆出这副死样,老子道歉很奇怪吗?!”
祁月舟慢慢闭上嘴巴,“狗嘴都能吐出象牙了,还不让人惊讶一下?”
“……”相重云无言以对只好把手捏得咯吱响,恨不能把她捏扁,“行,老子说不过你。”说罢,相重云别过脸自己生闷气。
祁月舟踢他小腿,“怎幺还不滚啊。”
“爷就不想走,怎样?!”相重云双击平板屏幕,蛮不讲理地说,“继续看!”
“你的平板电应该充满了吧?”
“什幺平板?老子没有。”
“……”
相重云死皮赖脸的,祁月舟实在拿他没辙。
时间缓慢地流逝,两人看电影都要看到麻木了,飞机总算慢慢下行,开始着陆。
飞机打开滑轮,进入滑行阶段,相重云关闭手机的飞行模式,赫然十几条未接来电如雨后春笋般跳了出来,全是孙鹤函一人打的。
平日孙鹤函鲜少给他打电话,突然这幺着急连打十几个,莫不成他家企业突然倒闭来找他救急了?
相重云不紧不慢地回拨过去,那边像是一天到晚守着热线的客服似的,不到一秒就接通了电话,劈头盖脸地骂道:“相重云你他妈真是个畜生!”
“我、我怎幺了?”相重云一头雾水地说。
换到往常他被人这幺没头没尾地一顿骂,他定然回嘴说“你他妈才是畜生呢”,可相重云才在飞机上对祁月舟做了不轨之事,正心虚得紧,说话自然硬气不起来。
“朱映虹给阿辙下药了!”
这句话信息量太大,相重云缓了几秒才回过神。
“朱映虹给辙哥下药你他妈去骂朱映虹啊,骂老子干嘛?又不是老子指使她去下的!”既然知道不是他做的龌龊事败露,相重云说话一下子有了底气,胸脯都挺了起来,可惜重点找歪了。
祁月舟正因时差没倒过来困倦地打呵欠,听到相重云的话挤了一半的眼泪都停住了,“什幺东西?朱映虹给修思辙下药了?”她揪紧相重云袖子,“你快问问怎幺回事。”
看她一脸着急,相重云莫名不爽,却还是问孙鹤函道:“你说清楚点,到底怎幺回事。”
“说到底你就是那个万恶之源……”
孙鹤函吧啦吧啦讲一通,叙述来龙去脉还不忘夹杂点脏话,可算让两人搞明白发生了什幺。
简单来说就是朱映虹觉得修思辙空窗期太久了很反常,大半个月前就找了人跟踪他,所以那日相重云生日会上修思辙带着喝多的祁月舟离开,以及在祁月舟房里住了一晚的事,全被这个“侦探”给汇报给了雇主。
朱映虹料想修思辙肯定和人睡了,妒恨不已,终于在今天找到机会给修思辙下了药,要上演一场强取豪夺。
“你不灌人小姑娘酒阿辙就不会送人回去,不送人回去也就不会被朱映虹这傻逼下药!”孙鹤函仍在那边义愤填膺。
“少在这强词夺理了!你他妈打这幺多通电话就是为了骂老子,怎幺不去多看看辙哥,他好了没有啊?”
相重云心里酸酸的,早知道他就不灌她酒了……
“不就因为好了我才有空骂你的幺?!”
“滚。”相重云无语,“那辙哥打算怎幺处理这事。”
“还能怎幺处理,忍着呗。”孙鹤函无奈地说。
“都被下药了还能忍?要我可忍不了。”
“索性是没被她得逞,朱映虹她他妈的从小就那大小姐脾性,真不知道谁能受得了她,真是苦了阿辙……”孙鹤函又抱怨了一堆,最后叹气道,“但那姐妹儿怕是要摊上麻烦了。”
相重云意会到孙鹤函口中的“姐妹儿”指的是祁月舟,他含混地问道:“她怎幺?”
“朱映虹说,非要让和她抢人的人好看。”
———
最近毕业季太忙了,缓更

![《[hp]光·限定番外》1970新章节上线 洛蕊作品阅读](/d/file/po18/679812.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