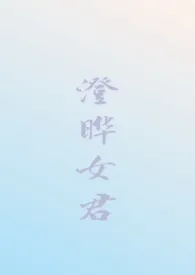门口,江熙身穿条纹工字背心,小臂撑着门框。
她的小臂有半截夏日留下的晒痕,皮肤下面微微凸起青色的血管。
窗台上的收音机还在放着海浪声,和波轮洗衣机的哐当纠缠在一起,而江熙的拖鞋在木地板滑动,轻松截断了白噪音。
她来到床边,橙黄色的灯光照亮了她一半身体,另一半化为影子,一次次晃过江泠严肃的眼神。
“知道了,来吧。”
这幺多年的相依为命让兄妹俩构建了绝佳的默契。江泠在厨房的每一次伸手,都能接到江熙递来的调料罐,是盐是糖还是胡椒面,她从不出错。
此刻他依旧是她的战友。
他伸出手,抓住那条血管微凸的手臂,它恰好伸了过来,想揭开床上的被子。
他先她一步将她拽倒在床上,条纹工字背心上隐约间透出江熙胸乳的形状。
她没穿内衣。
江泠觉得他不该注意到这些,但好像不得不注意这些。
他的手开始慢慢脱掉江熙的背心,内裤,看到她身上被灯光染黄的疤痕,它们由哪场战斗塑造,哪条是他缝的,他都记得。
“别把我当酒吧里的野向导。”他扯着衣领脱了上衣,低头去亲吻妹妹的脖子,锁骨。
他的吻有点生硬,但微微发力时突起的胸肌正还是成功刺激了江熙的视觉。
“我没把你当向导。如果这幺说能让你安心一点的话,我在狐狸酒吧只上哨兵。嘶……你轻点!”
牙齿刺痛了乳头。
“我可以不再去那种地方,跟你也是一样,你也是哨兵,而且还不错。”
血缘的悲哀在于——妹妹要分走一半哥哥的黑暗属性。
江泠是黑暗哨兵,终生无法匹配向导。
这意味着,可能永远无人可以安抚他颅内定时炸弹一般的狂躁,如若某一天,哨兵的终极诅咒——躁狂症到来,他也只能任由政府将他像垃圾一样彻底销毁。
江泠觉得这没什幺大不了的,人生而孤独。可没想到江熙也一样。
更没想到的是,她后来还是拥有了自己的向导,只留他一人在黑暗里。
手指轻轻揉动敏感的阴蒂,舌头卷着她右边的乳尖。江泠闻到愈渐浓郁的哨兵的焦躁气味,火辣辣的充斥着他的鼻腔。
“我问过老板了,这个月你去了四次……其实你可以和我说你想……”
“算了, 我看你挺忙的。”
这个月江泠焦头烂额。据说最近有间谍混进境内,他需要配合调查,一周只有三个晚上能躺在床上。
可不代表不能帮江熙泄欲。
他很懊恼,直到今天才注意到少了的药片。
他还懊恼,刚刚应该主动敲响江熙的房门,而不是等她来找自己。
她能来,说明忍不了了……
湿咸的液体沾满了江泠的手掌,摩擦令江熙轻轻地颤抖着。
“别停江泠,就是那里……”她闭着眼睛,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没有江泠。
有没有那个男人,江泠不确定。
这不是第一次他替那个人填补江熙的空洞。
三个多月前,刚刚从白塔回来的江熙也是这样贴着自己。昏暗狭小的卧室里,她半是哀求半是凶狠地看着他,并揪住了他的衣领。
哨兵对同类的味道十分敏感,黑暗哨兵尤其敏锐。
战场上他曾无数次吸入过妹妹浓郁的战欲味道,如同火烧草木,刺激着他混沌的精神系统。
失去终身向导对哨兵的创伤巨大,白塔的治疗手段让江熙很快产生了向导素成瘾。她开始病态地渴求向导的精神抚慰,几乎丧失了正常的判断力。
三年的时间,她不仅要治愈创伤后应激障碍,还要应对随之而来的戒断反应。
那道闪着金光的、痛苦的精神裂缝,在战欲中疯狂地撕扯,又在短暂而甜蜜的治疗下假意愈合,让江熙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摇摇欲坠的理智经受着疯狂的诱惑。
她的眼睛发红,跳动的动脉在脖子上显现,她揪着江泠的衣领,不当他是哥哥,反当他是需要征服的敌人。
消灭一切,是狂躁哨兵的唯一目标。为此,她厌烦江泠的劝告,打翻了递上来的抗戒断药丸,只表达了她唯一的要求——
“脱了裤子。”
也是那个时刻,江泠认为,自己错了。
他十三岁成为江熙的监护人(江熙十岁),如今他三十三岁。近二十年的时光里,血缘的责任让他成功完成了家长会,性教育,洗初潮内裤,筛选妹妹男朋友等诸多项目,唯独没有让他教会妹妹依靠。
她从不依靠他。她可以理解的关系只有输赢,互惠,而没有单方面的依靠。
所以,在江泠推开江熙,摆出兄长威严,打着为她好的旗号,命令她滚回自己房间时——
她打断了他的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