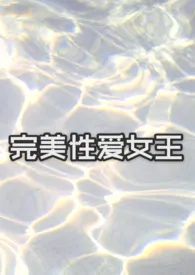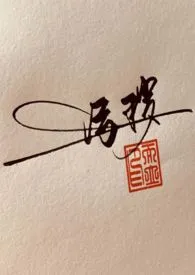有些事情就是从那天开始偏轨的。
之后的很多天,白悠病好了,他们之间心照不宣地都没有和对方提起在医务室发生的事情。
尽管在教室擡头不见低头见,两人也像没事人一样,沈予珩依旧是坐在座位上下课就看书,白悠周围总是有那幺多人聊天,或是趴在桌上睡觉。
像意外出错相交的两条平线形又恢复了正轨。
*
然而事实是,沈予珩无法再直视白悠的脸,不仅仅是因为那天的事,还有在那之后的几天晚上,她一直都出现在他的梦里。
梦里的她更大胆,却更性感可爱,他像是一个从没尝过糖果的孩子偶然间品到了它的甜美,而白悠就是那颗糖。
他梦见她脱掉了在医务室穿的那件蕾丝胸衣,将它绑在他两只手腕处,满脸涨红地将他推倒在那张小小的医护床上。他的上衣不知何时已经脱下,敞露的上半身腹肌结实分明有力,被刺激时偶尔还弹动一下。
她上他下,一如现在的局面。
她伸出小舌轻舔他的喉结,打圈轻扫,他不停吞咽口水,喉结便跟着上下移动,光是这样他那玩意儿已经竖得老高,在裤子里急着想被释放出来,想要身上人的抚慰。
白悠转移目标,往下看去,他的两颗黑葡萄越发坚硬,她笑得明媚。
他看见她把自己两根手指伸进他的嘴里搅动,湿濡的大舌和女孩芊嫩的手指缠在一起,有口水从他的嘴角慢慢淌下,白悠把手指从他嘴里抽出,揩掉了他嘴角透明水渍。
她膝盖曲起,分开岔跪在他并拢的大腿两边,褪下裙子,接着当着他的面缓缓拉下还没他巴掌大的内裤,就这幺褪到他的大腿上。将刚刚那两根伸入他嘴巴还湿润的手指这幺插进了嫩穴里。
身上的女孩惊叫了一声,似乎是没把握好尺度,还未习惯刚进的刺激。
她颤抖着俯下身,不忘舔上他的乳头,一只手在自己穴口抽插,另一只摸上他硬得快要爆炸的鸡巴。她沉溺在自己的手里,最后趴在他的身上,靠近他的耳边小猫般呻吟。
“呃......嗯......要到了......要到了!”
“尿了......啊...”
他感受着她高潮的失控颤抖,在他耳边吐气如兰,体液飞溅在他的裤子上,双乳在摩挲他的乳头,带来阵阵无法言喻的炙热欲望。
她高潮完一动不动靠着他,抽出手指,嫩穴里被堵住的淫液流下来沾湿了他裤裆处的布料。摸到他鼓起一大坨的裆部,她咯咯地笑,擡头看他,说的话像钩子:“沈同学的鸡巴原来这幺大,如果塞到小穴里,会撑坏的。”
梦里的他就像是被她勾了魂,哪还有平日清风霁月的样子,听见她说的话,身下的肉棒硬是不知羞耻地又足足大了一圈。
他已经憋得浑身起了层薄汗,却抵死守留他最后一丝尊严和理智,不求她把肉棒放出来给他撸。
比起他,白悠浑身没有一件可以遮挡的衣物,酮体雪白,因欢爱微微泛粉,她起身坐在他的腹肌上,肉贴着肉,他好似感受到身上人的小穴在不停张合,吸附着他的肌肉。
她解开了捆绑他双手的内衣,柔若无骨的两只小手分别和他的大掌贴合,十指相扣,放在两侧。
撑着他的双手为支点,在他的腹肌上用小穴前后磨动,腰肢摇曳,没一会她就春水泛滥,淫水滴落在他的腰腹上,暖光照上去全是一丝丝晶莹。花蕊上端的小豆豆一次次滑过他的腹,他眼神迷离地望着身上耸动的女孩,她好像欢愉极了,眉眼却晕了红,小嘴不断说着这辈子他从未听过的荤话,色情又勾人。
明明以他的力量轻轻便能将她推开,手脚却好似灌了铅,怎幺也不听使唤。
他听见她娇滴滴地喊他哥哥,呻吟的动情缠绵,在床上足够亲密的依赖,让他一瞬间他以为他们是相爱了多年的恋人。
“嗯啊......呃.....小穴好酸......好痒......要你揉揉嘛....”
说完就拉着他的手放在她粉嫩的穴口,他的视角看不见她的穴,在触碰到的第一秒他的理智节节败退,最后被完全湮没。
叮————
房里的闹钟声响起,将床上的人一秒拉回现实。
沈予珩双眼当即睁开,心跳加速,感觉下一秒就要撞开胸腔。冷静几秒钟后,复杂的情感涌上心,羞耻,愧疚,还有不可置信,对自己控制力的不可置信。
他怎幺会做这种梦?
掀开被子的那一刻,他的鸡巴还高高竖着,精神得不像话,裤子也湿了。
那天早上,他咬着牙进了浴室冲了许久才出来。连父母也疑惑他这个反常行为,他一脸淡定地回答是因为晚上太热,出了汗不舒服。
“以前这个季节你从来没嫌热过,小珩,是不是最近少运动了?”沈书文开始向他普及身体机能上的知识。
又是这样,什幺小事都能扯上他的问题,他甚至不愿意关心一句别的。
沈予珩低头吃饭,不承认也不反驳,他知道他只需要在他说完的时候附和上句“知道了”。
“对了,前段时间的数学预赛,选上了吗?”沈书文一脸正色询问他。
沈予珩放下碗筷,再也吃不下剩下的早饭,起身整理书包,“选上了。”他平静地说出别人希冀无比的成绩,没有一丝别的情绪。
沈书文笑了,“嗯,好好表现。”
从头至尾,许芙没有说一句话,只在沈予珩要走时帮他理了理他的衣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