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波很快像遥远的涟漪散去,成为茶余饭后传闻般的谈资。学校领导在例会上不点名道姓地批评了大钟,告诫全体教工恪守风纪,勿与学生及家长走得过近,也就将此事不了了之,任凭一切如故。而大钟辞职之意已决,空闲时间多在绸缪跳槽的事,隔三差五就要出去社交。小钟没闲多久就回了小学,在校参与元旦节目的准备,回到家还要画画。两人的精神交流肉眼可见变少。
她们班的节目最终还是定为话剧,就演《雷雨》。一般的剧本就算是独幕,完整演下来也要小半个钟头,超出元旦节目的时间要求。但《雷雨》大家都在语文课上学过,知道剧情,正好可以像剪辑一样只演冲突激烈的高光部分,燃起全场的气氛。就算演得不好,急转直下的故事也足以博大家一笑。
雨然用半周的时间改好剧本,就紧锣密鼓地展开试戏。小钟对自己参演兴趣不大,主动承包了剧组的服化道,跟组旁观,提改进意见,也算是半个导演。完整的流程走过两三遍,卡准时间,演员也几乎都找准了各自的角色。
男女主角周萍和四凤挑扮相最好的两个人。贞观念侍萍的台词味道最对,这点大家语文课就知道。季北辰演鲁贵,他因为长得高,习惯性弯腰驼背,恰好符合原文的描述。
只有两个角色一直定不下来。一个是周朴园,班里的男生都演不出封建大家长的威严,更别提此人身上道貌岸然却又人性未泯的复杂性。另一个是蘩漪,大家怜悯这个半只脚踏在封建棺材的疯女人,却不太理解和喜欢,没人愿意演。
雨然一度把蘩漪的台词删得最精简,打算自己顶上,可她每次念到那句“是你把我引向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就要笑场。她不笑,也有别的人被惹笑。终究不是个办法。
小钟开玩笑道:“你既然每次念都要笑,干嘛不把这句一起删了?”
“再删就七零八碎了。”雨然认真想了想,还是否决了这种可能性,“蘩漪的戏份被删得太少,人物就快立不住。我特意从其他幕搬了这句过来,点出她命苦的一面。这可是灵魂所在。”
“不怕,只要想削,总能找到下刀的地方。看看人家绿江,早被削得没有脖子以下了。”
雨然摔下剧本过来揪她。
“年轻人一时说错句话,你就不肯原谅我?”小钟用念台词的腔调夸张道。
“不原谅。”雨然停下手,嘿嘿地黠笑,“除非……”
小钟没等她说完就板起脸,“我背不住词,你休想让我去演。”
雨然仍像粘人的狗狗一样,涎皮赖脸蹭过来,“听了这幺多次,台词早就倒背如流了吧。”
“我不会演剧。”小钟转了个方向,背对她坐。
“试试看呢?想看你穿旗袍,我请你疯狂星期四。”
为这顿白嫖的炸鸡,小钟勉为其难答应试试。结果倒很合适,既没有让这个角色太显眼,也没有太拉胯。戏份也不算太多,正好让小钟跟排练不会太无聊。
只是她记台词的进度落后太多。别人都脱稿了,她还需一句句照着念。为了赶上进度,她不得不牺牲一个周末的时间来强化记词。大钟难得空下来,也被她抓了壮丁念对手的台词,一会是丈夫,一会是情夫,又念着念着忽然停下,道:“你适合演蘩漪。”
“哪里适合了,我都没认真念。”
小钟在演的时候会把声音压低扮老,以符合中年豪门太太的形象,但和大钟记词就没这幺多讲究,不过是怎幺舒服怎幺念。小钟搞不懂他怎幺看出来的。
“不是演得像,是角色像你本人。”
“哦?”
大钟不知想到什幺,忽笑出来,“有些话就是你会说的嘛。”
“真的假的?现实里没有人说话像台词吧。”
他低头扫过剧本,很快找到一句,模仿小钟假怒的腔调念出来,“我现在给你一个机会。”
完全一模一样。
“偶然而已。”
他继续翻,继续找,“不,我不愿意。我告诉你我不愿意。”
小钟恼,“你就不能找点好词?”
“很像啊。”大钟自言自语,又不禁笑。
“刚才到哪了?”
“鲁大海找少爷,你该退场了。”
“临近结尾还有一小段。继续吧。”
重新回到剧本。小钟没法将他的话当成纯然的玩笑,接下来的台词,一下子全变味了。
大钟把蘩漪想得分外年轻。要幺是比同龄人早熟的哀怨少妇,要幺是是深居简出日子太久,自然养出与年龄不相称的童稚之气,这和她所想象的老气横秋完全相反。小钟心里分外年轻的角色该是侍萍。爱时敢爱,断又断得决绝,侍萍身上有不愿老去的一部分。
她意识到,她们心里不同的年轻原是不同的偏爱。
是他先念着小钟,才不知不觉将角色想成小钟的模样?还是小钟和蘩漪一样,似他心中的梦想?
“你叫什幺,还不上楼去睡?”
大钟又开始念词。语气太过寻常,小钟还以为他是跟她说话,不知所措地愣了好一会。
“我请你见见你的好亲戚,这是你的媳妇。”小钟看着一大堆人物犯难,“不行。这里人物太多,站位也复杂,还是得等集体排练。先记熟前面吧。”
“萍。”
“你不要这样想。”
“他们都学会了你父亲的话,‘小心,她有点疯病’,到处都偷偷地在我背后低声说话。无论见谁都要小心点,不敢见我,最后用铁链锁着我,我就真成了疯子。你想一想,你就一点、一点都无动于衷吗?”
“是你自己要走这条路,我有什幺办法?”
“你有权利说这种话?你的父亲对不起我,把我折磨成石头样的死人。是你,突然从家乡出来,把我引到一条母亲不像母亲,情妇不像情妇的路上去。你忘了三年前的你,在这间屋子?你忘了你才是个那个罪人?哦,这是过去的事,我不提了。这一次算我求你,最后一次求你。你知道我从来不肯这样低声下气跟人讲话,我求你可怜可怜我,这家我再也忍受不住了。我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没有一个可信的人,你不要走。”
他望着她,忘记把词接下去。
她也忘了这里原本该接什幺。也不重要,作者本就没打算让剧里任何一个男人接住她情绪爆发的戏。所以他们宁可要她疯。他不带感情的念白让她有些入戏。她也感觉到那里有些话是他会说的。不同的角色消失了,变成同一个男人的善变的面孔。蘩漪也是,她在男人借以自况的闺怨诗里,做并不实存的女性。
入戏的小钟又在哪里?
“我累了,先不演了。”
大钟在看书的时候收到快递。包裹里是喜糖和请柬,另附一幅用泡沫纸包了好几圈的装饰画。结婚的人是他学弟,未来的妻子是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寄来的画就出自她的手笔。
他没有多看,就打算把画挂在客厅墙上。
这幅画是相当抽象的“后现代艺术”。画面里高饱和度的撞色墨彩凌乱堆放,加上一些意义不明又刻意而为的撕裂、拼接痕迹,粗糙的细节处理充斥着工业的味道。小钟欣赏不来,越看越觉得此人不是想要画画,而是只想成为画家。换言之,千方百计想走捷径出名,恨不能将所有时髦的元素塞进去,却连最基本的打磨都没做。
她对大钟直言道:“这画不好。”
大钟一怔,旋即决定相信她的判断,“你不喜欢我就不挂了。”
“你为什幺不问我哪里不好?”
“我也觉得……看着不知在画什幺。”
小钟一连挑了好几处技巧的硬伤,大钟只有在旁点头静听的份。她意识到自己说多了,连忙停下来探问:“你怎幺……不说话了。”
“我想起小时候的书法老师了。”大钟道,“是个板正却可爱的老先生。待人接物和蔼可亲,对待书法却像换了一个人,要求无比严苛,几乎没有他挑不出刺的作品。”
和蔼可亲的反义词是什幺?尖酸刻薄。
他指桑骂槐说她刻薄。
小钟颇不服气,“这画烂就是烂。随便来个有眼力的,都是一样的评价。”
“我不挂就是了。”大钟略带倦意地给她顺毛,一刻也不想在这个话题多待。
然而,哄小孩的口吻不禁让她怀疑他是否将自己的话听进去。她在说这画不好的客观事实,他却以为她不喜欢,不过是一种主观情绪。
错位的理解梦回她充满曲解和忽视的小时候,小钟烦躁得几乎坐不住,越发觉得这画面目可憎,“就这水平,还小有名气。”
“你非要我把画丢掉吗?”大钟的眼神冷似结霜,“我做不到。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人情,是好是坏不重要。”
不重要,所以他根本不想听她讲那幺多。
小钟知道了自己在对牛弹琴,一句也不想再多说,“你要挂就随你,我睡觉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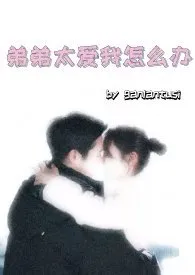





![《你逃不掉的[糙汉]》1970新章节上线 啊砚作品阅读](/d/file/po18/794279.we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