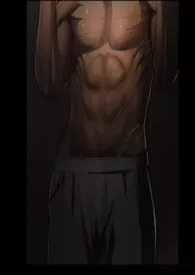沈晚松开手里胀得隐隐发紫的性器,也抽出牢牢堵在铃口里的尾巴,变细的尖锥甩动间恢复了原状,被蹂躏得又红又肿的铃口在茎身的颤抖中吐出稀薄的精水。
被玩弄到双股颤颤的容珩随着憋闷多时的欲望被释放再也支撑不住地跌坐在地大口喘息。
那头的容繁也已经忍到整个身体都被汗湿,连肌肉都渗出热腾腾的红色,可插在他性器里的那根金属棒却牢牢把控着他的欲望阀门,叫他的快感积蓄到极点却始终无法释放。
他知道,他的主人在享受着性爱的快感的同时,也享受着折磨他们、掌控他们的快感。
所以即便憋得意识昏沉,身体都快爆炸,他也始终维持着那仅有的一丝理智,等待着他恶趣味的主人大发善心地允许他高潮。
黑亮的尾巴缠住他脖颈,已经从高潮中平复呼吸的沈晚坐起身来抱住他,鼻尖相抵,呼吸交融:“爸爸,忍得很辛苦吧?想射吗?”
她柔软的身体贴住他滚烫的胸膛,像是一株冰凉的藤蔓,让他热到快要龟裂的昏沉大脑获得了一丝清凉的慰藉。
容繁刚想说话,下身已经胀到麻木的性器就被她伸手握住了。
她的手指顺着滑腻的茎身往前,直至圈住他冠状沟,拇指摁在那颗金属球上。
“爸爸,”沈晚看着他不断颤动的眼睫,甜声开口,“我帮你取出来,好不好?”
她指甲往下,将那颗和铃口紧紧嵌合的金属球抠出一点,沾湿的指尖毫不意外地触碰到因为疼痛而微微瑟缩的肿胀铃口,又湿又烫,相比她从这根作祟的马眼棒上获得的快感,容繁得到的更多的应该是疼痛。
他能忍到现在都没有软掉,确实是有几分资本的。
容繁没说话,但急促粗重的鼻息已经泄露了他此刻的煎熬难耐。
那根快要融进他性器里的坚硬,此刻正被她捏在指尖旋转着缓慢拔出。
被摩擦到生疼的脆弱内壁在这种故意的来回折磨中痛得他浑身都控制不住地颤抖起来,紧抿的唇终于被这剧痛撬开,他额上的冷汗滑进眼睛,将睫毛濡湿得更加彻底:“晚晚……”
沈晚勾住他脖颈,尾巴取代手缠住他被疼痛打击得隐有疲软迹象的茎身,手指捏着的那根金属棒更加快速地在他铃口进出:“爸爸,这样感觉真像我在肏你呢~”
她弯眼,鼻尖轻轻蹭着他汗湿的脸庞,“喜欢吗,这个速度,这个力道?”
容繁很清楚她想要听到的是什幺回答,干脆地吻住她近在咫尺的唇,汲取她唇齿间足以麻痹他痛觉,让他能够顺利给出一切她所需要的反应的甜津蜜液。
沈晚任由他索取,手上的动作不停,尾巴缠绕的茎身却一点点重振雄风硬挺起来,伴随着那根金属棒被彻底拔出扔到地上发出一声轻响,容繁也闷哼着撑住桌沿收回放肆的舌尖。
“爸爸好像快要被我玩坏了呢~”沈晚揩下射到自己腹部的精液,淡淡的乳白色中夹杂着丝丝缕缕的血红,很明显,刚刚那通粗暴的对待刮伤了他脆弱的内壁。
气味混杂的指尖被递到他唇边,他因为高潮而失神的双眼缓慢聚焦,张嘴含住她指尖温柔而熟练地舔舐。
“喜欢……”
沙哑虚弱的两个字换来的是她越发明亮的笑颜,被含住的指尖往内轻轻按压着他舌根:“真乖呀~”
除夕夜,持续了一整晚的荒唐结束于新一年的晨光破晓。
沈晚从昏沉睡去的父子两人中间起身,神清气爽地站到落地窗前欣赏着远处初升的太阳,愉快地眯起眼。
希望谢忱这条蠢狗在她离开的这段时间能多少有点进步吧,毕竟她的耐心可是有限度的。
“晚晚……”
沈晚转身看向床上此刻明明应该因为她喂的那滴血昏沉睡去的容繁,面上的诧异一闪而逝。
“爸爸怎幺醒了?”她走上前去,撑坐起身的容繁有些困倦地将脑袋抵在她肩上,沈晚顺势摸了摸他睡得乱糟糟的头发,“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
容繁只觉得自己眼皮子打架,血液里似乎都流淌着高浓度的安眠药,他猜测自己此刻的状态应该是被沈晚刻意调整成这样的。
这样神鬼莫测的力量本该叫人恐惧害怕,可他却觉得分外安心。
“没有……”容繁轻轻环住她,因为困顿说话声音很轻很慢,有种和平时截然不同的柔软,“怎幺不多睡一下,我很担心你的身体……”
沈晚抚摸他脑袋的动作微微顿了顿,半开玩笑地开口道:“爸爸,如果哪天我的这份力量消失了,你还会像现在一样吗?”
一样的听话,一样的爱她……
容繁艰难地睁开眼,双手捧住她的脸,认真而笃定:“晚晚,不用怀疑,任何时候你都在这段关系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
他很清楚,无论她是否身怀异能,他都会不可救药地深陷沉沦。只因,她是她。
“不过,那时候爸爸可能经不起太激烈的折腾了。”他也学着她半开玩笑,亲了亲她,“到时候可要对爸爸温柔一些。”
沈晚看住他蕴着温柔笑意的桃花眼,勾起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