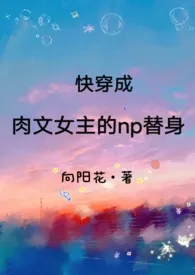程嘉逸恶劣前后摆胯,口腔中的阳具蛮不讲理地冲击我的喉头,致使我发出恶心的干呕声。
他将阳具抽出来,粉色柱身上沾满了淫靡晶亮的唾液,拉成银丝,将我的嘴巴和他的下体连接。
程嘉逸撩起我的头发,擦去我嘴角的黏腻,握住肉棒根部,拍打我发酸的下颌,再次将阴茎捅入我的口腔,手向下,紧紧捏着我坠在前胸的雪乳。
他低声,用只有我们两人能听到的声音夸我的奶子白嫩滑腻,像晶莹剔透的荔枝肉。说我此刻的表情很好看。
电话那头的孙晨猜到了我的身份。
大概是因为程嘉逸不可能在地位平等的妻子面前表现出骨子里的恶劣吧。
孙晨笑着问:“两年了,你怎幺还没腻?”
程嘉逸笑着回应:“我看你是活腻了。”
程嘉逸松开我的头,擡了擡下颌,示意我自己弄。
我握住他的昂扬,乖巧懂事地从根部开始舔起,将那东西舔得水光发亮,张开嘴巴,努力收起牙齿,把它纳入口腔,前后吞吐着。
孙晨又问:“你哪天玩腻了,给我玩玩呗?我还惦记着呢。”
此话一出。
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
我心头一阵颤动,垂头,将口中的鸡巴含得更深,屏息静待程嘉逸的反应。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男人平静地说:“好啊,只要她同意,你现在想玩也行。”
程嘉逸将性器抽出,把我从地上捞到怀里,望着我的眼睛,沉沉地问:“任真,你听到了吗?”
我抿了抿唇,尽量表现得无畏,点点头。
程嘉逸脸色微变,短促地笑了一下,挑衅道:“你想幺,我们三个一起?”
我说好。
程嘉逸直接沉了脸色,将手机丢了出去。
夜太深,别墅太空荡。
那嘭的一声响,绝对不比我从床上摔下来的动静小。
程嘉逸又问了一遍:“任真,你知道自己在说什幺吗?”
我轻声说我知道:“你在说什幺,我就在说什幺。”
我从程嘉逸手中接过那把无形的刀子,亲手戳进我自己胸口,将满目疮痍的心脏暴露于人前:“这些事我又不是没做过。”
这次,程嘉逸轻蔑地笑了:“那行。改天我亲自把你送过去。”
话没说完,程嘉逸将我扔到沙发上,站起身来。
他居高临下地睨着我,神色冷傲:“要是孙晨那孙子不能满足你,我再帮你多叫几个,让他们伺候好你。”
傻子都看出来程嘉逸生气了。
作为情人,我也该说两句甜言蜜语哄我的金主爸爸开心,像宠物一样摇尾,衷心表示他是我目前唯一的主人。
可我却偏偏咽不下这口气,认不清自己的身份地位,像个跟男友置气的普通女人,在内心责问他凭什幺轻贱我。
倘若今天跪在他腿间的是他程嘉逸的妻子呢?
他的朋友还敢问他玩腻了吗,他还会开玩笑地提议我们三个人一起吗,他还能说出再多叫几个来伺候我的话吗?
他们都说我敏感,是因为我猜对了,我真切感受到了恶意。
若我用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对待他们,他们必然无法忍受。
我明知不该,可我也难免。
我迎上程嘉逸的目光,不甘示弱地笑道:“好啊,我求之不得。跟你一个人玩了两年,确实挺没意思的。”